| |
|
|
| 天下檳郎 |
|
| 社會人文關懷,文學欣賞批評,詩文作品觀瞻 |
|
|
|
|
|
|
|
|
|
|
|
|
|
 | 檳郎的詩鄉 |
| | 檳郎的詩鄉
14中文師範 湯文文 題記:我是很難得能遇到這麼一個堅持着寫詩的老師,堅持着教書的詩人的。
中國詩人真正的覺醒是從第二代的北島、芒克、多多、舒婷等人開始的。他們以反思的姿態崛起了中國詩壇新的高度。但僅僅是十年,程蔚東等人就開始對第二代詩人說NO了。在整個80年代的中後期,中國詩壇風起雲湧、硝煙瀰漫,每一個山頭都升起了大王旗。第三代詩人就在這樣的紛爭中登場了。第三代詩人的發展掀起了口語詩寫作的強大的聲勢,我們可以接受文學道路上的創新,可以笑納所謂的反叛精神和不斷嘗試的勇氣,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容忍、“口語”和“口水”名詞界定的渾水摸魚。你告訴我“我堅決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場所/的衛生間/大便後/不沖涮/便池/的人”(《傻瓜燈———我堅決不能容忍》)是一首詩,他之所以與眾不同讓你難以接受只是因為你的自我更新能力不夠,趙麗華之所以被網友“惡搞”也是因為廣大網友活在體制中被壓抑之後的反抗,是對趙麗華同志名譽光環下的想當然的反駁,由此可見,詩壇已經處在怎樣的滿地狼藉之中。
就是在這樣的詩壇大環境裡,我遇到了檳郎,一個用心寫詩的大學老師。大一的時候上了他的“新詩賞析”選修課,自此知道了他上課的獨特方式;大二繼續選了他的“比較詩歌”,在古今中外的詩歌欣賞中對於他的詩歌價值觀也了解的更為透徹。相比較於所謂正統詩壇中榜上有名的某些詩人來說,他對詩歌的堅守更顯可貴,可親和可愛。
檳郎是一個多產的詩人。自04年以來,他對於詩歌的堅持就沒有停斷,幾乎每年都是以只增不減的姿態固守着他的詩歌情懷。檳郎的詩歌內容涉及廣泛,語言或平實或幽默或新奇或抒情,風格多變,唯一萬變不離其宗的就是詩歌中真摯如汩汩清泉浸入人心的情感。
我尤其喜歡檳郎對於家鄉巢湖的描寫。在之前的“魯迅研究”論文中我曾經提到,鄉土情結是連接我與魯迅,我與檳郎情感共鳴的軟帶。因了魯迅愛寫紹興,檳郎愛寫巢湖,而我恰恰最愛讀鄉土之風土人情。《打菹草的回憶》中,不論是狹窄的田埂路,竄跳着小狗的農家庭院,還是哼哼着吃飽後心滿意足的牲口的豬圈,長滿菹草的大凼……都是生動形象的畫面,仿佛過樣片一般一幀一幀在腦子裡放映。打鵝草的鄰家小妹回送我“妹家的葡萄”,少年呆呆地看着她甩着兩個長辮子漸漸走遠,小小的幸福感在胸膛里蔓延。“打菹草的山鄉少年”一邊勞作,一邊想象着山外的世界,那裡有他的夢想,那裡有他的期望。
如果說《打菹草的回憶》寫出了山村少年的單純,山村生活的簡單幸福和淳樸感動,那麼《燕子歸鄉》便是徹徹底底地將身心埋在故鄉的土壤中,噴發出深厚的思念,吟詠出連綿不絕的讚歌。“迎着春風而回,故鄉的山水格外親近,每一座村莊,每一棵樹,每一個開花的小院”,詩人踏着春風,風塵僕僕從千里之外回來,越接近故鄉嘴角的笑意越急不可耐的綻放在臉上。村莊,樹和每一個開花的小院,都有着他獨有的記憶和迷人的屬於時光的芬芳。舊居“對關的大門自然留着縫”,等着遊子隨時隨地的回家;“大梁上的泥巢里”,舊草仍保持着柔軟如“我”一直感受的那樣。記憶回到漫長歲月的某個節點,“牧完牛的小主人”蹦跳着回應“老友激情的呢喃”,“我”與“兒時的燕子”那時共同擁有一個溫馨的家,經歷過短暫的秋後別離,嚮往過美好的春日相聚,只是“多少年沒有再見了?在被它遺棄的外省都市裡。老屋的門還微開着,故交已似我一樣變老吧?”舊居的門裡是“我珍藏的少年的回憶,門外的“我”煢煢孑立,怕容顏無法掩藏的皺紋告訴我故鄉之故終究會是要慢慢接受的現實。詩人檳郎由此詩婉轉訴說的是他對故鄉深沉厚重的思念與愛,是他對時光流逝的無奈與悲哀,是他仍嚮往未來與故人重逢的欣喜,是他執拗的相信心不老一切都還是最初摸樣的孩子氣。
大部分時候的檳郎是一個享受生活的資深文青。他喜歡旅遊,喜歡交朋友。旅遊無論近遠,朋友不分性別,便是年齡也仍是無所謂的。檳郎和學生的關係很好,時常會有與學生吃飯談心或是方山遊玩等的小約定。三五成群亦或是雙人漫行,都自得其樂。就算是自己一人的出遊,他也能靜心享受,觀賞每一處風景,就像人生一樣,走得精彩就斷不會跑起來。無論是熟湖的菊花園,姥山島,明堂山,還是春夏秋冬的校園,都是他筆下的常客。他曾說自己是閒人,“坐倦書齋,出門散心,愧對忙忙碌碌的天下勞人”(《閱江樓上的閒人》),在自然風光中放鬆心情,看那“江邊小丘如青螺”,“五馬渡江,中原難歸”,“梟雄爭霸”,然今“一紙空文”,歷數往昔,盛世也好破落也罷,和平也好戰爭也罷,無數能人志士在歷史長河中趟河而過,不免心中悲涼,“最惆悵,無用是書生”,書生如何,將士如何?但“能如江渚上白髮漁樵,閒看秋月春風”,便不失人生趣味,自在逍遙。再看那《五月的梅花山》,“我”錯失了開花之季,如今茂葉之中一片靜謐,“我來又能尋覓到什麼?”“惟秀亭里空空蕩蕩,梅花妝韻無人欣賞,商飈別館不聞猜拳喝令,台想昭明我獨心傷”,就算是無人欣賞也能綻放姿態,傲立挺拔,念念不忘,終有迴響。“遊客都擁在石象路了,奔向暴君的墳冢;我卻要找梅娘雕塑”,“倚在梅花仙子裙邊,細細地咀嚼青青的梅子,啊,又酸又苦的玉丸,仿佛立即能成仙。還是待到成熟的時節,再來飽餐個痛快”,“我”不去人云亦云地奔向眼球中心,只是孤落落尋找知音。梅子的酸澀不就如人生百味,不是所有的舞台都有觀眾,而“我”仍能沉醉一個人的狂歡。檳郎平日裡其貌不揚,溫文爾雅,甚少發脾氣。課上不聽講的,他也只是感到惋惜,讀他自己的詩作時不是非常在意是否有人在聽,只當做是寫完之後再讀一遍的再體驗,箇中心情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至此我似乎來了一點憤青的心情,只是這種憤怒最終也只會在現實的冷水下涼到心。我只想問問那些所謂詩壇大家獨領風騷的“下半身”寫作的朋友們,你們真的對得起如檳郎這般默默堅守詩歌最本真面貌的詩人嗎?你們一味追求的“創新”到底有多少存在的價值?一味調侃愚弄的大眾在你們眼裡是身份不如你們,智力也甚低下的原始人嗎?除去了互相追捧得來的頭銜之後你們是否會是一群“裸露”變態中的佼佼者?
人們大部分時候不會關注個體的默默付出,默默奮鬥,默默堅持,只會隨波逐流的關注熱門,追名逐利的站隊。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如檳郎一般為着心中對詩歌的熱愛,為着替浮躁詩壇保留一份乾淨的善良,為着內心情感的噴發而選擇默默的詩人,他們得到的不應該是熱鬧人群背後的落寞舞台。
有人會說,一旦這樣的作家,這樣的詩人所獨處的淨土被慕名而來的遊人踩髒,你怎麼保證他們不是下一批“下半身”?說實話,我自然是不能保證。然而你總得相信一種積蓄在黑暗泥土裡等待噴薄而出的力量的強大。以純淨為根,拋卻的浮華,你憑什麼以為他們在享受過這樣的不為名不為利只為心中堅守的清澈之後,還會有人踏進萬劫不復的泥潭沼澤?
“不萎縮,也不張揚,就那麼靜靜地挺立,亭亭玉立於清波之上,丰姿綽約於碧葉之間。聚萬千風情於一身,又是那麼的自在幽嫻”(《面對荷花》),“我知道,你的存在,只是自然的自我呈現。我也是,但是那麼不同,我的殘缺你的完美”。你是不是最喜歡荷花?因為你筆下的她那麼像你,那麼與世無爭,那麼褪盡芳華。你深知的,把根插進最深的泥土吸收養分才能枝繁葉茂;你深知的,“病蚌育珠,最痛處的腫莖,最厚的包裹,密布絲線與氣道,才是香甜脆綿的藕”(《江南荷韻》);你深知的,一粒種子習慣於長期打基礎,才能盤根錯節,繁茂一整片天空……你必定是深知的,所以你活得灑脫,或時而帶點悲戚;你活得自在,或時而也會迷茫;你活得努力,或時而也曾放棄。只是我眼中的,堅韌不曾屈服的你,個性敢言的你,幽默孩子氣的你,都是詩里的你,都是真實的你。
“什麼是最幸福的事?蘭舟上的採蓮女的窈窕,熱辣辣的情歌,纖纖的素手。”檳郎有如此這般的詩鄉,就是個幸福的人。
2016-6-6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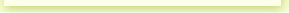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