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天下槟郎 |
|
| 社会人文关怀,文学欣赏批评,诗文作品观瞻 |
|
|
|
|
|
|
|
|
|
|
|
|
|
 | 诗人槟郎的情怀 |
| | 诗人槟郎的情怀
武青青 说起槟郎,大多数人对他的定位是教现当代文学的老师;上过他的选修课稍微了解他的人也会知道他是一个爱游山玩水的会写诗的徒行者;但是你如果平时留心观察过他,从他的不经意的话语和行为中,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老师这个身份也许是他养家糊口而不得已从事的职业;旅行者这个身份也许只是他吟诗作赋获取灵感的来源;但对诗歌创作艺术的追求才是他最终的归属。
槟郎首先是个诗人,他所有的情感与经历都可以从他的诗中有所寻觅。他的诗歌有写故乡的,《故乡的葵花》“故乡的神的花朵,朗朗乾坤。在故乡的田塍边溪塘边,农田里山坡上,到处都是,小树一般亭亭玉立的苗条腰身,扇一般的叶子,天神一般的花盘。那黄色和绿色浓抹的世界,天高气爽,蓝天白云的背景,还有什么比你更诱人的伊甸园?”借故乡的葵花来抒发自己对故乡的那种深切思念。我甚至能想到槟郎在写这首诗时嘴角露出的笑容,故乡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每当槟郎触碰这份柔软时,必定是开心又惆怅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再怎么不起眼的葵花,在槟郎的笔下就发出“再没有比你更神奇更灿烂的花了”的感叹了。家,只是一个字,却是在经历了纷纷扰扰的世间情,世间事,世间人纠缠喧嚣之后,一个最温暖的去处。对于槟郎这个漂泊外乡的游子,家的意义对他来说更多的是个精神支撑了。而槟郎对家乡的热爱与思念绝不是这一首《故乡的葵花》可以说的尽、道的完的。《巢湖西坝口》、《故乡的油菜花》、《忆巢湖姥山岛》等等还有许多举不尽、列不完的诗都寄托和诉说了槟郎对家乡的那份深情。
他的诗有写爱情的。初识槟郎时,觉得他是个毫无情调可言的小老头,读了他的诗后才发现自己对他的定位是大错特错了。从他的诗中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浪漫深情而又充满幻想的人。在《女神的小城》中槟郎对自己的爱情婚姻充满了憧憬。“美丽的女神来了,走到夫子庙泮池边,裹嫩黄灯芯绒的外套,浓密的长发如披风将双肩笼罩。从手套中抽出纤纤玉指,在寒风中握住我,拖我走向烟月深处的秦淮人家。升州路上的婚纱照和文德桥边的喜宴之后,月亮甜蜜在安德门出租屋里”。这样的爱情在平淡中渗透出丝丝甜蜜,怪不得槟郎会说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般的诺言呢!不过有时觉得挺可惜的,槟郎的这份深情与浪漫全都给了他笔下诗歌中的姑娘了。而他实际上是个内向拘谨、不善社交的人,每次读他的爱情诗,在感受槟郎的浪漫与想象之余,也能窥探到他内心的那份孤寂。
对于槟郎来说,“故乡”与“爱情”只能算得上是他的小情,而他的大爱则是国家了。他的诗有许多表达的是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表达了他对这个国家的担忧和对国家前程的祝愿。《太石村在落泪》中,“国歌唱了多少年,我们的心很热,天总是很冷”。槟郎在这失望的环境中仍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祖国便是我的宿命》中,“祖国便是我的宿命,只要有一口气,我便挣扎开肿重的双眼,蠢动着苦闷的激情,继续写下笨拙的文字”。他以弱小的力量诠释着对祖国全部的爱,最后不惜发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的呐喊。槟郎对祖国的爱别人是不能感同身受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对这片土地倾注了多少爱与热忱。
槟郎的诗还有很多很多,包含的范围也很大很大,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三个系列----写故乡,写男女爱情,写祖国。一个既有小情又有大爱的人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槟郎是诗人,一位其貌不扬但却有灵魂的诗人。槟郎不仅仅是位诗人,我说了,他还是具有宗教情怀的人,在他心中宗教占有重要的地位。
槟郎对宗教的热爱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早在他的大学时代,他就想皈依佛门,奈何由于种种阻碍,最终没有随了他的愿。但是他对宗教的那份热爱却丝毫不减,甚至越来越痴迷。也许很多人对槟郎的这种宗教情怀是不理解的甚至是不屑的,但槟郎总是以“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心态一笑置之,只能把他的这份痴情倾注到他的诗中。《槟郎前生为僧》中,“槟郎在海慧寺为僧,方山隐逸,何曾问过时政?”槟郎幻想自己前生是位僧人,那种宗教情怀是由前世而来,今生也必定为之而去。
《有个禅师叫法融》中,“我在山上,看到了你的白石的塑像,使我惊喜,向你鞠躬”,槟郎的那怀着崇敬而鞠躬的身影浮在我眼前,我想即使当年唐皇赐建的繁盛的寺庙的牛首山,而今只剩下一两间陋屋,一个牛角也已被铁矿挖塌,那弘觉寺也避讳换字,但是法融遗留下来的那种精神文化一定一直存留在你心中。《灵谷寺的桂花》“灵谷寺的桂子繁多,金桂似灿,分布最多;银桂若雪,少而珍奇;丹桂如火,花开最热烈”,因为对佛教的热爱,所以在去灵谷寺的时候对其内景色观察的十分仔细,一花一草都被他赋予了生命。
槟郎也曾关注基督教,《怀念耶稣》中,“我走向你,道路真理和生命,凭着无神论时代的诗神的密令。”他也关心伊斯兰教,写过《怀念穆罕默德》等诗歌。他想皈依佛门,想投奔耶稣,但都落了空,我想当时他肯定很失望吧,甚至也很迷茫吧。好在上天垂怜他,给了他一个容身之处---道教收留了他。至于为什么只有道教才成为他最终的归属,他在随笔《谈方山洞玄观的群聊碎语》中有做说明:“首先,我好像生来就有宗教情结;其次,我出过家未成功,进入基会读经班,也没找到感觉;再次,后来发现除了宗教情结,还有民族情结,而道教是唯一本土大宗教,中国文化根底”。从此他就有了一个精神家园,他开心的像个孩子。住持孙敏财道长和他很投缘,他成了那边的义工,我想这就是他的归属感吧,就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瞬间找到了家的方向,别人是不懂也体会不了他心中的那份雀跃的。他把他从中获得的欢乐和满足都谱写成了诗歌。
《初游茅山》“大茅山巅远眺,三天门上叩谒三清;积金峰南坡流连,第八洞天,第一福地。道祖广场和睹星门;仙人洞和华阳洞,还有喜客泉的咕咕声”。面对“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中国道教圣山茅山的如此美景,就算是诗人槟郎也只能用最原始的语言“茅山,我神往的人间仙境”来叹服。茅山再美奈何距离太远,但好在离槟郎家近的方山洞玄观也算得上是一个小茅山,槟郎为它写过不少诗。洞玄观是“七十二福地”中的“第69福地”;这不禁使槟郎感到他家附近有“福地”,便也觉得“槟郎道人”是有福之人了。
槟郎爱道教,时时把道教的发展境况放在心上。槟郎为洞玄观的重建捐了三百元,并且表态:“永远支持洞玄观建设,敬畏祖宗神灵,弘扬民族文化”。他还认为教內之人应该主动关心芸芸众生,主动引导他们向道,虽然无缘不化之人也只能随之,但是要有足够的主动努力。面对如今道教的不景气,槟郎写诗《遗弃道教的南京》来抒发自己的愤懑:“而今南京道佛基伊多少寺,大兴土木,多么奢靡,还有几个是祖宗的原创?”这是槟郎为被遗弃的道教发出的声声呐喊。槟郎对宗教的痴迷之事无法在我笨拙的笔下尽显,但是我能切身感受到他从多个宗教中徘徊、迷茫,最终归属于本土宗教道教的那份窃喜,以及想为道教重建贡献自己微薄之力的热诚之心。
槟郎有多重身份,但在我眼里他只是位诗人和一个单纯的宗教徒。他是个有灵魂的诗人,是一个有信仰的宗教徒;之所以有灵魂,必因其有信仰。我这个算得上他半个弟子的假徒弟,却是永远学不会写诗的,我爱读诗,但绝不提笔去写;不过如果有机会倒是可以一起去道教的洞玄观做义工,借着本土的道教文化来洗涤自己的灵魂,跟着他一起不为求丹炼药长生不老,不为讲经论道探讨学术,只为传承本土宗教文化,接受道教神灵熏陶。当然,槟郎本质上是个文人,他对宗教是很文学化地对待的,并且也是包容了儒道佛基伊而以原乡的道教为主的,有容乃大,这也促进了他的诗歌写作。
2016-11-6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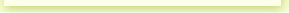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