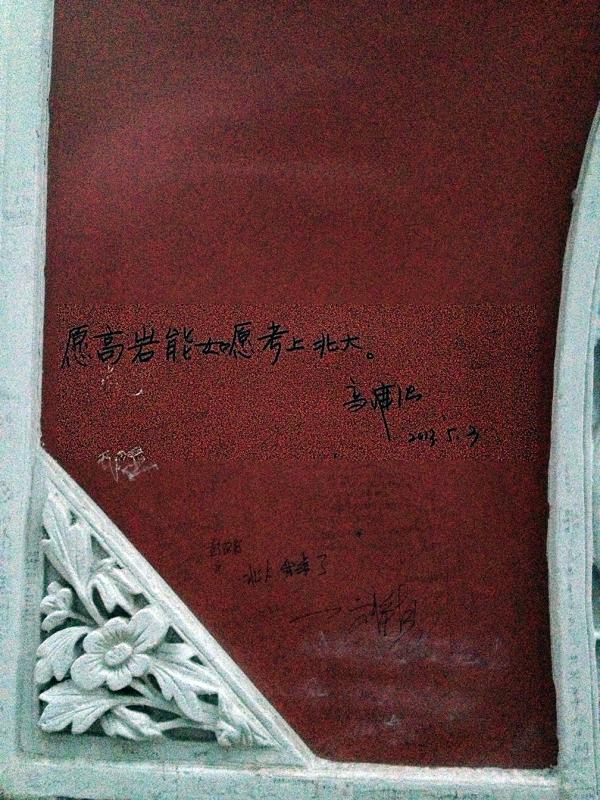
懸 賞 當我從深圳市公安局刑偵科第三室靠近門口的那個辦公桌上把十五萬元嶄新的人民幣往我的帆布口袋裡摟的時候,我的手是不停顫抖着的,我竭力控制自己,但我根本就控制不住,像我奶奶七十歲那年突然得的一種怪病,拿任何東西不管輕重,手總是抖過不停。刑偵科科長讓我簽字的時候我的手還一點都不抖的,後來每當我回憶起這個細節,我總是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結果絞盡腦汁還是不明所以,或許我簽字的那一刻我還是沒有想到我真的能拿到那麼多的錢,只是把公安局要找的一個人的位置告訴給警察就能拿到錢,這一點我是不太相信的。然而我真的拿到了,而且是他們說的十五萬,一分都不少!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今生會一下子擁有這麼多的錢!我神色慌張地收緊布袋口做賊一樣躡手躡腳地離開了刑偵科的辦公室,三層樓的樓梯我不知道是怎麼下來的,總之我一個台階都沒有感覺到就下來進了停在樓下的我的紅色出租車裡。我沒有馬上去銀行,而是直接開回了我的住處,我要好好看看這些錢,儘管臨走前那個矮個子科長叫我注意安全,也許他是想拍着我的肩說注意安全的話的,因為我的個子比他高出很多,結果他只拍到了我的肚子。 我住的地方是深圳典型的握手樓,站在房間的窗前伸一下手就可以握到另外一棟樓的窗戶里生出來的手,如果恰好那裡有人願意跟你握手的話。這就是最具深圳特色的農民樓,因為誰家都不會輕易把樓基往地界後面退一毫米。如果有一個老人到我的老家也劃上一個圈讓全國人民來開發,變成一塊熱土,也許我家蓋起樓來更要寸土必爭睚眥必報的。本來出租車公司是有集體宿舍的,但因為條件差環境吵且每個月扣的錢卻很多,我睡覺又特別挑,只要有吵聲我就睡不着,在家的時候,我睡不着的時候我那整天托着個長煙袋靠在牆根的父親總是說我是沒有乾重活作怪。不管怎樣,既然干着這份把命搭在油門上的職業還是讓自己睡好覺為重,所以我還是自己租房子住了。像我這樣的農村人也許永遠只能跟農民打交道,特別是在這樣的城市,誰會看得起我?誰會把我當人看?正如一幫窮哥們在一起說的“命苦,不能怨政府!”我出生在那個恨不得把泥巴抓起來當飯吃的山村里,能怨誰?要怨就怨父母做愛的時候不注意安全,但他們做愛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生孩子啊,不是我就是另一個跟着一起受窮的傻小子或傻丫頭。不過感謝父母給了我一個好腦子,沒用專門交學費,跟村上一個運輸專業戶跑車我竟學到了開車的技術。 回到房間我立刻關好門還插上了插銷,其實平時睡覺時都沒有這樣嚴實過,因為我從來就沒有什麼能讓小偷惦記的。現在不同了,現在咱有錢了,而且是十五萬。是能讓我那癱瘓在床的母親嚇暈過去的那麼多的錢。我把錢從布口袋裡一疊一疊地拿出來,這一疊一疊的像我老家過年時鎮上賣的雲片糕,只是這每一塊雲片糕的正面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標準照和他老人家安祥的笑容。我一疊一地地撫摸着,像是撫摸熱戀的情人,當然是我想象中的熱戀,因為我壓根窮得還沒有找過情人,在這兒開出租除了賺一個每天在車裡風不吹頭雨不打臉之外沒落下什麼錢,因為要上交的費用太多,組長說上面各層各級的領導占的乾股太多,所以出租車的價格一直降不下來,生意不好。每個月的兩千多塊錢除了我的衣食住行剩下的就剛好夠我老娘的醫藥費了。幸好老娘在恰當的時間癱瘓,如果不癱,他們一準還會給我弄出個弟弟或妹妹,那他們的學費還得我去拼命地踩油門。 我不知道自己把這些雲片糕撫摸了多久,當我那些天馬行空的萬千思緒喀嚓一下斷掉回到這些錢上時,我發現自己的手還是不停地抖動着的,跟剛才在刑偵科里抖動的節奏一樣,我還是控制不住自己。但是我的直覺告訴自己趕快去銀行存錢,否則以我這樣的情緒可能會出事。於是我顫抖着把一疊一疊的錢又塞回布口袋,像抱着嬰兒一樣鑽進出租車直奔銀行。在銀行的櫃檯前,我還是顫抖着填了存款單連同布口袋一起遞給了櫃檯前那個漂亮的小姐,靚女滿腹狐疑地把身份證上的照片跟我對照來對照去,我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因為再拖一段時間我也懷疑這些錢是偷來的。想到這個,我的思維像是電的兩極被突然搭在了一起,衣衫襤褸的牛家官在垃圾桶旁那雙又黑又髒的手揮走一群蒼蠅抓起飯盒裡的剩飯朝嘴裡猛塞的情景立刻就浮現在我腦海中。 每天在街上拉客的間隙,看報紙幾乎是我固定不變的內容,當然,那些報紙並不是我買的,有時是乘客扔下的,有時是公司的同事看過的,如果某一天既沒有乘客扔也沒有同事給,我就把前一天看的報紙上沒有看仔細的內容再重看一遍。也正是那天中午我在重看前一天的報紙時注意了那個信息,那個看上去根本就不強壯甚至讓人覺得很膽怯的大學生牛家官他在宿舍里殺了四個同學,就在大學的三年級,再熬一年就可以畢業了,他卻殺了人跑了。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心態,我仔細地閱讀了報紙上對他描述的那些文字,我一向不太相信報紙的內容,所以我讀報紙都是反着去理解,讀完之後我莫名地覺得自己似乎能理解牛家官的心情了,因為我也有過貧困得被人嘲笑的時候,也有過因為沒有鞋子不敢進教室上課的時候,我甚至也有過想把那些從心底看不起我然後只在眼角傳遞鄙視的小子們猛揍一頓,但那也只是想想而已,因為我怕萬一撒不住手,把人家揍傷了我連醫藥費都付不起。沒想到這小子竟然幹得這麼驚天動地。 後來的日子我每天一閒下來就想這個牛家官的事,遇到願意跟我說話的乘客我就會搭上去聊幾句,聽聽別人的想法,探聽一下進展。但我發現所有的人都是用恨之入骨的口氣詛咒牛家官,於是我絲毫不敢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我想,對牛家官的理解我應該是另類。在不久之後的報紙上就出現了懸賞十五萬的大幅標題。那幾天公司里認識的同事談論的話題都是這個十五萬元人民幣。我沒有一點興趣,因為牛家官不知道在中國的哪一片土地上,即使他到了深圳,我整天出車不可能碰到他,碰到了舉報了警察也不一定能抓到他,抓到了也不一定能拿到那十五萬,懸賞這樣的事是解放前的行徑,現在只是用作宣傳宣傳,當不得真的。 但人總是有活見鬼的時候,那天我居然就見到了牛家官,否則就不可能有後來我的一系列節目了。那天是給車做保養,這家裝修、保養兼洗車的公司就在我們公司的隔壁,在洗車場的旁邊有一個公共廁所,這也是我們出租車司機最常用的廁所,廁所左前方有一個垃圾桶。車的保養還要兩個小時,我那天上完廁所出來時就一直在考慮怎麼打發這兩個小時的時間,這個時候,我游離的視線里就出現了牛家官,他正躬着身子在垃圾桶里翻找,好像他什麼東西被不小心丟到了裡面。我出於好奇就走了過去,這才發現他身上的頭髮衣服都又亂又贓,還散發着一股酸臭味,可以想象他已經好久沒有洗澡了。看他迫不及待地揮趕着蒼蠅去抓吃飯盒裡的剩飯,我想他一定已經餓得不得了。我小聲地說了句吃這樣的飯會生病的,他居然聽到了,立刻抬起頭望着我,我瞬間覺得這張面孔有點熟悉。他也一直跟我對視着,也許他已經猜出是怎麼回事了。他說這是他兩個多月來聽到的唯一對他說的話,且還是關心他的話。說這個話的時候他的臉上好像還出現了感激。聽他說兩個多月,我的腦海中立刻掃描到了牛家官三個字,我突然指着他說“你是”,我還沒有說出來,他就打斷了我說,沒錯我是牛家官,是正在被通緝的殺人犯。他說公安局現在報紙上懸賞呢,你去舉報吧,可以拿到十五萬的賞錢,真的,你去舉報吧,我不走了,真的不走了。我說既然這樣你為何不去自首?!他說我去自首也是槍斃,身上背着四條人命呢,還不如讓人拿筆賞錢,也算是我被槍斃前做了一件好事,就衝着你剛才跟我說的那句話,我就坐在這兒等公安局來抓我,你去舉報吧。我聽了他的話覺得特別不真實,當我看到牛家官一臉的誠懇,我的心底又油然升起一股近乎敬佩的感覺。我問他你為什麼要殺人,而且那麼殘忍並且殺了四個人。他說人都殺了還問為什麼有意義嗎?所有的事情都能說得清為什麼嗎?任何一件事情都只有簡單的答案和理由嗎?他說這番話的語速很慢,眼睛突然變得很空茫。說完之後臉上浮現出一副已經與世隔絕的神情。這時的我反而一點也不想舉報他了,甚至瞬間產生了一種不希望他被抓住的想法。見我一直沒有動,牛家官似乎很着急,他說真的,我真的很想被抓去伏法了,誰都不知道這兩個月來我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餐風宿露提心弔膽,連飯都沒有正經地吃過一頓,無論什麼樣的毅力都無法抵擋心理的這份煎熬。我不想再這樣活着了,我想早點死,請你去舉報吧,我只想成全你這筆賞錢,這是我還能做的唯一的事情了,求求你了,你也成全我吧!說着他就要在我面前跪下了,我一下子慌了,忙伸手去扶他,但是他堅決不起來,他說我一天都不想再逃亡了,你去舉報吧,我給你電話費,我這兒還有一張電話IP卡,給你用吧,我這兒還有錢也都給你,我殺過人帶出來的錢一分都沒有用,沒有機會用,你幫我用出去吧,這些錢都給你,說完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已經摩得看不清畫面的電話卡,然後又把手伸進褲腰,在貼身的小口袋裡扣出了幾張皺皺巴巴的一百塊錢,雙手把卡和錢一起塞進我的手裡。那一刻我似乎被感動了,我後來苦思冥想自己到底當時是怎麼考慮的,卻始終沒有一個完整的答案。我真的去三四十米之外的路邊電話機上打了110。牛家官被帶走的那一刻他朝我點了點頭,一臉的讚許,像是我做了一件對人類特別有意義的事情。這就是21年來最讓我刻骨銘心的事。 有了這筆賞錢之後我就辭掉了出租車司機的那份工作回老家了,娶了媳婦養了兒子,後來還跑起了運輸,雖然沒有致富,但家裡從此脫貧了。不過生過兒子之後剩下的十萬元錢我在銀行存了十八年定期,留給兒子上大學用,這之間不管發生什麼困難遇到什麼樣的資金短缺我始終沒有去提取過,一直到我兒子考上了一所他自己也夢寐以求的重點大學。兒子開學要離開家的前一天我喝了很多酒,還專門開着車帶着兒子去銀行取了錢,然後把錢換成了活期的又存了起來,當然換成了兒子的名字。事情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着,我心甘情願地從中年亦步亦趨地向老年踱步。可是沒想到三年後卻發生了那樣的事! 也許是一種報應吧。我兒子跟牛家官不同的是在大學二年級就殺了人,還有他是在同一天不同時辰殺了四個人,真不明白是怎麼殺的。如果我能找到他我一定要問問他,不問他為什麼,我知道到這樣的景況是問不出為什麼來的,我要問他到底是什麼動力讓他連殺四人,而且是同一天。 今天的報紙上已經在懸賞了,三十萬!中午有記者打電話到我家問我對這件事怎麼看?我說,無可奉告! 2005年11月11日凌晨 深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