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天下槟郎 |
|
| 社会人文关怀,文学欣赏批评,诗文作品观瞻 |
|
|
|
|
|
|
|
|
|
|
|
|
|
 | 逍遥的采诗匠 |
| | 逍遥的采诗匠
16秘书学 刘丹妮 风书月影,春风笔瘦。我恍然间将指尖触在显示屏上,隔着冰冷的荧幕,我却能从其上白底黑字间抚摸到属于一位笔名槟郎的诗人的温暖。我曾向我乐好游山玩水的父亲提到过我的一名老师,而关于他,不得不说能与其相识是一份特别的机遇。兴趣使然,亦或许是冥冥中自有天意,我在大一下学期抢课时有幸抢到了由李槟(不知为何,我更喜以笔名称呼他)教授的选修课“旅游文学”。而在经历了数月的学习后,我不禁感慨:遇见这一名采诗匠,何其甚幸。
槟郎,原名李槟,是文学院的一名副教授,听说他还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希望在往后的日子能有机会去聆听。再谈回旅游文学这门课本身,槟郎风趣诙谐的言谈令我沉迷在那五光十色的世界中,他的作品也令我流连,不禁反复品读。
读槟郎之诗,明槟郎其人。我漫步于槟郎笔下的丹青雪色间,试图去更深地了解这位其貌不扬、朴实憨厚却心藏炽焰的红尘逍遥客——是的,逍遥客。
在我看来,槟郎虽常自嘲地称自己为“教书匠”,他戴着厚重的黑框眼镜,淡淡笑着,却仍是掩不住文人的不驯风骨。他说,“寒风中的虬枝伸展,孤傲的花朵璀璨。剖身的杨邦乂的铁心,灭十族的方孝孺的傲骨,都征象在这片花海”。这仅是在说梅花与义士吗?浓墨重笔下,是否还有一颗热血的心中随寒梅开绽而砰动得愈发激烈?我想象一人于梅树下举樽豪饮,杯中梅影浮沉,竟有风雷之声,这便是槟郎的力透纸背的笔力罢。似经半生倥偬戎马,踏过千峰万仞,碾星夜为墨,取日月作笔,落天地为宣之大气!一名授学的教师,也能发出“私家江山在宿命里兴亡,总有凛冽的霜雪,必有碧血丹心的疏影。"的兴叹。然《雨花台的梅花》一诗,却并非是在开始就写道一腔热血与家国兴亡。欲赞其骨,先扬其表,亦连其心。“白梅如雪,红梅如霞,绿梅如晶莹的翡翠,在这细雨的年节,在这江南霾都的一角,寂寞地为我绽放。”花开一瞬,梅树下茕茕人影心绪难平,如江流泛涌,一人江畔抚琴,终奏一曲激昂。
然槟郎有的不仅是金戈铁马下的铮铮硬骨,他还有自己的温情。是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细看这一首《执手桃叶渡》:“牌坊上的对联,楫摇月,枝带春。那叫纪映淮的伤情女子,又当多羡慕你。坐在滨水的茶桌边,看着碧波的河,想到王献之的艳情,我们的初次约会”。那名诗人含情脉脉,他的妻子顾盼生辉,恍惚间能望见“丹唇外朗, 皓齿内鲜, 明眸善睐, 靥辅承权。 瑰姿艳逸, 仪静体闲”的佳人倩影。桃叶桃叶,让人不禁忆起《诗经·桃夭》,其言“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而槟郎想描绘的不也正是这他与妻子的和睦,举笔间尽是款款深情,惹得纪映淮欣羡,又比之王献之与桃叶的恋情,使人不得不称赞一声——妙哉!逃之夭夭,灼灼其华。惟愿现世安稳,勾唇相视一笑。
而云山画梦,在观尽铁马冰河,莺燕良辰后,槟郎又引领我们前往六朝古都的著名胜景:“古都解放门台城南面的鸡鸣寺路,樱花盛开。”他言,“樱树尽花,花如雪,天女巧织的绸缎,锦簇成精致神奇的花朵;大片大片,如白沫的海洋,又如纯白蒸腾的祥云”。我似在这寥寥几笔间见滂沱樱雨,槟郎细腻的笔绘下,予人“蕙风轻卷舌,樱雨细沾唇”之感。世人称道娇兰清竹,却时常忽视疏樱暗香,而槟郎却能在阳春三月的明媚下追寻那一抹樱芬,似与一千多年前的那名诗人在某一瞬产生共鸣——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槟郎笑,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见那一袭红衣夺目于玉树琼枝间,这是怎样惊艳的一幕哇!春风骀荡,早梅凋零,牡丹未盛,唯雪樱韶朗,幽芬浮藏。
再言回课堂。李太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言:“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如若将其翻译为白话,则顿觉与槟郎教授我们的这门旅游文学有扯不断的联系。天地是万事万物的旅舍,光阴是古往今来的过客。而人生浮泛,如梦一般,能有几多欢乐?古人持烛夜游,确实有道理啊。况且温煦的春天用艳丽的景色召唤我们,大自然将美好的文章提供给我们。是啊,大自然以美景呼唤我们,将美好的文章提供给我们,这不正是呼唤我们观尽名川大河,行遍五湖四海吗?而槟郎作为一名采诗匠,以小我观大我,见微知著,用欣赏的眼光去看身边的一景一物,一叶便知秋。
他好似一位浪子,逍遥畅游天地,故我在此篇开头就写道,在我心中,他是那不拘于世的红尘逍遥客。而他虽为布衣,却不胆怯权力。他在《布衣之怒》中写道,“你手上有权力,我空手也有菜刀才平等。唐雎不辱使命,布衣之怒使我站起。”昔秦王天子之怒何其可怖,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槟郎自比唐雎,不畏权贵,正是有如此心胸,才能广纳山川美景,才能用一颗昭昭明心去往他想到达的每一个地方。这份情怀是如何难得?
“功利在身边翻滚,情欲在身上坠落。色相即空,随缘任运,他傲然地扭过头去。”他在这首《居士的情怀》中这般写道。以窥破六道红尘的目光,此身缥缈如浮云,功利终为身外物,既“探不够重重地狱,究不够重重天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众生偏向地狱沉沦”,何不“参透今生的奥秘,感动宇宙的情怀。终于成圣,毅然决定:度尽众生方离开”?笔句大开大合间一腔豪气油然而生,从始至终,初心未泯。党怀英《村斋遗事》有言:“人生天地真蘧庐,外物扰扰吾何须。”而槟郎向来专注于诗,身投文炉,《居士的情怀》中的词句与这两句正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作为高中的篇目,此句想必我们无人陌生。虽用于此或许并不说特别合适,但那种心境想必正是槟郎所追求的、所修炼的。而逍遥逍遥,何谓逍遥?身居于市,指握笔砚,心存四海,如是而已。
可逍遥以外,槟郎,也向往山林隐士的生活,或许他本就有一份恬淡的心境。《方山记事》中,“劳累了一天的太阳,只待将最后半张脸也隐去,休息的时候,方山脚下,东坡畦里的人影赶在夜来之前,忙浇园,拎桶抄瓢菜垄间。”我看到一人忙碌却乐在其中的身影,他唇角或许还携有轻浅的笑,他“挥汗如雨地耕耘和播种”,在他身上,五柳先生的影子渐渐浮现出来,我恍然大悟,这不正是陶潜在《归田园居》中描绘的隐居生活吗。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正是有着相似的志趣,他们才能在千年后有着如此心曲共鸣吧。“真正的农民被赶走了,这里圈进了江宁科学园。便有业余的陶渊明不忍见地荒,相邻的主人交谈种菜的经验,相约着地主收走便潇洒地再见。”看,槟郎也是如此认为,他正兴致勃勃地在诗中与陶渊明交流种菜心得呢。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方山暮色下,采诗匠扛着荷锄,悠然而归。
我欣羡槟郎有如此心境,他是驰骋沙场的将士,是云游四海的浪子,是将与妻子携手青丝化暮雪眼含柔情的丈夫,是南京方山下的隐士,而归根到底,他是一名诗人,一名揽风光付笔墨的采诗匠。
“一条长长的栾树路,横亘在文学院的楼前,独特的风采,特别的情感,闪耀在我天命的诗篇”,“我在逐渐地衰老,栾树路不离不弃地陪伴。记得何时初相见,确已熟稔到心灵共颤。”木栾是无花的乔木,可当我行走于校园的栾树路间,就会想起槟郎的这首诗,每当这时,清风就似携来一阵诗香,令人沉湎其间。我想,这就是属于槟郎诗歌的魅力罢,那镌刻着特别情感的诗篇,其独特的风采,是指引我在学海中前行的启明星。
他的脚步终将踏遍河山,留下一个又一个故事,一首又一首诗章,这是行者之路,亦是文学之路。不知还能同槟郎在文学的道路上行走多久,风雨兼程,唯愿这一程能再长,再长一些。
2017-5-9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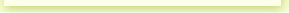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