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谷优加子是个会讲中文的日本人。 她学中文其实才4个多月,就已经能讲一口好听的普通话了。因工作原因常跑中国,所以,她口语进步的速度也就老让我一惊一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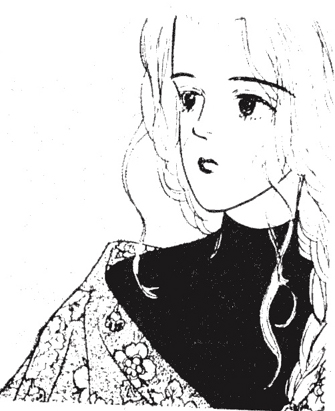
说是4个月,每周也不过才上一堂课,一般是在周末,一下班她准时来,进门先说“晚一上―好一”,自己就先笑。如果出差误了课,那她进门就会睁大眼睛歪歪脑袋笑眯眯地说:“好久不见啦,身体好吗?” 这些话我还真没记得教过她,也不知她从哪儿学来的,有时猛地蹦出一句,“喜欢茉莉茶、小笼包、旗袍”,吓我一跳。 那是一堂“指示代名词”的练习课,用“哪里”造句,她看了一下课本,然后轻轻唱起了中国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如果闭上眼睛不看人,你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刚学中文的、日本女孩唱得歌!字正腔圆,连我都唱不了。 她说每天上下班都在地铁里听邓丽君的CD。 中午,她经常给我发邮件,开篇总写∶“吃饭了吗?”。 我估计这时她饭已吃好,刷了牙(日本多数白领午饭后有刷牙的习惯),补了妆,而上班时间,还差那么一点点,便想起发邮件练中文。 这倒像是给自己开个小玩笑,那种感觉或许很轻巧。她每次发邮件的内容虽然不同,但不管写什么,都忘不了添上一句“吃饭了吗?”,这句话,我从来没教过她。真的没有!可她偏偏喜欢一用再用,她说这句话的发音好听也好学,比“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听起来亲切。 一次,她练习职业单词的发音,在几十个单词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项,一脸迷茫。 教师、医生、工人、农民、护士、司机、演员、歌手、律师、记者、秘书、警察、教授…… “我呢?” 你是服装设计师,我说。 她赶紧把我写下的这行字抄在自己的小本上。 她设计的时装,由她公司的老板带到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去加工,然后返销日本。公司不大,但每月的定单足以让那个公司的全体职员忙得人仰马翻。 那年,她第一次跟老板去广州,一下飞机便问:“长城在哪里啊?” 周围的中国人全笑了。 她说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难为情啊,“我真傻,玩笑开得也太大了,是吗?”。 她笑起来很好看。 睫毛长,眼睛圆。最近,她刚刚学会说“好看”。那天,她穿了件丝绸春装,淡紫,反光,莹亮,肩上绕了流苏披肩,一进门就问:“今天我好看吗?” 她很羡慕自己的老板,因为老板的中文已经讲得很地道了。“中国来电话,老板叽哩哇啦,说一大串,我要是能那样有多好啊!” 不过,我听她老板的中文里,有浓重的港台口音,“有没有搞错——!”模仿台湾人。 老板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沾沾自喜。他说幸亏他进中国进得早,要是当初不选择去中国发展,那公司根本到不了今天。 一次,我们开茶话会,都是一帮学中文的。百谷优加子和她老板带来一瓶意大利名牌葡萄酒和两袋日本式酒肴,我们吃饺子喝汤圆,中日文混用边说笑边吃喝。后来不知谁起头唱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一听,都兴奋起来,放声高歌,有板有眼。唱完老板来了情绪,说起中国的事情,滔滔不绝。他说中国人聪明、滑稽。 滑稽? 我说你指什么? 他说:“先说聪明。你看,中国人多么会翻译外来语:电脑――电力的电、大脑的脑,可不说了个正着!手机――手里的机器;入世、巴士、奥运、反恐、下载、因特网,还有好多好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滑稽是说,中国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做。很直接。比如我去中国,跟那边的同事一起吃晚饭,本来谈业务的人只有两个人,可是到了餐馆后才发现,整整坐满了两大桌!我的天!那些不相干的人都是来干什么的?再说,谁来付帐呢?” 学中文的人都点头笑了。说有同感。 大家还说起了中国的流行语。老板笑说,在日本学中文教我们说“出租车汽车”,太落后了!现在都说“打的”,去中国,谁还说出租车汽车啊! 一次, 白谷优加子神秘地告诉我∶我有男朋友啦!是个中国人,帅哥! “他会做饭,我喜欢会做饭的中国男人。” 白谷优加子告诉我,“当初刚认识他的时候,邮件往来,有时他回信不及时,我就用中文写∶吃饭了吗?他马上就回信了。” 这真是一种特殊的表达结成的特殊缘分。 白谷优加子与她的中国帅哥交往也有一段时间了。我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想了想,然后俏皮地说∶不知道。也许,什么时候他给我来信也主动写“吃饭了吗?”我们就要结婚了。 说完我们俩你看我、我看你,哈哈笑出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