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茉莉是湖南邵阳人,邵阳这个地方以民风彪悍著称,出土匪,也出豪侠之士,近代有讨伐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将军,当今有为民主宁死不回头的壮烈义士李旺阳。来自邵阳的女子茉莉也有刚烈豪侠,择善固执的性格,她不怕挑起争议,最爱打抱不平,常用笔为弱势者仗义执言,并自诩为”以批判为己任的作家” ,所以我称她是文字女侠。当然她所争所议的,我并非每件事都是赞同或完全赞同的。但她的批判精神,她敢爱敢恨的个性,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永远选择站在鸡蛋一边的精神,我一直深为佩服。正是因为茉莉这种追求社会公义错锄强扶弱的精神,她特别关注西藏问题,要站出来为受到压迫的藏民族说话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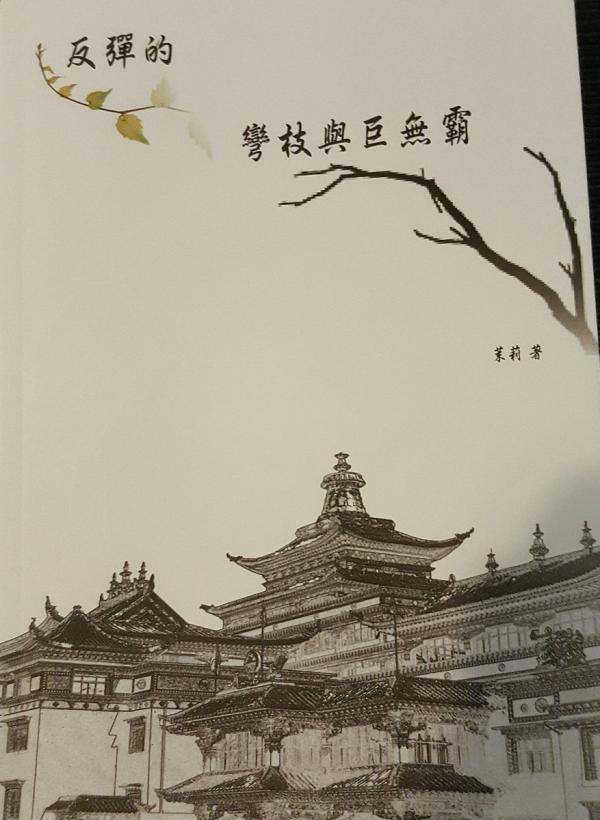
茉莉继第一本关注西藏问题的著作《山麓那边是西藏—一个中国流亡者的观察>後,她第二本关注西藏的新书《反弹的弯树枝与巨无霸》最近在台湾出版。这本书,我读来很亲切,因为其中好几篇文章就来自於《开放》杂,而我又是这家杂的编辑,文章早已拜读过。第二因为西藏是我和茉莉共同关注的话题,容易在我心中产生共鸣。 茉莉这本书用扳弯的树枝做出反弹来比喻藏民族在中共强权下的反抗。 我读过法国记者董尼德的书《西藏生与死》,这本书与茉莉的观点很相似。认为藏民族主义在上世纪的兴起与中共的统治有关。董尼德认为,在中共入藏之前,藏人的民族意识不是很强烈,更多是地区意识,但在遭受外敌入侵和占领,藏地本土文化和传统受到威胁後,产生了作为整个藏民族这个共同体的生与死的集体危机意识。在中国汉民族的压迫下,藏民族主义遂愤而崛起,也即是茉莉所说树枝被扳弯後的强烈反弹。因此对藏人的民族主义,茉莉是肯定的。她说,相对於中国富侵略性的大汉沙文主义,藏人新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和平的民族主义,没有对外扩张的进攻性,其追求只是本民族的自救。 茉莉这本书提到汉人视角中的西藏,是对西藏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的曲解,抹黑和误导,这个曲解、抹黑和误导很多是通过汉人对藏地的写作完成的,茉莉称这些汉人笔下的西藏作品是一种遮蔽真实西藏,具有“麻醉”作用的冒牌西藏文学。 我最初也是通过这些伪西藏文学来认识西藏,茉莉书中提到的一些汉人作品,五十年代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我中学时代读过,印象很深,後来是对西藏极尽抹黑之能事的电影《农奴》,以及本世纪初汉人女作家马丽华有关西藏的多部著作。马丽华在西藏长期生活,熟悉西藏,文笔又好,她对西藏风情和民俗的描述非常吸引人,我当年也是受到吸引者之一。但读多了,感觉她多少是以中原汉人猎奇的视角来观察异邦西藏文化风土和宗教传统,有作为汉人这样的世俗民族,对藏人这个注重精神生活的民族有难以沟通的隔膜,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她的西藏风情的散文如中国历史上的边塞诗一样,只不过是中华帝国边疆文学的延续,是用边境的荒凉美和奇风异俗来衬托帝国中原的繁华和文明,或满足中原人对边陲“落後”文化的优越感。茉莉还指出,马丽华的书最致命的要害是有意回避了西藏的现实痛苦,那些藏人宗教受到打压,传统文化被破坏,大量藏人流亡海外等等,这些西藏的真实,在她的书中连影子都没有。 对西藏和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的认识为何在中国大陆境内外有很大的反差?就是因为中共占领西藏之後日积月累的宣传洗脑的结果,上述伪西藏文学所起作用相当大。 我本人也认识一位冒牌的西藏诗人,我家邻居杨星火。她是1951年以征服者的姿态随解放军入藏的文工团员,後来还收养了一位藏人孤儿,专门写作一些藏地诗歌,五十年代传唱一时的那首所谓藏族歌曲《叫我们怎麽不歌唱》:辽阔的蓝天,雄鹰在飞翔,雪山下面有著无数的宝藏…就是她的作词。就在她歌颂美丽西藏的歌曲在中国传唱的时候,西藏人民正在遭受屠戮,美丽的藏地正在流血,但抒情的歌声把这一切血腥都掩盖了。我童年时,杨星火从西藏回家探亲,与邻居们闲聊拉萨的生活,大谈当地人如何愚昧和怪异之类,早熟的我挤在邻居伯伯和娘嬢之间听得很著迷,至今还记得一些细节,现在看来这些叙述是一种解放者的优越感。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殖民者姿态。 茉莉这本书对西藏问题的讨论很广泛,历史、政治、宗教、文学、生态等等皆有涉猎,对於想认识西藏、了解西藏的人读茉莉这本书会有很多启发。 比如读茉莉这本书,我才知道,中共占领西藏,竟然是出自斯大林的劝说。中共上台之前是把西藏当外国看的,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的观点,承认西藏的民族自决权。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还指西藏是外国。但为何後来中共的西藏政策竟然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茉莉说,原因就来自中共的老大哥苏联的冷战战略考虑。 茉莉引用中国大陆一位学者胡岩2006年发表在《西藏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的资料说: “从一九四九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议中共「不要过分大度」,不要让西藏独立从而在中共执政後缩小中国的领土。此後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九五○年元旦之後,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於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 这样,一个毫无自我防卫能力的高原佛国,在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成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讽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间的转变,是由於另一个更大的「外国」–苏联的指示,而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以及藏汉两族人民的愿望。” 仅就此来看,所谓西藏自古属於中国,完全是一个中共占领西藏後为了需要编造的神话。 我最近在读一位清乾隆时期供职於皇家天文台(钦天监)28年,任台长(监正)十馀年的欧洲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刘松龄( 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的有关资料,刘松龄写回欧洲的一封信介绍北京的政治社会生活,提到了属於理藩院交涉的外国之一“西藩”,这个西藩就是今天的西藏及其他喜马拉雅山国家如不丹、锡金等。刘松龄的信至少说明,在乾隆时代,西藏仍被中国视为外国。 其实有关西藏自古以来就不属於中国的史料甚多,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刘汉成业馀时间专门研究中国的有关西藏史料,收获颇丰,得出的结论都与中共所谓“西藏自古以来属於中国”恰恰相反。但在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中国,这类研究都是禁忌。 关於茉莉这本书的论述,我唯一觉得需要商榷的是茉莉提到中藏谈判可以回到已被中共废除的十七条的基础上,她认为值得一试,但我觉得毫无可能。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特徵是,革命目的一切,手段可以不择。对於中共来说,所有隆而重之的承诺或条约都是为达到某种终极目标的欺骗手段,从来就没有愿意遵守的打算,一旦目的达到,这个承诺或条约,就会被撕毁。比如中英两国有关香港97前途安排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最近中国外交部竟然宣称这个联合声明仅是一份历史文件而已,已经失效。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共与一西方大国签署的正式文件,都可以公然撕毁,何况是早已被中共撕毁的十七条。中共吞下去的,绝不会再吐出来,绝无可能让西藏回到十七条承诺的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时代。如果说西藏希望的是香港式的真正高度自治,但现在连香港的高度自治也已岌岌可危,这种希望岂不是过於脱离现实了吗?茉莉这篇文章写於2007年,十年过去,我想茉莉的看法很可能已有改变。 当然西藏的前景也不是绝对令人悲观。我完全同意茉莉这一论述:西藏不是一个孤岛,其命运是与整个中国的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寄托於中国的民主化前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