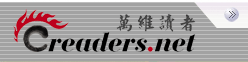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在他的书《侯宝林自传(上)》(1982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说相声有个口头语儿“是不是?”每说几句话,就问郭启儒:“是不是?”我自己没有感觉,郭启儒也没有感觉,但是张学礼感觉出来了。我每次演出,他老坐在第三排听,听着听着,就用胳膊肘捅捅旁边那人说:“你瞧,不又来了嘛?过两句还有哪!”“你瞧怎么样,又来了嘛?”后来,他索性接我的话茬儿,我说两句,他在台下就说“是不是啊?”我在台上听见了,才感觉到我这口头语不好,就改了。但后来又改说“怎么样?”的口头语,这个毛病,后来也没全改好。因为我说相声爱说即兴的词儿,我说着话,脑子里老想该组织个什么语言来反映个什么问题,于是就要说句口头语来填补空白,这个毛病就是观众发现的。这是观众培养我。 在这段话中,侯宝林先生提到了这么一个说法“说句口头语来填补空白”。这种在说话中用来填补空白的词语,在语言学中叫做“填充词”。英文叫做“space filler”。说话中的填充词现象,在语言学里也是一个研究对象。就连相声大师在说话时都难避免使用“填充词”,可见“填充词”的确是不大容易避免的东西。 据语言学家观察,几乎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特有的“填充词”。有些填充词是无意义的。比如有的人爱用“嗯 ——”。有的人爱用“是吧?”那个“是吧”中的“吧”往往说得很轻,上下唇一般都不需要碰一下,它跟“是”连在一起,形成的声音似乎介于“杀”和“刷”之间。 有些填充词,其本身是有意义的。比如有的人爱用“告诉你!”。说话时用这个填充词,弄不好会让对方有不太好的感觉,好像说话的人在教训人似的。或者说话者过于自信。 曾经有一个流行的填充词“那个”。有人说着话,嘴里就不断地出现“那个”、“那个”。现在在英语世界都有人知道中国人说话时会使用“那个”。与“那个”同时还流行着“这个”。分析起来,说“那个”,大概是说话者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在脑子的某个角落里,他潜意识里意识到了“那个”想法,于是嘴里就说出了“那个”。跟“那个”还同时流行着“这个”。 还有一个流行的填充词“那么”。“那么”本身是一个转折词。它提起的后文,一般是一个基于前文的结果。比如,“你连着忙了好几天了。那么,你就歇歇吧。”用“那么”做填充词,就难免让对方总以为说话者在连续地做结论。可是细听起来,每句话之间又不是“前提”和“结论”的关系。这就难免让听话人的思路受到一定的干扰。 还有就是“然后”。“然后”表达的是递进,其基本意思是“接下来”。“我在上海出生。然后,我小学是在大连上的。然后,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武术。然后我爸爸很不愿意我练武术。然后我说什么也放不下。然后我平时就偷偷练。……”听到第一个“然后”时,听话的人也许以为那个“然后”说的是他出生了“然后”到大连去上小学。虽然这个“然后”用得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的那个几个然后就更不大合理了。于是,听话的人就意识到了,他那些“然后”是填充词。 分析起来看,用然后做“填充词”时,说话者脑子里也许想到的是“然后我想告诉你,我小学是在大连上的”,“然后我想告诉你我爸爸不愿意我练武术”,“然后我想告诉你我说什么也放不下练武术”,等等。 使用“然后”做填充词,原因之一还可能是说话者的语文水平不甚好。他们把“然后”做“全能连接词”了。用上恰当一些的连接词的话,这段话就可以说成“我在上海出生,可是我小学是在大连上的。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武术。我爸爸很不愿意我练武术,可是我说什么也放不下。于是我平时就偷偷练。……”。这样就好多了。 有些电视节目有字幕。如果电视中那个说话者说话时用了填充词,字幕上不一定会出现那些填充词。这说明字幕制作者知道那些是填充词。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普通人正常说话时完全不用填充词一般是不可能的。但是,填充词如果用得好,说话效果不会受影响。至少不会让听话的人的思路跟着跑偏。有些情况下,甚至效果可能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