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是一名“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尽管在学术圈内人所共知,但与当下学院派之外自封并喧嚣为“公共知识分子”者相比,却沉静得很。这一方面与他低调的为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是历史学者有关。“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先贤的教诲是浸润到骨髓里的。
不过,眼望历史的天空,为的是对现实的关照,这也是历史学者大半会与思想界融汇的缘由。从1980年代跻身于启蒙思潮主流之中的青年思想先锋,到1990年代学界中广为人知的专家,王学典的学术历程较多地从微观层面上透露了八九十年代思想界嬗变的若干信息,这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可能颇具典型意义。
我这样说,并非在衡量王学典的学术造诣有多高——那是专家们的事情,我所感兴趣的是,他的学术研究与时代思潮同步共振的现象,这也是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人的特征——烛照现实,扎实深沉的学术考索中洋溢着浓郁的理论思辩风格。他的《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黎澍及其探索的问题》一书,在在体现了这种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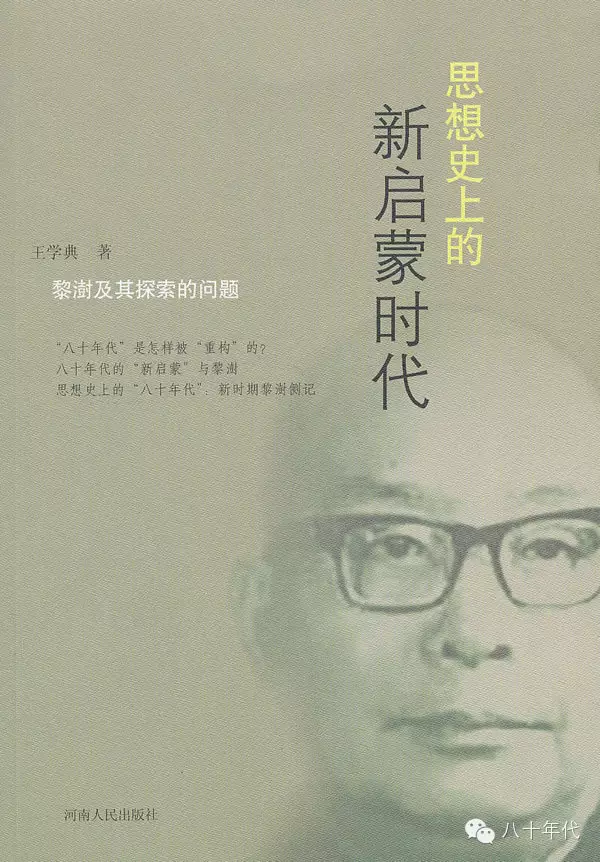
(王学典勾勒1980年代思想地图的专著。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1980年代的历史,距今不过30多年的距离,但“八十年代”这个固有名词象征着什么?却是那样的模糊;人们基本都同意,“八十年代”是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而“思想地图”却难以勾勒。这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一个年代像‘八十年代’那样纠结着如此丰富的内涵”。作为亲历者和参与者的王学典,对“八十年代”有着这样的描述:
这是一个过渡的年代;这是一个彷徨的年代;这是一个摇摆的年代;这是一个矛盾的年代;这是一个方向不明上下求索的年代;这是一个走一步退两步改革举步维艰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斥着激情、幻想、怀疑、狂热、偏激,甚至歇斯底里的年代;这是一个旧事物旧思想旧观念在挣扎在死亡,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在萌芽在生长的年代;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产生了英雄的时代,那么多的政治英雄、思想英雄、学术英雄叱咤风云;这是一个焦虑的年代,焦虑“文-革”悲剧重演、焦虑“异化”等;这是一个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拯救意识空前高涨的年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东林党人的对联是对这个年代学子的精神状态的最好写照;这是一个“文化热”持续升温席卷整个读书界的年代……
这是查尔斯·狄更斯式的语言——看过《双城记》的人,都能记得他开篇的句式:“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地狱。”
这样的时代所造就的历史,必定要打上“启蒙”的烙印。于是,在“五四”启蒙运动走过一个甲子后,历史轮回,1980年代新启蒙开场。
在“‘八十年代’正从‘现实’走入‘历史’”的今天,“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如何描绘这个年代的“思想地图”,逐渐成为成为当下学界的主要言说。
王学典认为,“八十年代”可以具体断分为三截:一截是从“文-革”结束到1983年10月的“清除精神污染”,持续了大约六七年的光景,这一时期的主题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反封建”。从1984年开始至1986年底,构成了“八十年代”的第二截,其主潮是以“反传统”为主题的“文化热”。从1987年春至1989年的春,构成“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截,这一截的主流思潮除继续“反传统”、“全盘西-化”外,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思想博弈重新浮出水面,并酿成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与上述时段划分相对应,在“八十年代”知识圈里活跃着三部分人:理论界、思想文化界与学术界。活跃在第一个时段的主要是以周扬、于光远、黎澍、王若水等为代表“党内理论家”,他们主宰了当时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清算“文-革”、反思党史、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反对“封建主义”、起用“异化”概念、主张“人道主义”、推动“理论务虚会议”的召开、参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和讨论等等,是这一批人在此期间的主要活动。1983年10月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使这一批“党内理论家”遭到迎头一击。

(从1980年代走来,学人的一大特征是激情四射,王学典这样眉毛斑白,也照旧)
此后,原本处于第二线的一些比较纯粹的学界中人则被推到了前沿,这就是以李泽厚、庞朴、王元化等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界”的崛起。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思辨天赋而领袖群伦,掀起了一股“文化热”。
与此同时,以“新三届”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崭露头角登台亮相。1986年底以后的“反自由化”等事件使“文化热”遭受重创,这反而激起了更强劲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潮流,“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倾向,几不可挡。以“狂人”和纪录片《河-殇》编创人员为代表的全体,最能反映这一时段社会思潮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指向;而以“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名义,汇集起来的著名的两大青年学者群体,则成为声势浩大的援军。
王学典之所以要勾勒“八十年代”思想地图,是针对现今对“八十年代”的误读。在他看来:“眼下许多人正在争夺‘八十年代’,一场‘八十年代’的书写竞赛似乎正在展开。而为人们忧虑的是,一些圈子和学界的人物,利用现在所拥有的话语权,以‘八十年代’当事人的身份所带来的优越感,正在合谋篡改‘八十年代’!这种‘篡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得到认可。”因此,他在勾勒八十年代的思想地图的同时,对学界内部可能会带来误导与遮蔽的观点与言论进行了批评:比如他认为甘阳在《古今中西之争》一书和访谈中,常常“偷换问题偷换概念”,将自己摆在了八十年代学界主将的位置上,有抢夺话语权之嫌;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名不副实,只是“主体缺席的80年代”言说,对当下读者的“80年代想象”容易产生比较严重的误导;许纪霖为《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一书撰写的“总论”,根据历史当事人的自我陈述、自我认定来叙述历史,并想方设法淡化、削弱和缩小以“狂人”为代表的“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又千方百计强调和突出甘阳、金观涛等人的地位,不自觉地用价值判断取代了事实判断,这种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叶的地位来安排“80年代”格局和座次的做法,有违历史主义原则,实为一种典型的“后设叙事”。
因为体现着“八十年代”学人的特征,王学典叙事以考证为索引,论述则以思辨为基本,全书所陈述的问题虽然涉及到人物黎澍、历史学界拨乱反正的历程,多头多面,却丝毫不游离“八十年代”的主题。而他充满激情的语言,在纸页上飘零和沉积,恰如屐齿印苍苔,成为“八十年代”激情的镜像——后“八十年代”的学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丝半缕的余晖,依稀照耀这那个逝去的令人追念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