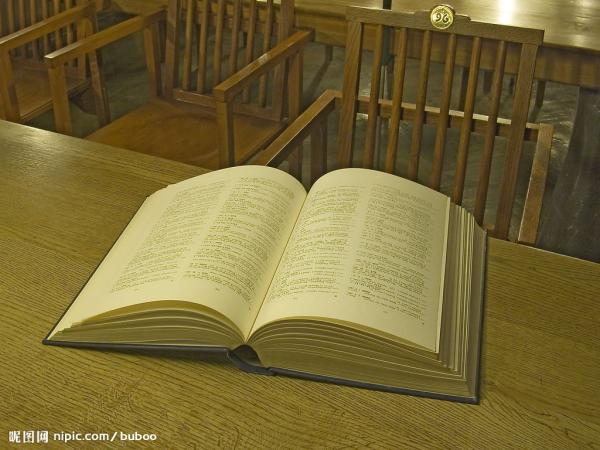
占座(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一) 浮云何轻狂,深埋日月光。 雁归多迷途,踌躇旅更长。 (二) 山高不见谷,来去皆彷徨。 客愁千里外,托梦到故乡。 序: 我们那一代人,人性是封在坛子里的酒,燃烧在胸腔里的火,苦乐自知。七情六欲就像当时小说中被方格子代替的文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禁欲的历史时期,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相对于时下的年青人而言,他们真可谓是封闭、盲从、无知和人性扭曲的一代人。 70年代末期,他们中的一些幸运儿挤进了文革后关闭了十年的大学校门。寂静多年的高等学府里,一下涌进来了千千万万个不同年龄段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入世深些的,自然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而那些从学校门到学校门的应届毕业生,充其量就是在大观园里糊里糊涂走了一遭的刘姥姥。那时候的人太单纯,尤其是后者,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带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理想,飞蛾扑火般的决绝奔向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了。 占座可以说是当年大学的一种校园文化,也是鸡肋一样的新鲜事物。占座可分为明占和暗占。所谓明占,即有的放矢地为那些已知的对象占座。而后者事先并没有预设的目标,是一个将偶然变成现实的故事。当时人们占座的手段可谓八仙过海,形式各异,林林总总。比如有人在桌子上放几本书,表明所属;有人则将座垫拴在座位上;更有甚者,有人干脆将书包锁在凳子的扶手上。。。。。。 起初,我颇觉不以为然,因为许多座位因被占而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些空着的座位,仿佛是人在饥饿时可望而不可及的蛋糕。我那时才16岁,少年气盛,做事从不计后果,凡事喜欢率性而为。面对有座不能坐的困扰,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找到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密谋”决定,在闭馆前的几分钟先躲进厕所,等没人后再对那些上了锁的书包进行一场“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其手段非常原始,即用刀割断所有拴在扶手上的带子,然后尽数掷于窗外。事后,我有些心虚,怕事情搞大会挨校方的处分。但几天过去了,竟然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一样。许是因为占座并非合理合法,所以那些丢失书包的人,只能自认倒霉。几个回合下来,锁书包的人少了许多。我们为这种恶作剧所产生的效果着实得意了一阵子,但想不到的是,占座现象竟流感般很快地死灰复燃了。就在我耿耿于怀,绞尽脑汁苦无良策时发生一件怪事,让我厌恶的情绪瞬间转化为一种莫名的甜蜜和温馨的感觉。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正当我经过一张被占的座位旁时,竟有人悄无声息地挪走了放在桌上的书包,我似心领神会,并有些受宠若惊地坐下。因为虚荣心,我根本没有认真看一下是谁给我让的座,只知道是个女生。记得当时我装模作样地拿出书,却一个字也读不进去。坐了40分钟,我装作满不在乎地离开了座位。虽然我们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的心中却充满了骄傲、满足和甜蜜。 事后,我默默地期许这样的事情能再次发生。我真是像中奖般地幸运,如此头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但让我遇上,而且美丽了大学余下的三年寂寞时光。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我愿意,就可以随时享受到同样的礼遇。许是为了面子,我只是在实在找不到空位子时,才肯接受她默默无闻的关照,我也乐于坐享其成。或是更深层的原因,即她当时并非我钟情的那类女生,起码当时注意的对象不是如她那样,在百花从中静悄悄开放着的一朵洁白的小花,所以我根本不在乎她的感受,她之苦乐。人就是这样,往往会忽视那些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等觉悟了却又为时已晚。她似乎从不介意我想来就来的随意,像母亲一样宽容我的“任性、无聊和无礼”。随着我降临的次数多了,她似乎也习惯了这种若即若离关系,便开始有了些表示。如,有时冲我浅浅地一笑,旋即就又将头重新埋在深深的发际中了。最多也不过就是微笑着默默地朝我颌首示好,仅此而已。直到大学毕业,我也始终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她是我同系同专业但不同届的校友。说好听点,我是她的师哥。那一年,我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学校,当然包括没有一次真正的恋爱,也包括与她在一起那么久竟连一句话都没说过。其实她的名字早已像刀刻过的一样印在了我的心上,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罢了。 许多年后我从加拿大回国度假时,突然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和这个曾经为我占座并让我骄傲和甜蜜了三年的女孩见一面。我千方百计地打听到她恰巧就在我就读的大学里教书。我欣喜若狂,第二天上午,就赶到计算机系去找她。不巧,她那天没有课,不在系里,我感到有些失望,却又不甘心。于是就问系里的其它老师,得到的回答却是后天下午再来看看。情急之下我只好告诉他我是从国外回来的,请他无论如何帮我联络她。那位老师犹豫再三,最终给了我她家里的电话。我看看时间已是下午,心想别太唐突,于是就耐着性子,等到了第二天,那一夜我失眠了。 第二天上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拨通那个被我攥得发皱且汗渍斑斑的小纸条上的电话号码,话筒里传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喂,你找哪位?” 我紧张得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ZYH吗?”我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自信。 “我就是,你是哪位?”声音一如印象中那般沉稳。 当我报过名字后,我真怕她想不起我是谁抑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像个机警的耗子,随时都准备放下电话而逃之夭夭,但她却迅疾地问道: “你现在在哪儿?你不是出国了吗?” “回来度假。”我顿了一下,然后鼓起勇气问道:“能见你一面吗?”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这句话出自我的口中,因为我从来没有主动邀请过女生。 “好啊!”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于是我们约好中午在某个餐馆里见面,因为我考虑那里离她家很近,不会让她感到不方便。说心里话,出国多年国内早已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却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盲,就这家餐馆,也是昨天路过时无意间发现的。 当我见到她时,感到十分诧异。除了身体略微比从前胖了一点儿,模样几乎与在校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更加成熟和有魅力了。我们简单谈了些离开学校以后的事情后,话题就转向如何移民加拿大和移民以后的生活,看得出当时她对移民的事情很感兴趣。 次日她在一个温馨舒适的茶馆里回请了我,让我切实体验一下当时在国内方兴未艾的茶文化氛围。我们原本就不是很熟悉,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陌生,但我们相识就有一种默契,因此即便各自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彼此之间还是倍感亲切。像多年未见的老友,但又有一种陌生和暧昧在里面。这种关系有点像在焖在锅里的米饭,需要时间和温度去成就它,但这些在当时我们都不具备,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只能像一锅夹生的米饭。 以后由于忙碌,回加拿大前我们没有再见过面。更不幸的是,我不小心将电话本弄丢了,其中就包括她的信息。两年以后我移民去了美国,从此天各一方音讯皆无。后来我听说她也移民到了加拿大,但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
真的希望她能过得比我好,而我在有生之年也能为她占一次座。 浮云多轻狂,淹没日月光。归雁可迷途,踌躇旅更长。 山高不见谷,来去皆彷徨。客愁千里外,托梦到故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