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死了,中国人比美国人伤心。为什么呢?据说因为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死了,无处去问。但“中国人民”是基辛格的“老朋友”,却因基辛格的去世,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官方的唁电,到网民的悲悼,几乎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所以,说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倒不如说“中国人民是基辛格的老朋友”,来得靠谱。 就算基辛格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也是位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朋友。中国人民过去半个世纪来,最波澜壮阔的事业,莫过于“改革开放”。和中国“改革开放”有关的外国人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别的不论,光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起码一半以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过力。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左到右,都曾排着队去中国出谋划策。但有谁听说过基辛格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过什么?基辛格是谋略家,擅长纵横捭阖,和“改革开放”不沾边。要等到中国出事情,如北京开枪杀人时,基辛格才会现身,奔走游说于朝野上下,纵横捭阖在中美之间。也就是说,中国人民的好事都和基辛格无关,只有坏事才和他有关。所以,基辛格就算是老朋友,也是位时隐时现的朋友,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 当然,也有人说,基辛格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是被中国政府收买,替中国做“大外宣”的。这回“中国人民”阔气,做上了基辛格的老板。但这种说法,有点太小看基辛格。基辛格虽然生不逢辰,没赶上春秋战国,也没赶上欧洲“维也纳会议”的年代,但终究是位谋略家,什么世面没见过?凭基辛格的资历,哪能随随便便为五斗米折腰?在基辛格的行业里,他属于“现实主义”流派。但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中国语境中的“现实主义”不太一样。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总有点“机会主义”的意思,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江泽民执政以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更野蛮演变,变成了赤裸裸的“有奶便是娘”、“闷声大发财”,一切向钱看的“捞钱主义”。所以,中国人比较容易相信,基辛格“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为咱们打工。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讲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其理论根源,是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 H. Carr)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人创立的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不同,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状态,而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在一国之内,张三打了李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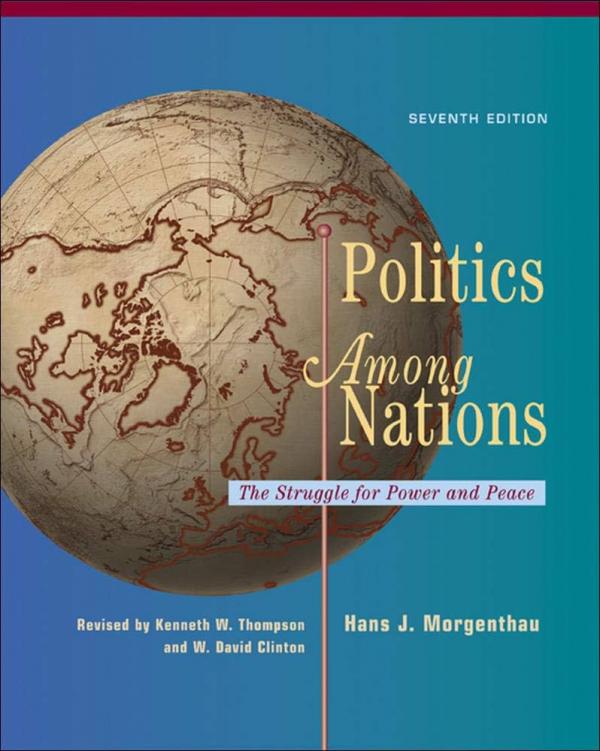 警察会管。在国际社会里,A国打了B国,没有世界警察来管。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同样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弱肉强食。所以,在国际政治里,没有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个国家都只能拼命增强实力,以求自保。现实主义学派后来经过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人的发展,变成了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强调体系和结构的作用。有什么样的结构,比如两极世界、多极世界等等,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行为。就像天体运动由万有引力决定一样,国家行为或外交政策,是由国际关系的结构决定,和政治领导人的主观意愿无关。 警察会管。在国际社会里,A国打了B国,没有世界警察来管。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同样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弱肉强食。所以,在国际政治里,没有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个国家都只能拼命增强实力,以求自保。现实主义学派后来经过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人的发展,变成了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强调体系和结构的作用。有什么样的结构,比如两极世界、多极世界等等,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行为。就像天体运动由万有引力决定一样,国家行为或外交政策,是由国际关系的结构决定,和政治领导人的主观意愿无关。
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现实主义,都把一个一个的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而忽视国家内部的情况。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内部的情况无关重要。在一定的国际关系结构下,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有相同的行为模式。所以,他们不重视人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重视均势、地缘政治和国家实力。所谓国家实力,在他们眼里主要是军事实力,以前是看谁的坦克大炮多,后来则看谁的核武器导弹多。所以,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的所作所为,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偏爱,也不是要到中国捞钱,而是出于自己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信仰。 但现实主义也有现实主义的问题。例如,前苏联有那么多的导弹核武器,在基辛格们的现实主义看来,无疑是庞然大物。但这么个庞然大物,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了呢?面对这样的问题,现实主义显得相当苍白,有点难圆其说。苏联刚解体那会,有位基辛格的知音,同样信奉现实主义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赶紧出来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我们即将怀念冷战”(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意思是苏联一解体,好端端一个两极世界瓦解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以后天下大乱,你们就要“怀念冷战”了【注1】。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世界人民,包括同样是基辛格知音的“中国人民”在内,好像没人“怀念冷战”。米尔斯海默后来又写了本题为《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的书,从头到尾没有新东西,都是些现实主义教条的重复。一如以往地数坦克大炮,一如以往地数导弹核武器。甚至至今认为,陆军是最重要的军种,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等等【注2】。写了洋洋数百页,不忍卒读。世界上任何主义,往往创立者是天才,追随者则每况愈下。例如,马克思是天才,马克思主义者却往往是庸才。现实主义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卡尔和摩根索相当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辛格重在行动,最多算列宁斯大林。到了米尔斯海默,水平相当于中央党校的老师。 基辛格及米尔斯海默们,眼睛盯着坦克大炮看,看久了难免眼花。例如他们数中国和俄国的坦克大炮,数着数着,心生敬意。以为这两个国家,坦克大炮那么多,必须高看一眼。所以,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他们便大惊失色,以为要出事情。一年前,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他们一方面忧心忡忡,一方面又难掩得意:“看,我们怎么说来着,大事不好了吧”?没想到普京打了一年,非但没把乌克兰干掉,自己反倒差点被干趴下。这次,不知道基辛格及米尔斯海默们怎么说,不会是“我们即将怀念俄乌战争以前的岁月”吧? 所以,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种种言论,主要是他数坦克大炮,数导弹核武器数出来的。因此而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点自作多情。面对不算“老朋友”的俄国,他会说同样的话。有人可能不服气,说基辛格还是和咱们交情深,你看他来中国访问一百多次。临死前几个月,还不远万里来中国开场生日派对。他和俄国没这交情吧?是,基辛格是没去俄国一百多次。但那不是他不去,而是俄国没人请他去。除了中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热衷于邀请基辛格去访问。作 为一个迷信“权力就是春药”的人,基辛格离不开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中国的邀请,对基辛格来说,是历史舞台上的回光返照。所以,对中国抛来的邀请,基辛格来者不拒。连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基辛格都会赶去捧场。可见,离开了历史舞台,又不甘寂寞的基辛格,对重新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机会,多么饥不择食。 为一个迷信“权力就是春药”的人,基辛格离不开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中国的邀请,对基辛格来说,是历史舞台上的回光返照。所以,对中国抛来的邀请,基辛格来者不拒。连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基辛格都会赶去捧场。可见,离开了历史舞台,又不甘寂寞的基辛格,对重新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机会,多么饥不择食。
“中国人民”最喜欢的美国政治人物,第一要数尼克松,第二就是基辛格了。但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整个西方世界里,并不怎么受欢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美国人民赶下了台。当年的毛主席,和“中国人民”一样,对这事很不理解。心想就这么点事,至于把皇帝打倒吗?毛主席讲义气,听说尼克松下台,就派架专机,把尼克松接到北京,好言安抚,惺惺相惜一番。毛主席心里的算盘是,你都下台了,我还把你奉若上宾,够患难见真情吧?毛主席的算盘打得天衣无缝,几乎是中国式现实主义的顶峰。但毛主席没想到的是,他和“中国人民”一样,对外部世界不甚了了。他的那点算盘,是和蒋委员长争天下时积累下来的,用在尼克松身上,牛头不对马嘴,根本不对路。尼克松不是西哈努克,不需要北京庇护,他能对你感激涕零? “中国人民”喜欢尼克松,爱屋及乌,自然也就喜欢上了尼克松的宰相基辛格。但问题是,“中国人民”喜欢基辛格,基辛格喜欢“中国人民”吗?基辛格多半并不喜欢“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基辛格远比不上任何一位美国的汉学家,甚至比不上许多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的汉学家。基辛格非但看不上“中国人民”,他连自己的老板尼克松,也未见得看得上。基辛格看得上的,是十九世纪欧洲维也纳会议的灵魂人物,奥地利帝国的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在马克思看来,像梅特涅那样的人,无疑是全世界最反动的人物。在《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指出梅特涅是旧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但基辛格最崇拜的人物,恰恰是梅特涅【注3】。基辛格人生在20世纪,心却留在19世纪,痴迷于维也纳会议里的外交氛围。因为在那里,几位亲王贵族在沙龙坐定,一番纵横捭阖,便能搞定全欧洲的地缘政治。基辛格喜欢这种氛围:神秘、狡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在自己的外交生涯中,基辛格也经常故弄玄虚,搞得好像自己是梅特涅再世。一分钟前,公然让肚皮舞娘坐在大腿上撒娇;一分钟后,神秘飞往某国,展开战略核武会谈。这是基辛格的高光时刻,集权势、神秘、美女于一身,充分实现了自己对“权力就是春药”的期盼。 所谓“权力就是春药”,也是基辛格从梅特涅那里学来的。梅特涅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外交界,以风流倜谠闻名。为了看上去更像梅特涅,基辛格亦步亦趋。梅特涅风流倜谠,基辛格便倜谠风流。别人有绯闻,都是遮遮掩掩。基辛格有绯闻,恨不得满世界都知道。所以,基辛格的风流韵事,被炒得满城风雨,从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一直传进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 毛主席多年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哲学家,不知道谁向他报告,说基辛格是“哲学博士”。“中国人民”那时比较闭塞,不知道所谓的“哲学博士”,即PhD,在西方大学里,是可以通用于任何专业的。基辛格获得PhD,并不说明他学的是哲学。但毛主席不管,一口咬定基辛格是“哲学博士”。毛主席这人有个特点,对别人的学历比较敏感。一听基辛格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非要在会见尼克松的第一天,当着基辛格的面,不谈政治,只谈哲学。毛主席大概以为哲学是自己的强项,所以想从“实力地位”出发(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注4】,给尼克松、基辛格一个下马威。但没想到,当毛主席、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四人,在毛主席的书房落座后,谈的竟不是哲学,而是基辛格的风流韵事。四个男人围成一堆谈女人,不知在场给他们当翻译的唐闻生小姐,内心是什么感受? 基辛格告诉毛主席,他搞女人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外交工作。后来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Fallaci)采访时,基辛格讲得更露骨。说自己搞女人只是消遣(diversion),是一种业余爱好(hobby)【注5】。法拉奇是世界级名记者,素以采访政治领袖著称。当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念书时,她是我们那一代新闻系学生心中的偶像。法拉奇独家采访过的领导人,包括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巴列维、英迪拉·甘地、阮文绍、邓小平、基辛格等等。法拉奇的采访不是一般的我问你答,而是言辞泼辣,唇枪舌战。读她的采访,可以读得热血沸腾,感到提问比回答更精彩。其中,她对霍梅尼的采访,堪称经典。伊朗革命后,霍梅尼是伊朗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享有神一般的地位。她去采访霍梅尼时,被迫穿上伊斯兰妇女的黑色长袍。她问霍梅尼,为什么要强迫妇女穿长袍。霍梅尼反唇相讥,说这种长袍专为淑女而设,西方女人不喜欢可以不穿。她当即回答霍梅尼:“您真好心,教长。既然您这么说,我现在就扔掉这愚蠢的中世纪破烂货”!【注6】回答得果断、勇敢、掷地有声、酣畅淋漓。她当着霍梅尼的面脱去长袍,若无其事地继续采访。逻辑严明,步步紧逼。整篇采访,犹如战斗檄文,可以看作是伊朗革命后,西方文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漂亮的反击。但在法拉奇采访过的所有人中,最令她讨厌的人物,既不是霍梅尼,也不是卡扎菲,而是基辛格。 在法拉奇看来,基辛格虚伪、傲慢、冷酷、狡诈。她讨厌基辛格谈话的内容,也讨厌基辛格谈话的语调,她一度甚至称基辛格为“小丑”。共产党最喜欢骂别人“反动派”,但无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法拉奇那样的自由主义者,都视基辛格为全世界大最大的反动派(reactionary)。就这么一个反动派,竟几十年如一日地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不是很滑稽?其实,基辛格和“中国人民”,谁也不是谁的老朋友。基辛格和“中国人民”,不过因缘际会,一个秉承西方的现实主义,一个秉承中国的现实主义,一个数坦克大炮,一个“有奶便是娘”,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就这样,两个相反的极端,终于走到了一起。
注释: 【1】Mearsheimer, John J.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in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90. 【2】Mearsheimer, John J.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p 55-82. 【3】参看基辛格的博士论文,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4】中美安克拉奇会谈创造了两句名言:一句是布林肯说的“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中方理解为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谈判。但也有人说“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只是要从对自己有利的地位出发,即扬长避短的意思。另一句是杨洁篪说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杨洁篪是上海人,讲出来的话,充满上海的市井气。 【5】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采访,见https://scrapsfromtheloft.com/history/oriana-fallaci-henry-kissinger-interview/ 【6】纽约时报1979年10月7日刊载的法拉奇对霍梅尼的采访,见https://www.nytimes.com/1979/10/07/archives/an-interview-with-khomeini.html (2023年12月16日) 陈翰圣
原载《新世纪》网站: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12/blog-post_21.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