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亲历: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之二)资中筠 著名学者资中筠的最新自选集《夕照漫笔》,今年由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壹嘉出版推出。这是继2011年《资中筠自选集》、2013年《老生常谈》之后,资先生的又一个自选集,收入其2013-2022年间尚未入集的文章,以及讲座整理稿、访谈记录。年逾九旬的资先生依然思维敏锐,笔耕不辍。《夕照漫笔》共两卷,包括文化教育、公益与社会改良、历史与救国、世界观察、思故人、音乐家园、闲情与杂感和访谈录八个小辑,涉及学术思考、公共话题、私人生活等各个方面。 "难求于世有济,但行此心所安"。资先生修改曾国藩名联以自况。不阿世,不迎俗,倡导中国读书人摆脱"帝师"情结......洋洋五十万言,所思所虑,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本乡本土"。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祖籍湖南耒阳,1930年生于上海,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1951年毕业后,多年从事对外关系工作。1980年代早期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后,著述尤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本书的印刷版和电子版已在amazon, Barnes & Nobel, Kobo 等各大网上书店上市,各国朋友可点击进入相应地区的亚马逊购书网址:
美国亚马逊 加拿大亚马逊 英国亚马逊 日本亚马逊 德国亚马逊 法国亚马逊 西班牙亚马逊 意大利亚马逊 澳大利亚亚马逊 印度亚马逊 巴西亚马逊 荷兰亚马逊 如果您所在地区目前只能预购(并非出版社的计划,而是亚马逊的问题),请您选择预购,这样能促使亚马逊尽快将书变为“现货”。多谢您的支持! 因为审查,资先生新书的消息在微信上被全面屏蔽,无法利用这个中文世界中最有效的传播媒介。因此我们也希望借此各位读者朋友的力量,请您手动帮忙,通过其他途径,将这条书讯转给所有可能会有兴趣的朋友。诚挚地感谢您!

1958年7月斯德哥尔摩“裁军与国际合作大会”,与赫尔辛基大会相隔三年,气氛就没有那么和谐了。大会的主题是中东局势:前一年中东战争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1958年伊拉克出现左派政权,卡塞姆在共产党支持下上台,黎巴嫩局势动荡,中东局势有向对苏联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可能。美国遂派军队干涉黎巴嫩,英国也派军队进驻约旦。因此在中东问题上,中苏立场基本一致。这样,在这次大会上没有出现分歧。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中东局势的告世界各国人民书”,以及要求禁止核试验和裁军的呼吁书等。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中苏还能表面上勉强维持一致的大会。
那次大会还有一个南斯拉夫代表的问题。当时中国“反修”以南斯拉夫为主要靶子,在一切国际场合予以抵制。此次南代表出现在会上,中国驻维也纳书记郑森禹因未能事先制止而受到国内来的领导批评,这实在是很冤枉的,因为此事苏联不会先与中方通气,即使知道了也无力制止。记得郑森禹曾对廖承志公表示为了顾全大局,不在代表团内公开辩解,但是对批评不能接受。会上,南斯拉夫代表受到中国代表的迎头痛批。 国际方面,匈牙利事件虽然中苏保持一致,却是“和运”内部实质性分歧的焦点。西方人士,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普遍对处死纳吉想不通。原来英国哲学家罗素是大会支持委员会成员,本已决定参会,因匈牙利处决纳吉,致函“世和”总书记维尼耶,宣布退出大会支持委员会,并撤销对“世和”的支持,因为它只谴责西方国家,不谴责共产党国家,要求斯德哥尔摩大会通过决议谴责处死纳吉是背信弃义,否则不能认为“世和”是公正的组织。 中苏主要分歧问题: 在和运中中苏主要分歧问题如下: ——争取和平与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的侧重点:苏方强调前者,中方强调后者; ——和平力量主要依靠对象:苏方重视西方和平力量包括和平主义者;中方重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包括武装斗争力量;当时在欧美国家中反对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的舆论高涨,出现各种组织,苏联基本上把它们作为应该团结争取的力量,因而在文件决议中考虑这部分人的接受限度,中国认为不能为迁就他们而降低反帝调门。 ——反对核武器和争取裁军:苏联强调核武器本身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强调核战争无赢家,强调放射物污染大气层,反对地上核试验;中国反对渲染“核恐怖”,强调反对民族压迫,认为没有核战争,被压迫人民也正在天天死亡;关于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销毁一切现存武器,不能只禁止地上核试验;关于裁军,中国反对笼统谈裁军,应重点要求“武装到牙齿”的美国裁军,被压迫民族不但不能裁军还应加强武装; ——苏联强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强调高举反对美帝旗帜,甚至认为苏联与美国“缓和”不利于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国坚持要点明战争根源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归根结底,这些分歧都反映出当时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和路线的论战。后来毛泽东在国内以王稼祥为对象,批判“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到“文革”中升级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修正主义路线”。从实质上讲,苏联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对内否定斯大林,实行“解冻”,对外争取与美国“缓和”,这些都与毛泽东在国内一浪高一浪的阶级斗争和在国际上坚决反美,支持世界革命的取向背道而驰。 1959年在莫斯科和斯德哥尔摩分别开了两次会议。中苏表面上勉强求同存异。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在回答苏丹代表的问题中肯定了民族独立运动也是和平力量,当时亚非代表颇受鼓舞,但是赫鲁晓夫的表态并不能消除中苏在这个问题上的实际分歧,以后日益尖锐化直至公开对立。 争论激化到公开反目中国十周年国庆 1959年十周年国庆是一件大事,“世和”代表团应邀参加观礼,并访问各地。代表团规格很高,以主席贝尔纳为首(贝尔纳是英国物理学家,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去世后接任主席),成员包括苏联吉洪诺夫等五位各国籍的副主席。国内接待规格也很高。 “世和”代表团本来是来“祝寿”的,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免不了有一场争论:从外地回京后,贝尔纳与郭、廖、刘有一次严肃的谈话,由我做翻译。争论的题目主要是“世和”内部分歧。贝指责中方不合作,双方都说和运要跟上形势发展。不过贝指的是在西方国家应扩大团结面,改变“和运”是共产党把持的形象;中方则指的是要跟上蓬勃发展的民族独立斗争的形势,批评“世和”支持不够,不承认它们是重要的和平力量。另外还有对反核武器运动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加拿大文幼章在代表团离去后单独留了较长时间,到10月底与廖承志还有一次长谈。当时文幼章的处境比较为难,他和中共的渊源很深,从抗战在四川时就支持学生运动,在中共内有许多朋友,但是他在“世和”得听苏联的,而且他本人的观点也比较接近苏联和西欧代表。他曾表示,中国朋友把他看成不友好,使他很伤心。 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变化的根源就是苏联对中印边界分歧偏向印度的立场、赫鲁晓夫访华的讲话以及与毛泽东关于“联合舰队”等问题的谈话,此事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不必赘言。中苏关系骤冷,反映在“世和”,就是中国无限期推迟派人去维也纳书记处,苏方来催问则不置可否,也不说一定不去。这样拖到1965年底,忽然上面决定,这个阵地还是要占领的,至少可以是一个触角,了解一些外面的情况。于是又派了李寿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为书记,和一名中层干部,英、法文翻译各一名,共四人到维也纳。他们只呆了不到一年,文革开始后,于1966年下半年陆续调回,从此与“世和”基本断绝关系。 中国代表团公开退场和“死尸运动”之由来 1961年12月,世和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在正式会议之外有一场亚非拉代表的非正式集会。苏联代表,也是当时的苏联常驻书记切克瓦采,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有人指责苏联不反帝,辩解说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接着讲了一段话,大意为:和运与民族独立运动不可分,裁军有助于民族独立,因为帝国主义就是凭武力统治人民。战争是可怕的,如果发生核战争,引起亿万人死亡,这样还有谁的民族独立?只有亿万死尸!不希望是死尸的民族独立。话音刚落,中国代表团在廖承志带领下全体起身扔下耳机,大踏步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以后的小组会议上剑拔弩张,朱子奇与苏联代表几乎发生肢体冲突。最后通过决议时,中国代表投反对票后退场。与中国人采取共同行动的有几内亚和日本代表。 与此有关,我还干了一件傻事:那次会议我在翻译箱内做同声传译。苏联代表这段话是我译出的(从法文转译),我觉得把他的话说成是污蔑民族独立运动为“死尸运动”似乎有失原意,害怕我的翻译造成误解。出于职业的责任心,会后专门找到廖、刘二位领导重复一遍那段话的全文,说明前面有一段推理,怕我译得不完整,或他们没有听清楚。结果廖像哄小孩一样向我扮了一个鬼脸,刘挥挥手,意思不必啰嗦了。这使我感到自己完全是书生气十足,而且十分幼稚。问题绝不在于这段话原意的逻辑如何,而是当时“斗”的方针已定,就是要抓个由头做文章。从此,中共给苏共扣上“污蔑民族独立运动为‘死尸运动’”的帽子,而且后来写入《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的《五评》中,载入了史册。 为反对而反对 在此之前,虽然争论不断,有时为决议中的几个字争到半夜,但最后还是基本上一致通过。从那次起,中国开始投反对票。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不能表现出一致。有的决议措辞其实与中国立场并无不同,但为了不让它一致通过,努力提高反帝调门。有时就是争一项决议里出现几次“美帝”字样,现在看来有点像小孩子吵架。当时双方却都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在日本开会,起草小组为一项决议中的“美帝”字样,争了一个通宵。别国代表都撑不住了,只剩下中、苏两家。欧洲工作人员(文秘、翻译等)都不奉陪,早已回去睡觉了。只有中国、苏联和日本的工作人员在坚持。中、苏是当然的,领导不休息,焉能擅离岗位。日本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给我以深刻印象,不仅表现在陪我们开通宵上,而是在各个方面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与欧洲人(尽管是共产党员)的维护休息权成对比。中苏代表对文件措辞锱铢必较,主要不是真的认为那些话语有多大作用,而是为的向国内交账——如果文件口径不符合各自“中央”指示,代表回去就要挨批评。这里,中国比苏联主动些,因为不合己意可以投反对票,而苏联则必须保证其意图得到贯彻。所以有个别情况下苏方对局面失控,会上以多数通过违背莫斯科旨意的决议,他们竟在其所控制的文印处偷换文稿,使大会最后正式印发供公开发表的文本与大家举手通过的不符。以至于有几次会,决议通过后,我们还曾奉命到文印打字室去“志愿帮助”校对文本,保证其不被篡改。越到后来,中方越不重视“世和”,似乎只求其“不做坏事”,而不求其发挥积极作用;而苏联还是很重视,所以会议决议常常在《真理报》上全文发表。有的决议未能按苏方意图通过,在《真理报》上关键处还是改成苏联的原稿。可见其主要作用是对内宣传。 1962-1965年之间中苏关系可以说是波浪式地恶化,在这期间“世和”又举行过多次会议。中苏关系当时的状况反映到会议上,时而和缓,时而激化。中苏代表在会外有多次会谈,各自陈述立场,都指责对方破坏团结。此时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成为历次会议中心议题,越南代表(包括南、北越)在会上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每次越南代表发言都全场倾听,有时还起立鼓掌。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最少,西方和平主义者也都反对美国侵越战争。中苏两家都要争取越南“小兄弟”,而后者其实只关心自己的事,拿到满意的决议就满足了。“两大之间难为小”,对中苏分歧,他们只求息事宁人。实际上在国际共运内,胡志明就是扮演和事佬的角色。 批判“三和一少”路线 1962年莫斯科“普遍裁军与和平世界大会”又是一次转折。在此之前,5月间在瑞典举行筹备会,到那时为止,中苏之间似乎还有妥协的期望,所以才派郑森禹与杨朔参加。会外考涅楚克与郑、杨有一次长谈。我担任翻译兼记录(中介语言为法文)。那次谈话双方都坦率地摆出了分歧,不过气氛还比较缓和,表示了团结的愿望。到7月在莫斯科开会,中方代表团明显人数比往常减少,规格也降低,郭、廖、刘都没有去,团长是茅盾,实际负责人是王力(即后来在文革中有名的“王、关、戚”之一)和区棠亮,他们两人分别是中联部某局的局长。另外还有金仲华、朱子奇等。茅盾的发言稿是王力写的,在会上照念而已。此次中国代表团虽然与苏联有争论,表明了态度,但是没有投反对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态度最激烈,投了反对票。照例,代表团出国以前,参会方针一定是上面批准的,发言调子也是在国内基本定的。不料代表团一回国,就遭到了批评:对苏联太软,斗争不力,还不如“小兄弟”(即阿尔巴尼亚,好像他们已向中方告了状)。紧接着开过几次总结会,王力、区棠亮做检讨(茅盾名义上是团长,但大家都知道他不负政治责任)。他们似乎没有心理准备,感到委屈,区棠亮曾几度要辩解,被刘宁一制止。我还听一位“和大”的领导说,毛主席说:什么“和平共处”?就是“和平地”消灭帝国主义! 后来我逐渐明白,那正好与毛又一次发动的政治斗争有关。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提出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方针以恢复元气。据此,王稼祥作为中联部部长、书记处书记,与伍修权等部分党委成员于2月份向中央提出对外工作的建议书,主要精神是:为有利于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不要四面树敌,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中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就是以后被称为“三和一少”的路线。此信写给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并未遭到反驳。参加莫斯科大会代表团的政治负责人王力和区棠亮就是秉承这一精神行事的。而同为中联部领导的康生是主张“三斗一多”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一直在酝酿反击,从1962年中开始发动批判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风”,如“黑暗风”(对经济局势估计太悲观)、“单干风”(三自一包)、“投降风”(对民主党派),等等,在国际上就把王稼祥提出的主张概括为“三和一少”(“三”指“帝、修、反”,“一”指民族独立运动),而赞成“三斗一多”。从此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弦日益绷紧,提出“天天讲,月月讲……”,对外则发表“八评”、“九评”,与苏共以及其他欧洲共产党展开公开争论。反映到和平运动,如果中国还派代表参加会议的话,那就是为了利用其讲坛宣传自己的主张,揭露“修正主义”,争取第三世界的群众。当时亚非国家一些代表,特别是非洲未独立国家的民族运动人士,出席会议的经费只能依靠中国或苏联的援助,甚至他们在国内进行斗争的经费也是如此。在中苏对立的情况下,他们依违于两大之间,或两头为难,或两头得利。私下都表示感谢和支持中国“兄弟”高举民族独立大旗的立场,在会上表决时又举手支持苏联提出的决议。有人还向中方打招呼,说是需要苏联援助,是不得已的。一位中国代表曾叹气说:“和运的门儿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财力当然比不过苏联。与此同时,中国逐步把重点放在“亚非团结运动”,直到“文革”开始以后完全退出此类国际活动。 撇开国际干革命 大约在1966年文革初期,传达过一个毛泽东讲话(在什么场合的讲话,完全忘了),与他否定17年各个领域的成绩一样,完全否定过去这些国际会议,说是“完全没用”,“通过好的决议和坏的决议都没有用”。我当时听了挺伤心,十几年为之焚膏继晷都白干了。再一想,毛说的也没错,这些堆积如山的决议案的确是毫无用处,争得不可开交的一个词、一句话,谁还记得?想起来都觉得可笑。不过多年以后,在从事国际政治研究中想起这段经历,觉得对我个人也不算完全浪费——提供了一个“见世面”的机会。有些事当时不理解,待有了新的认识之后,却提供了赖以思考的难得的独家史料,也是一种收获。我体会那时毛对国际问题的主要思想是支持世界革命,强调武装斗争,已经对什么和平谈判、和平会议等等不耐烦了。还提出要成立“革命的联合国”之说。就是完全把现有的由“帝、修、反把持”的联合国撇在一边,由革命力量组成自己的联合国与之对抗。所谓“革命力量”包括:响应中国“反修”而从各国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左派、新成立的认同毛泽东思想的小党派、亚非拉亲中共的民族解放组织,和少数已经独立的亲华的第三世界国家。在那前后,我还听过一次康生在中联部讲话的传达,说当时与中联部有联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亦即所谓“毛派”)已经有52个云。不言而喻,这个“革命联合国”如果组成,当然是以中共为核心。不过此说我只听到过一次,以后未见再提起。事实上,那些小组织很少有成气候的。 后记:美国方面的反应我在写这篇回忆时,偶然在网上发现一份1950年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针对这一“和平运动”的长篇报告,引起我强烈的兴趣。原来我们后来自己都认为“没有用”的这个“和平运动”,美国政府却曾给予如此的重视和关注,称它为“对美国有严重威胁的苏联一项战略性的阴谋”!今天在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中国已经全方位开放的形势下,回顾当年“两大阵营”之间那种敌对、封闭和互相猜疑的程度,别是一番滋味,感到双方的思维方式其实非常相似,都把对方视为假想敌,夸大其威胁,国家之间的猜忌祸延本国平民。时过境迁,国际格局虽然有很大变化,而这种思维方式似乎很难有根本转变。 美国国会的那份《报告》篇幅极长,印出来近三百页,从内容看,美国政府确曾花费许多人力、物力对“和运”进行追踪调查,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其行文带有美国特有的繁琐作风。题目本身画龙点睛: “关于共产党‘和平’攻势——一场旨在解除美国武装并击败美国的运动——的报告”。这就是美国为“和运”的定性。《报告》的日期是1951年4月,所以不包括此后的情况,也就是还处于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的时期。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这种看法大约保持到 1956年左右,赫鲁晓夫上台,美苏关系缓和,而此时中苏分歧也逐步公开了。 这种对骂是否起到了瓦解对方民意和士气的作用呢?我看未必,也许效果适得其反。外敌(无论是真的还是假想的)攻击适足以促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甚至有助于执政者赖以巩固政权。如果一国统治者不能像原来那样统治下去——例如苏联的解体——绝不是被“敌人”骂垮的,而是内部诸多因素造成,最主要是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在信息极度封闭的情况下,统治者的谎言能在一定的时期起作用。一旦公众知道真相,哪怕是部分的真相,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神话就会破灭。正因为如此,1956年以后“冷战”双方攻守之势开始易位。大批左倾的西方知识分子从失望到幻灭,有的退出,有的转到反面。就是还留在“和运”内部的,对苏联也不那么言听计从了,因此苏共领导也意识到要改变策略和语调,更加强调要团结西方中立的和平主义人士,而毛泽东此时正日甚一日地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分歧于焉不可调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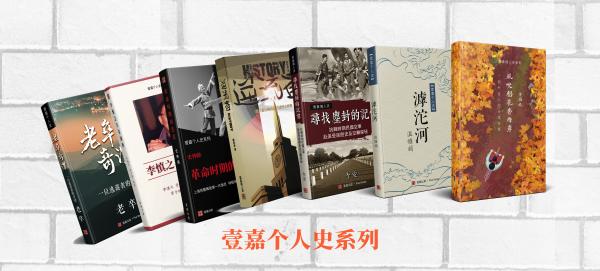
无数水滴汇成江河,无数个体成就历史 欢迎关注壹嘉个人史系列
点击阅读《中苏关系亲历: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