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1923.8.15-2003.4.22)是中国著名的体制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便参与组织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毕业后加入新华日报,后长期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多次作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和外交出访活动。1957年,他因为倡导"大民主"被"钦定"为右派。改革开放后,他先后陪同邓⼩平、赵紫阳访美,并受命创办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长。1989年,李慎之因同情学生运动再次被批,次年被免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职务,开始提笔著述。2003年去世。 李慎之先生值得纪念,原因不仅仅是他几起几伏的为官经历,更重要的是他离职之后奋笔疾书写出的几十篇文章。 李慎之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极度渴望精神自由的现代知识分⼦。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间,李慎之厚积薄发,提笔作枪,为自由正名、为民主摇旗、为启蒙呐喊,书写了他一生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 本文节选自壹嘉新书《李慎之自述与文章集萃》。自述部分系由李慎之档案中的自传、检讨,以及他⼈根据李慎之的自述整理而成。文章集萃部分或者源自李慎之本⼈写的文章和书信,或者源自他人对李慎之采访的文字记录。因此,本书可以说是李慎之的人生自述和精神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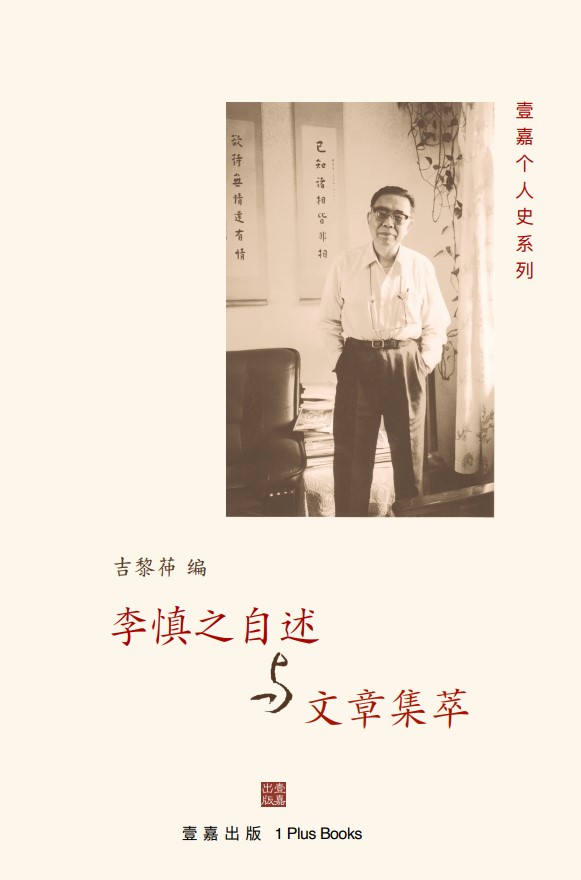
《李慎之自述与文章集萃》,壹嘉2024年9月版,亚马逊等各网络书店, 华盛顿DC季风书店有售
其一 远避名利 钱先生性格开朗,有时也是口没遮拦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论,
出版在六十年代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当
时,我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奇谈怪论”,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据乔冠华告诉我,他认为那是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我也一直怀疑,五十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锺书,何以竟能躲过五七年的大劫。有一次,我问他,他又不信佛教,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他说,那
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他后来又说:“I never commit
myself。”我想也许这就是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复了。 钱先生的诗,我最爱的是“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一联。据在清华低他一班的同学施谷告诉我,锺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如此少年高名,出国回来就
破格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但是到解放以后,就深自谦抑,远避名利。三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锺书的名字。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从来不去串门,到了晚年也都是别人去看他,他则只是
到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 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钱先生虽然躲过了五七年这一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却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这顶帽子是不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胸前挂着黑帮的牌子还昂首阔步,从贡院西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绝没有这样的气度。
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其二 学贯中西 自从海通以还,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学贯中西竞高争胜。确也出了一批大师。但是三个月前,杜维明先生就同我慨叹,真正学贯中西
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之,钱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钱先生有一次曾对我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今日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在这中间,钱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一个。他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世界文学的话后先辉映,实际上是未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先声。 因为钱先生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
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一九八九年唯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
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其三 钱钟书为胡乔木改诗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是乔木同志七十寿辰,但是为了给定于九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文件,他过了“五一”就带着我们这一班人上玉泉山了。比我更了解他的同志说,当时是乔木心情最舒畅的日子:三中全会已经开过,大批冤假错案基本平反,林、江两集团案件已经审判,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已经通过,改革开放征程初始,捷报频传,他个人与许多老朋友的交谊已逐步恢复。在玉泉山,他不但主持十二大的文件起草工作,而且负责处理许多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如就在这年六月份作过一次论证为何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精彩讲话,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所以那时他虽然年高七十,体弱多病,还是精神振奋,有说有笑,富有幽默感。还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他一个人仰卧在草地上,我
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有能源危机,要接点地气!” 我当时已是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我自信深知乔木同志内心的一个秘密。他虽然久居高位,“文革”以前已经因为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然而他心中最珍视的职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曾亲口对我讲过,“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当时他脑袋里真是“一片振兴学术之心”,想办这个所、那个所,起用这个人、那个人,颇有平生大愿,至此方得大展的劲头。这种意愿在与我闲谈中常有流露,惜乎后来大都无法实现。 大约是五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锺书”。我问为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三年了,我从来只知道“官能荣人”,现在才第一次看到了原来“人也能荣官”。 六月上旬的一天,我看到他在走廊里往复徘徊,又屡屡在我的房门口停留,似有垂询之意,不免奇怪,便请他进屋。他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锺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锺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我自以为对乔木同志的心情是理解的:四首《有所思》实际上是他七十岁时的人生总结,是他的平生自序。乔木同志与锺书先生虽然谊属同学(钱要高一班),然而在上大学以前就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投身革命、历尽艰险,然后是久赞枢机、管领意识形态,几十年来基本上是烈火烹油的事业;一个是矢志学问,自甘寂寞,虽然青年时代即名震清华,而解放后三十年,始终视声名如敝屣,如果不是“四人帮”倒台,著作印不出来,也不惜没世而不见称,可谓今之高士。两人之间的这个差别,钱先生本来十分了然,也不知为什么,那一次却似乎完全忘却了,就像改自己的诗那样,只顾一东二冬、平平仄仄,由兴改去。而乔木同志偏偏又是一个极重礼貌的人。这样,居然出现了“我诚心请你改诗,你也费心改了;我期期以为不可,但又怎么好意思请你再改回去呢”的尴尬局面,因此十分踌
躇。这种心情,其实不难了解,要解开这个疙瘩也不难,只要向钱先生提一提就可以了。 六月十二日,我带着这个理解来到钱先生家里,充当“说客”。我与钱先生同乡世谊,比他小十三岁,一向倚小卖小,直来直往,我说:乔木同志一生是个革命家,有他必须守定的信条,像“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
这样的句子,都是乔木的精魂所系,一个字也动不得的。你不能像编
《宋诗选注》那样,嫌文天祥的《正气歌》太道学气就不收的。以钱先生的绝顶聪明,几乎不等我把话说完,已经完全明白。他大概立刻想到了孟老夫子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说“是我没有做到以意逆志而以辞害志了”。然后,我们一起先是恢复原文,再选择我们共同认为不妥的地方改了几个字(如第一首末句“弦急琴摧志亦酬”原作“弦断琴亡志亦酬”,“断弦”旧多指丧妻,与作者原意不符,故改),由我带回给乔木同志。他大为高兴,后大概自己又改了一些,不久就发表在七月一
日的《人民日报》上。 乔木同志自称爱新诗甚于旧诗。看他的诗集,此言信然,虽然我还是偏爱他的旧诗甚于新诗。他的旧诗过去常请郭沫若、赵朴初先生,以至毛主席修改,后来则与钱锺书相切磋。他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就是请钱先生题的签。他告诉我,他在清华读书时,对老师辈最景仰陈寅恪,对同学少年则最佩服钱锺书,然而因为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后来虽有工作关系,却直到“文革”以后,才能倾心结交。
钱锺书的《管锥编》、杨绛的《干校六记》如今已成“当代经典”,当年如果不是乔木同志的亲自支持,是出不来的。
我常常想,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搞那么多人为的阶级斗争,能够让乔木同志从心所欲,尽展长才,在他的岗位上总持文章,宏奖风雅,今天中国的文坛、学界,或者再扩大一点,中国的精神文明,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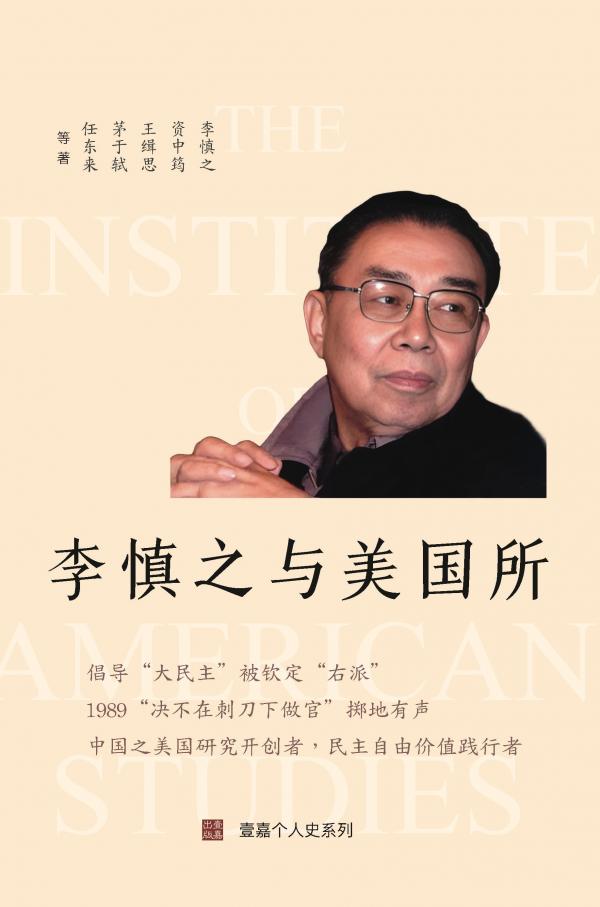
不明白播客丁学良教授推荐,点击购买《李慎之与美国所》
胡平:如果八十年代就算“高光时代”,那是非常大的遗憾
资中筠先生最新自选集《夕照漫笔》上下卷持续热卖中,各国亚马逊及其他网络书店有售
更多阅读: 李慎之:参加朝鲜停战谈判 美国史专家曹德谦:“不在刺刀底下当官”的李慎之 “他是第一个从不跟我说‘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领导”:资中
筠谈李慎之 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无民主也无科学 抗战时期国军后方的军民关系是怎样的? 被“宽释”之后,原国军少将的人生故事 “在光榮與至美的希望裡,我勇往直前!” 中苏关系亲历:从“牢不可破”到“反目成仇”——资中筠《夕照漫笔》书摘 徐友渔:终有一天,启蒙在中国还会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胡平:如果八十年代就算“高光时代”,那是非常大的遗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