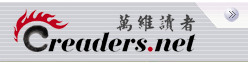中国何以兴盛何以衰落?--寻找中国人的神(三) 玄野 人的盛衰源于其精神的盛衰。国家民族的盛衰则源于其文化灵魂的盛衰,只是滞后效应十分严重,须以百年甚至千年计。中华文化灵魂的构造主要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得以塑造丰富并架构完整。这个文化灵魂支撑其后两千年的兴盛。春秋时期是中国最特殊的时期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当时周王室权威丧失但诸侯依然坚持着尊重王室的习惯。大诸侯间互相征伐但多无灭国之志,百姓还能安心生活。最核心的特点是士人皆可直抒胸臆,精神可以尽情驰骋,文化得以有效锻造。贵族仕宦的短视行为改变了政治版图,但在士人所追求的精神价值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不存在权力对文化的胁迫与操纵。著名的案例不胜枚举。在鲁侯敬拜故去的孔子时左丘明可以痛斥他为何孔子生前你不听他的话,死后却来装大尾巴狼。在宋国史上最牛国君宋襄公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他的庶兄左师子鱼总要批判他贪图虚名不切实际。中国历史上这个唯一的言论高度自由的时代正是中华文明灵魂的完整塑造期。春秋早期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的践行者在大胆试探,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晋文公。他仅在位九年,却对其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春秋末期则是思想家的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延续到了整个战国时代,以至西汉依然有些许成果。老庄孔孟,墨子荀子,孙武韩非,层出不穷。其中任何一位放在秦汉至今的两千年中国历史中都无人能出其有右。何以如此呢?当时人口不足五百万,却在三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大量思想家,而其后两千多年的数亿人口却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可以与先秦诸子相提并论的人物。中国人的大脑出现了重大退化了吗? 原因并非智力的退化。其实这与社会的硬件—人的关系不大,而是取决于社会的软件—制度。在大一统的社会里,每一个思想者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作茧自缚,否则性命不保。忤逆皇权后非但肉体消亡,你的精神遗产也会被付之一炬,名誉上也必须是遗臭万年。想如同苏格拉底那样在必然朽坏的肉体和必然永生不朽的精神之间选择后者,是完全不可能的,历史根本不给你这个选择权。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一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就是你的标签。秦始皇序八州而朝同列,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启了物质文明在东亚的繁盛。而这个大一统并且中央集权的巨大变化也正是中华文明走向衰落的肇始与核心根源。这就像二十四节气的轮转,夏至时节是北方天气最热的日子,同时这一天也正式宣告了天气逐渐转凉的必然。中国的春秋时代为后人奠定了精神的基础,于是就有了后面两千年大一统的物质繁荣。而自秦皇汉武以来,士人再无思想的自由,任何文化创建必须能够为当朝实现物质利益才是正道,否则便是邪淫之徒。于是中华的灵魂画地为牢,精神上再无进展,李唐达到国力鼎盛之后便是北宋以来的中华文明千年递降的尴尬结局。 这一魔咒并非中国独有,西方地中海文明—欧洲文明也重复着同样的轨迹。小国林立而言论自由的古希腊为西方世界奠定了精神的基础,强大的罗马帝国和其后一统天下的基督教使得地中海北岸和欧洲泥足不前近两千年。而最终罗马教廷的堕落造就了其下的各民族国家甚至城邦国家挟武自重。小国林立的局面又促生了言论自由的世代,由此才有文艺复兴,才有西方文明的横空出世。而当代美国之所以长盛不衰,其制度从欧洲诸贤那里的传承和实践是其国体上的根基,而其思想领域的核心保障就在于那个宪法第一修正案。至于是否有个伟大领袖出现改变美国现状也为未可知,因为国际局势的需要不是谁可以左右的。 英国人约翰密尔(或译作穆勒)有一部名著《论自由》,其中阐述了言论自由的四大益处。密尔所论依然局限在自由对当下的影响。当我们把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放到历史长河中来总结其价值的话,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言论自由是一个文化的生命,言论自由的有无决定了千年后这个文化是生机勃勃还是一潭死水。 大一统的出现在物质生产上建构了高效的体系,但在精神思想层面却打造了囚笼,将有开拓性却不利于当时物质生产的思想判了死刑。周朝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奠基时代,同时也是精神思想的主要成就时代,大一统之后再无思想层面的创建与突破。而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国帝制两千年最严重的问题是皇权神圣化。人们失去了本有的对神的信仰,只在先秦百家思想中摘取了那些利于维护当下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思想。这些教条虽然关注着仁爱,但这些仁爱只是人能照顾到的物质利益而已,而那些看似无用甚至于有害的哲学思想固然不利于当权者稳固当下的经济与社会,但那些思想却决定着这个文明在难以预测的未来中的沉浮。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白马非马论,本是逻辑学的根本问题,却因为感觉上无理却难以驳倒就被当权者漠视甚至禁绝了,而思想极其深邃的庄子荀子也因为不利于皇权统治而被边缘化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秦汉帝制以来过分沉迷于物质利益,沉迷于仁爱所达成的人类整体的当下利益,而丧失了对神的崇拜,泯灭了精神追求,灵魂变成了物质欲望的奴隶。 中国历史中被当代人严重忽视的一个世代是六朝时期。这段时期因为南北战争不断,中央集权不足,所以往往被人们鄙视。但是在文化层面这个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可以称作两千年帝制时期在文化精神领域贡献最大的一个世代。当时皇权孱弱,豪强并立,各势力保持着一个魔鬼平衡,于是士大夫阶层可以入世谋官,也可以“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如果没有这个世代在文化精神层面的开拓,就不会产生唐宋时期中华文化的洋洋大观。相比之下,因为再无六朝的相似世代出现,中国宋代以后在文化精神层面几乎可以说乏善可陈。遗憾的是,中国南朝的平衡政治并没有结出可以为后代继承的体制,最后还是为那个千古明君普六如坚一统江山。中国不可能达成欧洲的政治架构,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南岭到长城,河西走廊到大海之间的相对平坦地区的地域太辽阔,这个统一的九州地盘实力太强悍,周边地域断无抗衡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历史沿革的惯性。周朝以降的人文主义已经使得信仰和宗教丧失了神权主义的威慑力,难以让诸多独立的军事势力统一在同一个神权下达成恐怖的政治平衡。 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从普通民众的政治思路来看,当代中国与文艺复兴之后的法国启蒙时代的前期十分相似。这样的说法会导致许多人的不适,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在文化思想界落后于西欧三百多年。实际上用文化现象的比对来计算先进与落后是毫无意义的。中国神权主义的终结在牧野之战后的十几年间,而西方的神权主义终结是晚近的事情,那我们是否可以结论说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基督教文化先进了两千多年呢?文化可以比对,但无法简单定位个先进落后。文化比对的价值主要在于以史为鉴,照亮前行的路。 唯物史观是一个很草率的学说,因为其与权力的绑定,造成了其在许多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而这个学说与真实历史的相左,形成了文化界争相削足适履的奇观,这对学术本身不啻为灾难。封建社会的提法导致很多历史概念的错位。封建是一个政治军事的架构,而无关乎社会思想和经济结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周朝,而这个朝代是中国文化奠基时代,是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最大的时代,甚至可以说中国在精神层面对世界的实质贡献基本集中在这个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不存在中国文化。而其后两千多年的帝国时代和后面所谓的共和时代这个整体,在文化层面的价值彻底无法和周朝那八百多年相比。这个时代可以对标多利安人入侵后的古希腊。这个时代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中的哲学时代,是人类哲学最发达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因为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哲学思维在那段时期最为发达。后来因为宗法的禁锢,人类的灵魂被动地进入囚笼而失去自由。再后来因为科学的发达,人类的思想被每个人自主地锁入囚笼。以前的囚笼是有辱人格的,当下的囚笼是思维层面的,是许多人引以为傲的。 从政治军事架构看, 西方的中世纪与中国的周朝相似,是典型的封建社会。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帝制虽有分封诸侯的做法,但自汉景帝采用贾谊治安策削藩,到武帝稳固了中央集权以降,中国的分封诸侯完全变成了徒具虚名的形式,人们的思想中“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理念逐渐成为天经地义,任何宣称对个人领地有独自管辖权的诸侯都被视作大逆不道。而对个人领地的绝对权力就是封建的最本质所在。把中国两千帝制时代定义为封建社会造成了历史学的巨大混淆。但是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世人又不得不将中国两千年帝制与西方的中世纪封建社会时期划作同一世代。 这很令人纠结,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很简单,就是封建社会这个提法的荒谬。如果单说欧洲历史,封建社会的提法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过程看,显然封建这一历史现象绝非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个时代的最本质属性。而真正反映了历史发展共性的是这个时代的宗教统治。这个时代的最大进展就是爱不再以血缘纽带为必要条件,而是拓展到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任何人。而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宗教教条对人的禁锢。这些主要宗教的教主及以后的诸圣的智慧多是富有活力的,但岁月沉淀千年以后就演化成了僵死的教条。 这一过程正是铁器发展并应用于战争的时代,技术的进步将国家的征伐能力从局部的大约百里的小范围扩展到了陆路可达的自然边界天堑,诸如大海雪山大漠等等。技术拓展武力的同时,哲学家也将原来局限在亲情中的爱拓展到了人力可及的任何地区。博爱思想的蔓延为操不同语言的不同种族间达成和平奠定了基础。基督教世界的使徒时期以及近代两百年欧美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宣教过程是典型例子。中国儒教向周边地区的扩散过程,以及佛教的传播过程都是相似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