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今天向大家介绍台大政治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的书《高思在云》。朱教授对民主制度的现状的分析之大胆、精密、不受教条约束,足以令大陆的一些食洋不化、人云亦云、追逐时髦的犬儒知识分子们汗颜。值得指出的是:我个人认为中国无论是学术界、企业界还是决策层,受80年代西方新保守主义影响都十分严重,甚至邓小平的一些做法和说法,都带有新保守主义的色彩。而2008年以后的事实进一步表明,这种以【去法规】、【私有化】、【劫贫济富】为表征的新保守主义,是造成民主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反思改革开放的一些做法就显得格外重要。读过我以前的博客的朋友们应该熟悉,这是我自2008年以来一贯的看法。
幻象 很多读者可能还记得在南太平洋最接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岛屿,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海边,通过架设望远镜与摄影机,来迎接新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绝大多数人对于新世纪充满着乐观的憧憬,期望这个新的世纪是一个更和平的、更富足的、更公正的世纪,是一个合作互助、永续发展、良好治理的世纪。 这种乐观建立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基础上的,这个变化的主轴是“民主化”与“市场化”。西方知识分子甚至预言,人类正走向历史演进的终点,也是文明的极致。 在这种视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假设:民主可以带来和平,民主可以带来良治;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可以带来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人类社会可以享受美国盛世下的太平,全世界也会心平气和地接纳美国的领导,因为美国是打造世界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龙头。 然而,接下来的发展,与当时的预期几乎南辕北辙。 症结 美国盛世下的“天下不太平”的征兆已经昭然若现。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纷纷陷入严峻的治理危机,政治乱象丛生,甚至民不聊生;在全球各个角落,市场万能、自由化万灵的神话开始消退;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将全球经济推向大萧条的边缘…… 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市场”——被许多政治领袖与知识分子定义为架构2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正遭遇严重的变形与退化。 扭曲市场与民主的根本力量,是美国过去30多年来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个新的秩序让美国式资本主义所向无敌,让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两者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 新保守主义革命 回顾历史,过去30多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启动的新保守主义革命,逐步在全球打造了一个窒息民主的外部环境,也在体制内部埋下了腐蚀民主的因子,并在最近20年形成民主质量全面退化的全球趋势。 撒切尔夫人以铁腕手段大幅压缩福利国家体制,用最猛的高利率手段与严格的平衡预算,强力压制通货膨胀;全面解除经济管制,将包括银行、铁路在内的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并动用镇暴警察击垮工会的顽强抵制。 
1 这套政策思维,最后被升华为“华盛顿共识”,通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力推销,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的典范。这是一场敌视“政府”、丑化“国家”、神化“私人企业”、崇拜“市场”的激进革命。新保守主义推动的政策,加速了自由市场机制中的“弱肉强食”与“劫贫济富”的倾向。 比如,过去25年,美国97%新增加的所得,都落在前20%高所得的那一层。1986年,美国最富裕的前1%家庭拥有33%的财富;2011年,前10%的人拥有70%的财富,最底层40%的家庭只拥有0.2%的财富。 为何在一个放任资本家追逐最大投资回报的体制下,贫富差距的急速恶化难以避免?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种新保守主义革命冲击全世界的形势下开始的,中国再改开之初派到美国的经济学者,受这种新保守主义革命的影响之严重不言而喻。其中不乏把这种新保守主义理念当成【圣经】取回来,在中国大肆鼓吹的人。而这种思潮对中国决策层和企业界的影响之深厚,也就不足为奇了。 差距 《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指出:如果资本平均报酬率高过GDP的平均增长率,其结果必然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他利用先进工业国家几个世纪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资料估算,资本报酬率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增长率平均在1%~2%区间。 这意味着,在GDP中,薪资收入所占的比例会逐渐缩小,而资本报酬的比例会上升。富裕阶层及其后代可以轻易地用钱滚钱,他们财富累积的速度,将远远超过靠薪水过日子的人,何况多数受薪者的所得增幅还跟不上经济增长。除非有战争、国有化或再分配机制来限制财富积累,否则几代之后就可能出现极端的不均。 
西方国家曾出现经济增长与所得分配改善并存的现象,但这是300年间的例外,而非常态。其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以及经济大恐慌之后,西方各国推行高累进税制与社会福利。老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累进所得税,最高税率达75%。 但这些有助于矫正分配不公的制度,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被一一削弱。里根时,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被大幅调降到28%,小布什时期又改为35%;美国最富裕阶层实际税率通常不到20%,巴菲特缴税比例还低于他的秘书。 美国1970年代以后富者愈富的主因,不是富人比其他人更努力工作,而是他们能够利用自己既有的财富,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制定对有钱人有利的游戏规则。代表企业利益的利益集团,主导了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重新制定,并将过去维护中产阶级的租税体制、管制规则、保障体制逐一侵蚀,让美国民主逐步沦为“富豪政治”(plutocracy)。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沉痛地指出:“美国民主早已背离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实质上美国民主已经变形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 鸿沟 以前美国民众可以忍受贫富悬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社会是机会公平的,个人只要努力就可以晋升到上层。但是这30多年来,所谓乌鸦飞上枝头成凤凰的“美国梦”早已成幻影。美国的富裕阶层不但攫获了绝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果实,还不断在追逐各种排他性的特权,从子女入学、医疗服务、就业管道到晋升机会,以致社会阶级分化日趋严重,社会流动管道趋于阻塞,贫穷成为世袭。 斯蒂格利茨举出大量经验证据显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造成的分配不均、教育不均以及贫病交织,在经济上导致生产力降低、打击效率;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不前、家庭负债累累,也必然导致总体消费不足,拖慢经济增长并让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增加。 盖洛普公司调查显示,2006年在美国有小孩需要抚养的家庭之中,有13%的家庭有过因缺钱而无法购买所需的食物的经历,到了2012年,这个比例增加到22%,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 
失灵 美国政治日趋衰败是因为,传统的分权与制衡设计已经越来越深化与僵化,在政治两极化的趋势下这个高度分权的体制已经无法表达多数人的利益。美国各级政府因为“否决政治”泛滥而严重拖累效率。 一波三折的美国加州高速铁路兴建计划就是最好的写照。早在80年代,当时的州长布朗就曾倡议兴建,但直到奥巴马上台后,这个胎死腹中的计划才得到生机。现在,奥巴马快要两届任满还看不到全线动工的影子,预估要到2029年才有可能启用。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评估,美国59.9万多座公路桥梁中,高达1/4的桥梁结构“有缺陷”或者功能上“落伍陈旧”;美国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基本上都是50年代修建,基座与桥梁的寿命都已经逼近使用年限,但目前完全看不出来美国各级政府有能力处理这个棘手问题。 其实,冷战结束后的这20多年,美国的经济正一步步陷入泡沫经济的陷阱。期间美国的高生活水平,以及每年3%~4%的经济增长率,很大一部分是靠海外转包生产以及虚拟财富,也就是靠中国与印度的廉价劳力以及金融资产泡沫。0 
美国民主质量退化的第三个明显指标,就是酬庸与裙带政治大行其道。比如因卡特里娜风灾而辞职的美国联邦政府救灾总署署长布朗,在出任联邦要职之前,唯一的资历是一个赛马协会的会长,但他是小布什竞选总干事的好友;奥巴马时代,驻阿根廷大使是选举金主,外派前还没去过阿根廷,西班牙语也上不了台面;驻匈牙利大使是肥皂剧制作人,但她捐了80万美元给奥巴马。新任总统川普更是【内举不避亲】,直接任命自己的女儿、女婿为白宫特别顾问,【家天下】的势头不可阻挡。 劣质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取得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还积极将“变形民主”与“变形市场”推销到全世界,并试图将这种赋予跨国资本无上权力的宰制结构永久化,成为全球民主质量退化的最大传染源。 这对所有新兴民主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民主被树立为普世价值、唯一的选项;另一方面,美国的这种变形民主又被普遍模仿,人民只能逆来顺受民主包装下的恶质政治,因为民主似乎无可替代。 在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从东欧到拉丁美洲,民选政治人物为了选票,挑动选民情绪,政权变成职位分赃体系,贪污腐化横行;刻意操弄认同、宗教与族群议题,制造仇恨、两极对立与社会裂解,甚至引发种族暴动;民选政治人物的决策也普遍倾向短期回报,导致财政结构恶化或外债高筑。 这些多半属于后殖民社会的第三世界地区,国家体制原本就发育不全,党派间的恶性竞争就更加削弱国家机构,剥夺了人民享有良好治理的可能性。 民主 其实,今日我们所熟悉的“民主”,仍只是一个以“国家”为范畴的政治体制,而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主要权力行使者,却可以跳脱任何单一“国家”的管辖与节制。 比如,今日对所有重要的生活面向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决策者,往往不是选票产生的政府,而是一些几乎完全不受民主机制监督的跨国权力行使主体,如跨国能源企业、大型媒体集团、军工企业、华尔街投资银行、私募基金等。控制这些集团的跨国精英排斥任何限制其行动自由与压低其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还可以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联储的观点与政策。
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颠覆了国家层级的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经济全球化让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宰制下,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既无法有效维护公民基本福祉,也乏力回应公民的政策需求。过去30年,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自由经济秩序,让资本追逐最友善的环境与最高的回报,在全球打造“赢者通吃的政治”。 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在现存的体制下有没有可能改善?诚实的答案是“几乎没有”。在西方的主流思维框架中有没有思路可以为陷入恶质化民主困境的国家指出一条走出陷阱的道路?某些天真的西方学者可能会回答“民主的问题只有靠更多的民主来解决”,或者回答“要靠市民社会团体的改革力量”,或者回答“要先强化法治”。但任何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将这些教科书上的答案是没有实质意义的。 这种思想上的苍白反映出当前西方主流思想的封闭与贫乏,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治理 20多年前,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多年后,他已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而是认为,21世纪国家间竞赛的主轴,是国家能力建设。他提出一个简洁有力的口号:“没有优质国家,就没有优质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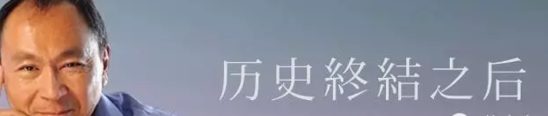
我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以民主方式产生政府,就好像让一辆巴士上所有的乘客,通过投票选出一位驾驶员。这位驾驶员要负责将巴士驶向多数人想要去的目的地,也要决定如何让大家分担汽油费。国家机构就是这部巴士,如果巴士的性能好、马力足、耗油少、配备齐,交给任何一位够格的司机掌控,都游刃有余。一个失败的国家就像引擎出故障的巴士;一个孱弱的国家就像马力不足的巴士。国家机构不健全,无论选出谁来当驾驶员都无能为力。 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却忽视国家基础建设。殊不知,大多数西方国家在一百多年前引进普选式民主之前,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国家机构及其职能,包括常任文官体制、独立司法机构、专业化军队、基础教育体系、现代财税体系、市场监管能力与中央银行等。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代议民主时,现代国家机构及其职能都还处于发育不全状态。 许多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经历了各种失败后终于领悟到,在现代国家机能发育不全的条件下,贸然实施普选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碍国家的能力建设,因为基层公权力机构很容易被宗族势力或地方豪强通过操纵选举而公然据为己有,这个现象在许多实施基层民主实验的中国农村一点也不陌生。 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第三波民主本来就是“揠苗助长”的结果,以至于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都注定要长期陷入劣质民主困境,进退两难。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健全的国家机构,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府治理质量,没有良好的政府治理质量,就很难持续发展经济。 0 0
美国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必将成为反思的对象。这个流行了30年的模式,强调低税收、小政府,相信市场万能与彻底私有化,现在已经走到历史尽头。非西方国家社会精英已经没有可以全盘模仿的普世模式了,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市场经济、政府角色、社会正义以及永续发展四者之间找到均衡点。 同样地,西方引以为傲的代议民主也迟早会成为反思的对象。非西方国家社会精英也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让民主参与机制能真正确保良好治理与增进社会福祉,如何不让“民治”与“民享”脱钩。西方的知识分子也迟早必须跳脱出“西方中心”的世界观,心平气和地去理解与欣赏非西方文明的丰富历史经验,并以开放的胸襟去探索超越现状的制度创新与体制变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