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思辨精神——质疑、探索和真理 什么才能使得我们从未知走向已知?……思辨是唯一的方式。—— 苏格拉底/柏拉图 对于宇宙、世界、自然和社会,人类从古希腊开始有了一个准确无误的立足点,这就是“理性”,这就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作者 “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发现杠杆原理的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212,图6-1)的名言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即便是在对于古希腊精神非常陌生的中国,也为所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知晓。但是,并没有很多人真的理解其深刻的含义和坚实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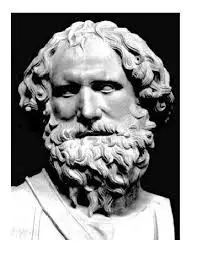
图6-1 阿基米德(Archimedes) 这位伟大的古希腊科学家所说的,不是口号,亦非大话。阿基米德的名言是理性和思辨的宣言: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人类的理性超越任何神圣,也将战胜任何愚昧,理性的力量将把人类从对超自然力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人类文明是从认识世界开始的,人类的进步本质上就是对世界认知的进步,亦即思维的进步。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旅程就是用理性代替本能和用思辨代替直觉的过程,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人类的行为逐渐远离直接功利和走向“间接功利”(相对非功利)的过程。人类的思维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人类思维的进步带来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和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思维能力和由此而来的创造力。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成果,而精神文明则是人类思维的结晶。 崇尚理性,寻找解释,追求真理,就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古希腊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素质之一的“思辨精神”。 给思辨精神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非易事,但是可以说“思辨精神”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1.理性至上:不以宗教或任何超自然因素为解释现象的理由,蔑视权威。 2.注重逻辑:寻求现象的本源和它们的内在关系,而不满足于归纳和猜测。 3.抽象概括:形成超脱于具体事物的理论。 4.直面证据:正视和理论相悖的现象,欢迎挑战和悖论,勇于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检验。 5.超越尘世:蔑视功利,不以实际应用为目的。 理性至上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首要特征。人类文明的几大体系,即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在数千年前几乎同时诞生,并且世代传承下来,影响着当今社会的基本价值。在这些文明中,有的以神权至上,有的以皇权至上,有的混迹于其间,唯有古希腊文明挣脱了神权与皇权的束缚,将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思辨精神使然,这也使思辨精神进一步得到弘扬。 功利曾经是人类文明初期活动的直接动力和目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功利表现得不那么直接了,一些看起来和功利并无直接关系的行为逐渐出现了,比如艺术,继而道德、宗教和哲学。它们不再是直接功利的,而和直接功利渐行渐远,但是它们仍然有着虽然间接的但是不容置疑的功利特征。这毕竟是人类文明从最初走来的必由之路。 人类行为和直接功利的距离可以视作文明程度的标志。如果一个民族的社会行为主要就是寻求当天的食物,那么其文明水平就很低,而如果其一部分社会行为从事非直接功利的事业,比如艺术,那显然其文明水平就较高。 道德、宗教和哲学是一个社会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因此,它们和功利的距离代表着文明程度。如果说道德和宗教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那么哲学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无疑是一个民族最高思维的代表,因此哲学和功利的距离就是文明的程度。 古代文明的哲学,通常有着非常强烈的功利特征。华夏的古代哲学就处于这样的境况,甚至华夏近代的哲学,都没有摆脱此境况,其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入世情节,它实际上是为更加功利的道德和权势服务的。 许多古代哲学都与道德和宗教混生。在中国,哲学一直和道德纠缠得难解难分。由于道德本身没有严格的衡量标准,于是哲学在其中也折腾得昏天黑地。另外一些民族,比如犹太民族,哲学和宗教混生在一起,由于宗教的不容置疑,遂使哲学成为了宗教的仆人。华夏后来更加不幸,道德和宗教都沦为了权势的奴婢,因此哲学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但是,“思辨精神”却使得古希腊与众不同,这是古希腊哲学和其它民族哲学的分水岭。“思辨精神”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使得“哲学和科学的结合”成为可能。在其它的文明中,哲学或者和宗教结合,或者和道德结合,但都没有形成哲学和科学结合的格局。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同时哲学和宗教的疏远,以及哲学与道德的竞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古希腊特质。 “思辨精神”正是形成“哲学和科学结合”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在古希腊,由于“思辨精神”的存在,宗教既不能成为哲学的教条,也不能成为哲学的伙伴,于是哲学和宗教是非常疏远的,宗教充其量只能成为哲学的“注脚”;同时,也是由于“思辨精神”的存在,哲学对于道德的质疑也使得道德不能成为哲学的准则或指南,因此道德至多是哲学的“副产品”。 哲学和科学的结合是古希腊学术最典型的特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他不仅仅是一个大哲学家,而且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在许多自然科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并非凤毛麟角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规律,因为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而且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都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造诣。 于是可以理解,阿基米德的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这就是整个古希腊世界的世界观。他关于“杠杆和地球”的名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古希腊人把理性和科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宰大地和宇宙的不是神秘的上帝,而是理性,世界和宇宙是可以被认知的,如果必要,也是可以被改造的。于是,意识和存在之间将由理性的“杠杆”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意识对于存在的认识和干涉是可以实现的。于是,人间的无知和恐惧在古希腊文明的科学理性和求真勇气面前淡去了,而天上万能的上帝根本就没能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古希腊世界落脚。在古希腊世界,神不是人的主宰,亦非永远正确的偶像,而是人的朋友、战友和竞争者。 宗教在人类文明中的出现带着浓厚的功利目的。宗教的现实和它所声称的“超凡脱俗”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民族的宗教都有这样的特点:上帝保护他们,对上帝的虔诚会有丰厚的回报。人们在贫困和恐惧中从宗教寻找慰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发展史上都出现了宗教信仰,俨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出自洪荒的人类要在这不可知和充满敌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期望克服恐惧,解释现象和认识世界,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和生存的信心。宗教应运而生,提供了这样一条“捷径”。毋庸讳言,人类最初的宗教信仰的基础是恐惧、无知和功利。 不难理解,一个文明的发达程度也是其与无知和恐惧之间的距离。而思辨把人类从原始的无知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思辨精神的意义在于给予人们以追求精神解放的勇气。正由于思辨精神,古希腊的宗教具有非宗教的特点。所有产生在古希腊以外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许质疑神和他的教导。但是古希腊人却完全不同,他们不仅质疑,而且把神塑造成和他们一样的外形和内心。古希腊神和古希腊人一样,具有人的缺点,这就是古希腊人对神的极大不恭,也是对神的极大信任。 正是由于思辨精神,古希腊的宗教和所有其它民族的宗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古希腊的宗教,对古希腊人来说就是神话,是古希腊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绝不影响他们对于真理的追求。他们没有把神话和科学事实混为一谈。古希腊的神话更像是小说,并不干涉作为学术的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别的古代宗教,甚至一些现代宗教,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逐字逐句的教义成为了人们必须信仰和履行的教条。而古希腊的宗教截然不同,其大致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完整的神谱——古希腊的众神有着清晰的来龙去脉。曾经有人把古希腊的科学思维归功于古希腊人的逻辑思维,古希腊的科学得益于完整和逻辑的神谱。也许更应这样表述:他们的神谱得益于对完美和逻辑的追求。 没有清规戒律——和后来的宗教(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相比,古希腊对神的信仰(或称“宗教”)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他们在意的是人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宗教的狂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神本身的人性化——是古希腊宗教的一个特点。古希腊的众神和人几无区别,只是他们比人更加强大。他们也有人的缺点,偷情、阴谋,甚至暴力。古希腊的神由于这样的特点变得更加可爱和容易被接受。当然也正由于此而被后来的宗教视为异教。 政教分离——其它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教合一的,这使得宗教信仰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和法律,从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直接导致了宗教迫害。但是古希腊不同,其政教分离是如此彻底,就是近代社会也不能做得更好。欧洲通过文艺复兴用很长时间才逐渐回到古希腊政教分离的传统。而在中国历史上,政教从来合一,唯一不同的是,其皇权大于神权,神权只是皇权的附庸,因此政教合一更加彻底,只是人们对于宗教的服从远逊于对于皇权的服从。皇权至上也使得中国的政教合一具有更加反人道的本质。古希腊的政教分离应归功于思辨精神和理性至上的理念,也归功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后者将在下一章阐述。) 宗教和学术的分离——宗教无权对学术进行限制或控制。这也就是将会在后面的章节中阐述的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在悼念阵亡将士时的著名讲演中几乎完全没有提到神。在古希腊,神和人是如此的接近,他们就是人的邻居和朋友,人们可以拿神开玩笑,可以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但是同时,神又是和人如此的疏远,他们既不干涉人的政治,也不干涉人的学术。唯一的解释就是,古希腊人把理性远远置于神或者任何超自然力以上。在古希腊人的思辨精神面前,任何神圣都必须让位,任何权威都必须俯首。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绝对无法让他们信服。对他们来说,如果有《圣经》这样一本书,那么也仅仅是一家之言,而且是不会占有多少地位的一家之言。古希腊人会对《圣经》进行质疑,从而发现《圣经》的说教本身无法自洽。古希腊人必定会从《创世纪》质疑其真实性,从《约伯书》质疑其道德准则。这也就是当时的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古希腊文明恨之入骨并欲彻底铲除的原因。 神秘主义通常伴随恐惧和听天由命,而在思辨精神占了主导地位的古希腊,神秘主义不会有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发达的古希腊的哲学和思辨没有发展出一套共同的宗教教义或者编纂出一套宗教经典。思辨精神也直接导致了古希腊社会的公正、宽容和理性。 正是这样的思辨,使得古希腊人的哲学选择了一条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创造了古希腊独一无二的哲学和科学,而它们进一步使得古希腊的“思辨精神”的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于是,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挣脱了尘世的羁绊,从而可以高屋建瓴、超凡脱俗,其达到的高度是任何其它民族的学术远远无法企及的。哲学和科学结合的传统也直接导致了西方的学术高于神权和皇权的格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基米德才能给出如此伟大的宣言。 阿基米德的时代已经是希腊化时期,距离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5-547,图6-2)已经过去了近四百年。泰勒斯曾经成功地在公元前585年预言了公元前584年5月28日希腊地区的那次日全食。比预测日全食本身更加重要的是,它表明从那时开始,古希腊的哲学家不再认为这些大自然的奇观是神秘和不可知的,而是坚信这些看似变化万千难以捉摸的现象背后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显然,古希腊的哲学家从那时开始就把揭示这样的规律作为自己的使命。于是,超自然的神秘和不可知的黑暗在理性的光芒下消失了,人类理性的黎明是在古希腊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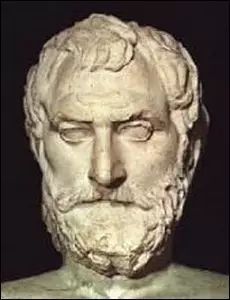
图6-2 泰勒斯(Thales) 这种规律,希腊人称之为“逻各斯”(Logos)。这个词的含义表示理性、真理、概念、逻辑等,今天中文的“逻辑”音译自西文Logic,而其词源就是Logos。古希腊人为此倾注了巨大热情,远远超过了对神灵的关注。注重逻辑推理,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科学不可缺失的一环。 理性总和尘世有着距离,泰勒斯曾经由于晚上走路还在一心留意天上的星星,居然掉进了路边的沟里。他的仆人笑话他光知道研究天上的东西,连自己脚下的路都看不清了。还是二百多年后的亚里士多德惺惺惜惺惺,举例说明哲学家并非不了解尘世的事情——有一年泰勒斯靠了解天文气象而投资橄榄榨房而赚了不少钱,哲学家要赚钱并非难事,只是他们的志向不在于此。确实如此,古希腊哲学家研究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并无什么眼前的利益可以追逐。在古希腊几乎没有富裕的哲学家,如此甘于清贫的物质生活而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因此,古希腊人追求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认识出于一种和眼前的功利根本没有关系的动机。正是超脱于功利,使得古希腊人在学术上能够超越尘世。古希腊数学完全是抽象的,这和一些其它古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许也正因如此,古希腊人对于改造世界并不像对认识世界一样热衷。他们对于世界和环境采取的是一种顺其自然与和谐的态度,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更多的是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以及让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和睦相处。他们并不热衷于把在探索未知世界中获得的知识用于日常的功利目的。 阿基米德在浴缸里突然发现了浮力定律,激动得没顾得上穿衣服就出门狂奔,还高喊“Eureka”(希腊语“发现”的意思),为了这“成功发现”欣喜若狂;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0,图6-3)在证明了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后,也就是后来以他命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杀了上百头牛来设宴庆祝。阿基米德的故事细节也许并不真实,但正是这样的传说得以流传的社会背景,体现了不仅仅是阿基米德,而且是整个古希腊民族对于知识近乎“疯狂”的渴求和景仰。这正是所谓的“希腊性格”,一种其它古代民族不具备也不理解的道德素养和价值观念。我相信古希腊阿基米德的“裸奔”是虚构的,就如同华夏“范进中举”中的范进由于突然的仕途亨通而发疯是虚构的一样,但是对于这些虚构的广泛流传和会心认可,则体现了古希腊民族的独特性格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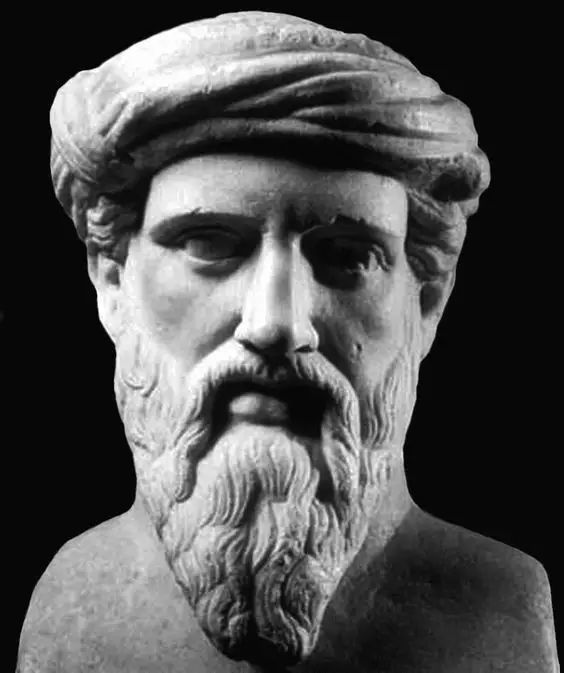 图 6-3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雕塑,陈列在罗马的Capitoline Museums 好奇的激情和沉思的美德,这是构成古希腊性格的重要部分。古希腊语的“Eureka”(“尤里卡”),伴随着人类社会走向理性和现代的步伐,在世界的所有角落回响。“尤里卡”揭开了过去未知的神秘面纱,也改写了曾经笃信的普遍常识。古希腊性格无可争辩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和现代社会中显现:越合理的社会,这样的性格就越明显;这样的性格越明显的地方,社会就越合理。 正是由于思辨精神,使得古希腊哲学脱离了直接功利。古希腊的哲学所研究的看来完全没有实际用途,而正是这“毫无用处”,体现了文明的更高层次,她对于人类的物质利益,居然要在千年之后才被逐渐理解。我相信,古希腊人并不确定他们所研究的具有如此深远的间接功利,但是他们对于直接功利的疏远,却证实了他们已经完全不同于其它同时代民族的目光短浅,而具备了我们甚至今天都不易理解的高瞻远瞩。古希腊的基于思辨精神的学术,居然在两千年之后,还不得不使我们对其思维的高度和深度赞叹不已。 正是古希腊人的抽象思维,使得我们现在所知的数学成为可能。毕达哥拉斯是一个里程碑,在此前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数字总是和具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毕达哥拉斯把数字和具体的事物彻底分开,于是数字就是抽象的数字,不再和具体的实物相联系。逻辑证明,是古希腊的数学和其它文明(比如华夏)的算术的另一个分水岭。暂且不说“毕达哥拉斯定理”从广义上被证明本身是一个伟大事件,更重要的是其体现出的对于数学定理的逻辑证明这一理念:从普遍意义上证明一个规律,而不仅从众多的现象中归纳或猜测。这是古希腊人对于人类思维的一个举世无双的重大贡献。从无穷无尽的现象中统计一种规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普适的逻辑证明,任何统计都是不完备的因此也是不可靠的。而古希腊人开创了逻辑证明的先河。 在华夏,“勾三股四弦五”也很早为人所知;在更早的古巴比伦,有人知道包括“勾三股四弦五”在内的十多种构成直角三角形的边长组合。但是这些都只是一些特例而已,并无法称作定理。 古希腊人不满足于直觉和个别特例,非上升到理论决不罢休。英文的“theory”即来自古希腊文的“theorein”,中文译为“理论”。古希腊文的“theorein”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研究事物,推导出普适的结论。数学定理是从一系列公理出发,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到的。所以,只要公理正确并且逻辑严谨,那么定理就是正确的和普适的。这一原则和方法在后来的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25-265,图6-4)几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欧几里得几何是古希腊科学方法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其对后世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西方物理学家相信,只有把对于物理现象规律的解释表达为“美丽的数学公式”,才算上升为了理论。  图6-4 欧几里得(Euclid),雕塑,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 古希腊人的思维当然也涉及到了“上帝”。有的学派认为上帝是存在的,而有的学派则不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428,图6-5)认为有一种神圣的精神在冥冥中主宰了宇宙,创造了万物并给予了意义。但也正是他,认为太阳也是物质组成的,其大小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差不多大。可见他的“上帝”并没有干涉他寻求理性的解释。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370,图6-6)所代表的学派则来得更加彻底,认为这样的“上帝”并不存在。近代的一些哲学家,给不同派别的古希腊哲学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比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但这都不足以描述古希腊哲学的本质。其实不管是哪个古希腊哲学学派,不管是以上哪种哲学观点,都和其它民族对于“上帝”的解释和对大自然的认识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古希腊哲学派系的伟大思想尽管各自独树一帜,但是它们都准确无误地表明,古希腊人允许“上帝”参与他们对于真理的探索,但是拒绝让上帝来主宰他们的思想或干涉他们的判断。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如同灯塔,指明了真理探索者的道路;如同阳光,撒向曾经是黑暗的尘世。
 图6-5 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  图6-6 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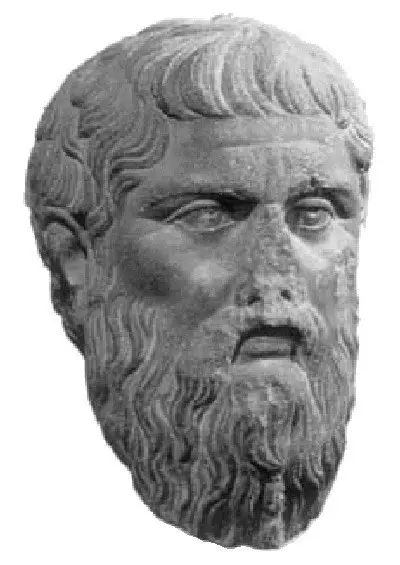
图6-7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在自然哲学中,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90-420,图6-7)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受到了来自以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原子论者的挑战,但是原子论者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亦即,如果我们认定存在和观测无关,那么观测对于理性就不再必要,于是理性赖以生存的证据就无法获得。亦即,没有了观测,对于存在就不可能有理性的认识,于是对于理性来说,就没有存在。这导致了两难境地:如果客观存在和观测无关,那么也就和理性无关,于是也否认了理性对于存在的认识和描述,那么,一个理性不可认识和描述的存在还算存在吗?如果是,又如何判定呢?这个争论实际上定义了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亦即,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究竟存在是否依赖于意识?在二千四百年后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基础的探讨中将激烈地重开这个争论,几度硝烟弥漫,尚未尘埃落定。那只诞生于哥本哈根的“薛定谔猫”,怎么看都像祖籍为古希腊。由此可见,古希腊的思辨是何等地超越时代。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方式,在数千年后仍然是我们探索真理的启迪和指南。 比古希腊所创立的那些伟大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探索真理的勇气及智慧,其对人类思维的发展可谓极其重要并且举世无双。这就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伟大之所在,其最高层次地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理性。思辨精神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其提出的理论之正确与否,而是在于其对于真理追求的态度和精神。思辨精神允许错误,但不允许欺骗;允许权威,但不允许扼杀异议;追求真理,但是从来不以真理自居;解答疑问,但是鼓励质疑。 正由于此,古希腊人创造了求真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使得科学的发展成为可能。这样的精神也创造了理性和宽容的社会环境,从而使得民主的诞生成为可能。 在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在学术上开放自由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我一直怀着特别崇敬和好奇的心情。这是华夏在哲学上唯一的春天,后来就一直是秋冬了,不同的只是深秋、初冬,还是严冬。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毕竟太短暂了,即便在绝对时间上还不能算太短暂,其留给华夏哲学家思辨的时间也是不够的。但是无论如何,那是一个我们必须景仰的时代。 只是,那个时代并未产生类似古希腊的学术。古代华夏并非没有哲学,只是其从一开始就更像是宗教和道德的附庸。换言之,古代中国的哲学还没有成年,就成了宗教和道德的童养媳。或者说在古代华夏,哲学还没有在思辨的艰难旅途上走多远,就一头栽进了宗教和道德的怀抱。当后来华夏的宗教和道德本身也沦为权势的附庸之后,哲学的境况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古代华夏的思辨先天不足又后天不幸,导致了辨有余而思不足。华夏古代的一些辨论文字,可谓十分精彩,但却有本质的缺憾。 “老庄哲学”是古代中国在思辨领域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也被当今一些国人推崇为可以与西方匹敌的关于认识自然的哲学。不妨在这里对比“老庄”和古希腊哲学家的不同。 老子的生平不易考证,传说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前470年左右。《史记正义》这样记载:“老子,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日月角悬,鼻有双柱。周时人,李母怀胎八十一年而生。”可见,他的130岁寿命值得商榷,完全不可置信的是老子的母亲怀了他81年他才出生。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名周,其著作《庄子》被誉为“天下第一奇书”,其中《秋水》篇又被人们公认为《庄子》中第一等文字。作为《秋水》篇中一则著名故事——《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实在精美绝伦。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文意思是,庄子和惠子一道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儵鱼游得多么悠闲自在,它们很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因此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鱼的快乐;你也不是鱼,因此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还是顺着先前你的话来说。你刚才所说的‘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的话,就已经先肯定了我知道鱼儿的快乐,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鱼儿快乐的。” 极其精炼的语言,几乎通篇的对话形式,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把辩论推向高潮。庄周的狡谲,惠施的机智,跃然纸上。双方的敏捷思路和睿智谈锋令人拍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庄周在最后有诡辩甚至耍赖之嫌,且手段并不高明。 但是,从这机智和狡谲的辩论中得到的仅此而已了。庄子和其他诸子的文字更倾向于文学和伦理,在语言和修饰上充分注重,而对于规律和本源却缺乏深究,这样的雄辩依然远离科学意义,而对此的津津乐道更阻碍了向科学的升华。庄周惠施的辩论和古希腊的思辨之间的不同,折射了华夏哲学和古希腊哲学的巨大差异。 在古希腊,哲学家绝不会满足于信口开河一些陈述。他们的思辨,充满着理性和智慧。在那些光辉夺目的古希腊思辨中,我们可以随手拈来一些例子。 在庄周和惠施辩论鱼的快乐之前很久,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一位小师弟证明了2的平方根是无理数。这个证明应该所有读过高中数学的都看到过: 命题:2的平方根不是有理数。 证明: 如果√2是有理数,则可表达为√2 = b/a,其中a和b是自然数,并且没有公约数。
那么b2=2a2,可知b2必是偶数,于是b也是偶数,并可以表达为b=2c,其中c是自然数, 于是4c2=2a2,亦即a2=2c2,所以a是偶数。 至此,a和b都是偶数,它们有公约数2,这和原假定不符。 因此,√2不可能表示为b/a,亦即,√2不是有理数。 这个狡猾的证明透射出的逻辑力量和智慧光彩在今天的大学课堂上也博得喝彩。 欧几里得对于有无穷多个素数的证明进一步展示了其思辨的伟力: 命题: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 证明: 假定素数的个数是有穷的,一共n个,其中Pn是最大的素数。可得n个素数的积: P1XP2X……XPn=S 现在考察正整数 S+1。如果其是素数,那么显然大于Pn。如果其不是素数,那么肯定可以被一个素数整除,但是这个素数一定不是原来n个中的任何一个,因为原来n个素数中的任何一个被用来做除数都有一个余数1。 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存在着比Pn更大的素数,因此我们最初的假定不能成立。所以最大的素数是不存在的,亦即,素数的个数是无穷的。 简洁明了的证明所隐含的思辨和逻辑的力量令人赞叹不已。这样的思辨和庄周的截然不同,前者是理性的思辨,而后者是艺术的争辩。在严谨的推断和简单的猜测之间的差距大概就是“思辨精神”。这不能简单地称为“差距”,而是“鸿沟”,一条人类思维和理念极难跨越的鸿沟,不妨称其为“古希腊鸿沟”。只有古希腊人跨越了它,而且跨越得如此优雅和轻松自如。我一直为这样充满智慧的逻辑所折服,不禁赞叹,这是何种伟大精神引导下所创立的人类思维的典范? 以上所举出的和此后要举出的仅仅是古希腊“思辨精神”一些极少的事例,它们就像是我们在一个巨型仓库门口窥见几件随手摆放的巨大兵器,那不可思议的尺度和重量令人困惑:那些打造了这些兵器并且可以潇洒挥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满库尘封的兵器到底还有多少? 庄子的《秋水》也很容易令人想起古希腊的芝诺(Zeno of Elea)悖论。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芝诺悖论中的一个,即阿喀琉斯无法追上乌龟。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二分法”,芝诺用其证明了运动的不可能性:如果一个运动要从始点抵达目标,那么它首先要抵达一半的地方,为了抵达这一点,那么还要首先抵达一半的一半的地方,依此类推,有无限个这样的点要首先抵达,这有限的运动物体,怎么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克服这无限的必经之路?不仅抵达终点不可能,而且实际上连任何一个距离的运动都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距离都可以再被分作无限的1/2的数列或者级数。于是,任何运动都是不可能的。 从技术上说,芝诺的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用微积分的方法解决,但是在芝诺的时代,距离现代微积分的诞生还有两千年的漫长时光。而芝诺所架构的“诡辩”,实际上就是后来微积分要克服的困难和解决的问题,亦即,在无限的过程和有限的空间之间的矛盾。毫无疑问,芝诺悖论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正是这显然的错误结论和严谨的逻辑所构成的两难将哲学置于必须直面的境地,这样在严谨逻辑支持下的“荒唐”结论恰恰构成了迫使哲学家不得不接受的严肃挑战。芝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困扰了世世代代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深化了无穷和极限的争论和研究,促使了微积分的诞生。 今天所说的微积分是英国的牛顿(Newton)和德国的莱布尼兹(Leibniz)不约而同在18世纪发明的。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就已经非常接近了微积分,而且运用“穷竭法”计算出了球面积和体积。他得到了现在用积分才可以求得的球面积和球体积的解析解。阿基米德也运用“穷竭法”计算了圆周率,尽管圆周率的计算相对于球面积和球体积的计算要容易很多,但是阿基米德的圆周率计算方法是开创性的,他的记录直到700多年后才被南北朝的祖冲之(公元429-500)打破。祖冲之使用的方法“割圆术”有点类似阿基米德的“穷竭法”。 古希腊人对于理论和方法的重视远远超过具体数值。比如古希腊人对√2的具体数值并不感兴趣,他们重视的是寻找表达完美的√2的方法。对于阿基米德来说,计算圆周率主要是为了检验他的“穷竭法”,因此在他引以自豪的成果中,并没有圆周率的计算。阿基米德按照古希腊的概念,很可能认为对于哲学家来说计算圆周率是一种“蓝领”工作,既然方法已经有了,无非就是大量重复的计算而已,因此圆周率只是自己随手拈来的副产品。 过去我也“愤愤不平”:阿基米德你也太牛了,凭什么一个自己都不在意的副产品就把世界给镇了?毕达哥拉斯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要不是你,这定理不就算是华夏的了吗?古希腊你也太欺负人了,本来很壮观的华夏,有你在就没法提了。 说到庄子,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无限可分的思想。这也是华夏的骄傲,他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其朴素的无限可分思想很有意思。但是,实际上一尺的木头棍子在这样“日取其半”不到一个月就不再会是木头了,因为那时就已经到了原子的尺度,远远小于了构成木头的最小组分,即分子,于是木头就不复存在,更不可能继续分下去。古人不知道分子和原子,这点我们不能怪庄子。不管如何,无限可分的思想还是值得称道的。 这也令人想起比庄子早一百年的古希腊德谟克里特提出的原子论。古希腊的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物质就叫原子。在古希腊时代,完全不可能用实验证明原子的存在,这一杰出的思想将在两千多年后才被实验证明。原子确实存在,只是原子还不是最小的物质存在形式,其依然可分。现在看来,物质并不能无限可分,不管是否最终如此,古希腊的原子论无疑是人类伟大思维的一个杰出代表。这是一个对于世界本源探索的巨大创举,是古希腊思辨精神之伟大的一个例证。 古希腊人的思辨,当然不仅仅限于身边的事物,他们对于别的民族认为神圣不可触犯的天体也绝无畏惧,显然认为“思辨精神”是普适的,甚至“天堂”也不能例外。 太阳和月亮俨然天上的主宰,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在古代中国有夸父追日、嫦娥奔月。那时国人也许并不完全相信太阳和月亮的确如同传说中一样,但也并无兴趣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古希腊人不这么看待这些似乎非常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而觉得这些都属于应该并且可以被认知的。于是,他们要看看这些天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古希腊人并不憧憬什么月宫嫦娥,他们的神就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和他们很近,而且习性也差不多,都有人的缺点。既然太阳神就在奥林匹斯山上,月亮自然也不会远了。 于是,古希腊人的思辨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天体,阿那克萨哥拉不恭地认为太阳不过是一个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小相仿的燃烧着的石头,比此更进一步,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0-230,图6-8)科学地测量了太阳和月亮对于地球的相对距离,计算了它们相对地球的大小,其方法让人拍案叫绝:当月亮正好呈现半月的时候,他测量了月亮和太阳的夹角,得到的结果是87°。这时的太阳、地球和月亮正好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月亮所在的角是直角。于是,月亮和太阳对于地球的相对距离就可以计算出来了。由此他算出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是地球和月亮距离的20倍。当然由于当时的观测精度不够,这个结果误差比较大。正确的结果,由于月球的近地点和远地点以及地球的近日点和远日点的缘故,应该是角度在89°50’31”和89°51’48”之间,从而距离比在362和419之间。尽管误差难以避免,但是阿里斯塔克的方法是完全科学的,其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亦即,太阳比月亮要远得多。由于太阳和月球圆面的视角相差无几,因此,太阳也一定比月亮要大得多。

图6 - 8 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阿里斯塔克还继续用月全食时地球阴影掩盖月面的时间计算了地球和月球的相对半径,他得出地球半径是月球的三倍,这已经和实际的3.66倍很接近了。因此,太阳也比地球大得多。这些结果很自然地导致了日心说,因为,小的物体绕大的物体转动显然更加合理。阿里斯塔克提出的日心说是如此地超越时代,这个学说在沉寂了1700年后在文艺复兴中再次被提出时,其掀起的轩然大波撼动了所有权威者和普通人的思想。 阿里斯塔克的观测和计算的结果本身已经非常伟大,更加值得称道的是驱使这样的观测和计算的思辨精神。我一直在考虑阿里斯塔克的办法为什么别的民族没有想到使用。诚然,如此大智慧并非谁都具有,但更重要的是勇气和精神。我们不妨把思辨称作理性至上和具有勇气的思维。许多民族把自己的思维禁锢在宗教和世俗的天地中,束缚在权势和功利的囹圄里,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大智慧。 古希腊人认为宇宙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并坚信这些规律是可以被揭示和认识的。比如,毕达哥拉斯确信宇宙间存在一种神圣的以数为基础的规律。毕达哥拉斯学派被称作有宗教色彩的学派,但其并没有后来的宗教那些特征,而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认识世界。 这些思辨和实践,使得古希腊人更加坚信理性高于一切,自然和世界可以被认知,可以被理解。欧几里得的理论更告诉了人类,世界的认识是可以被演绎的,亦即从有限的知识出发,仅仅通过逻辑演绎就可以得到从前未知的知识。欧几里得把前人和当时的几何研究成果按照非常独特和完整的方式整理成书,亦即举世瞩目的《几何原本》。此书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是课堂里教材的直接蓝本。欧几里得几何是古希腊思辨精神的杰出典范,她不仅仅告诉人们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而且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可以从一些基本的公理通过演绎进行认知。这样的演绎是人类思辨精神的登峰造极之作。 当世界上所有其它民族都没有大地球形的概念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6-194,图6-9)却不仅知道地球是球形的,还计算出了地球的子午线和半径。他发现在埃及的塞恩(今天的阿斯旺)夏至中午的太阳可以直射到井里,旗杆也没有阴影,而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旗杆则有一段阴影。他推断,只有大地球形才会导致这样的现象。于是他测量了亚历山大城到塞恩的距离,用几何方法就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子午线)和半径。其和现代的准确值仅相差1%,这个结果到了非常近代才需要修正。我相信埃拉托色尼的结果如此接近准确值应有幸运的成分,但是他的方法无懈可击,因此他的结果并不偶然。一千八百年后的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试图向西航行抵达印度时没有采用埃拉托色尼的结果,哥伦布对地球的尺度估计太小,以至于他认为从欧洲向西航行抵达东方的距离更短。如果哥伦布相信埃拉托色尼的这个结果,那么他就不会把他抵达的北美认作印度了。当然,也许他可能就不会取道向西去寻找东方的印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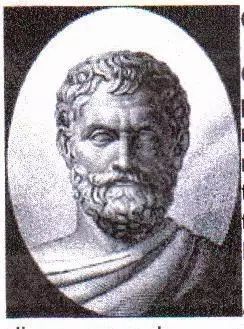
图6- 9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也正是这位埃拉托色尼,创造了研究数论寻找素数的一种方法,亦即埃拉托色尼筛法,至今还是经典的研究数论的方法。数论是数学中距离实际应用最遥远的理论,古代数论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只有具有纯粹并且强烈的求知渴望才有可能将如此枯燥且毫无实际功利的学术进行下去。 和埃拉托色尼和阿基米德同时代的阿波罗尼(Apollonius of Perga,公元前262-190,图6-10)所研究的圆锥曲线在当时也“毫无用处”。阿波罗尼用想象的平面以相对圆锥底面不同的倾角切割圆锥,他证明了所得到的平面和圆锥的交线就是圆、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并把它们开创性地统一为圆锥曲线。他对这些圆锥曲线的研究已经非常接近在1800年后文艺复兴后期笛卡尔的解析几何方法。他用纯粹几何方法对圆锥曲线的研究水平之高超,就是今人也不能出其右。近两千年后,科学家发现所有的天体运行都遵照这些圆锥曲线中的一种,其实,任何物体在保守场中的运动轨迹都必定是这几种圆锥曲线中的一种。

图6-10 阿波罗尼(Apolloniusof Perga) 这种“毫无用处”的数学研究还将由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城的刁潘都(Diophantus,约公元200-284, 图6- 11)进一步推进,这位当之无愧的“代数之父”将古希腊以几何为中心的数学研究扩展到了代数领域。这些伟大的古希腊数学家和他们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科学方法,使得古希腊当之无愧地成为数学圣地。 
图6- 11 刁潘都(Diophantus) 难怪著名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是希腊,弥留之际他数次说“我要到……希腊报到了。”并用颤抖的手写下“希腊”。 世人通常把不实用的称作“屠龙之术”,由于世上无“龙”,此“术”便无用,以此嘲讽那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古希腊人不在乎这世界上是否有“龙”,他们本来就不求实用,更不急功近利,于是他们对“屠龙之术”乐此不疲。这“屠龙之术”被尘封了千年后,终于被后世人们领悟其伟力。当那些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雕虫小技”都随着岁月淡出后,古希腊的“屠龙之术”的光彩却与日俱增,让后世人赞叹这和尘世和功利看来毫不相干的思辨精神居然具有如此伟力。 医学是检验一个民族理性的另一个直接的标准。几乎所有民族一开始都是从草药、咒语和宗教仪式中寻求对于疾病的治愈,但是古希腊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图6-12)开始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医学。希波克拉底并没有一蹴而就地创造了一个现代医学,而是从理念上和精神上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图6-12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将医学导向理性,把丰富的经验和合乎逻辑的推理相结合,使古希腊的医学从此超越了经验积累的框架而成为科学。《医学史》作者卡斯蒂廖尼(Castiglioni,公元1874-1953)这样评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因为它说明通过实验、实际观察和正确推理,可以得到极有价值的宝贵材料。”古希腊人大胆的合理假说、严谨的逻辑论证和苛刻的实验检验使得古希腊医学成为现代医学的源头。 从那时开始,古希腊人已经坚信,人类的疾病可以用有效的方法治愈,而不应靠祷告或神的干预。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尽管当时的医药知识还非常贫乏,但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作指导,古希腊人不迷信,而是用一种求真求实的态度来对待疾病。在下一章将看到,希波克拉底不仅从学术上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石,而且在道德上给予了医学以普适的人道准则。 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自己也对动物做了很多实验,试图了解心脏和脑的功能。亚里士多德的所作所为在古希腊很普通,一个哲学家动手做实验或者研究数学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是中国古代绝看不到的现象。作为哲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所进行的生物学研究是如此意义深远,以至于后来的达尔文(Darwin,公元1809-1882)这样说:所有现代的生物学家都应当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这绝不夸张。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希罗菲勒(Herophilus,公元前335-280,图6-13)被称作解剖学之父,通过解剖他对人的脑和神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同样是亚历山大城的埃拉西斯特拉图(Erasistratus of Chios 公元前304-250)被称作是现代生理学的奠基者,他深入研究了神经系统。古希腊医学上最著名的则是后来的盖伦(Galen,公元129-200,图6-14),当时在政治上已经是古罗马时期,但是盖伦在文化上仍然属于古希腊。他出生在Pergamon,也就是前几章提到的在小亚细亚的古希腊著名城市,在德国柏林有着那里出土的很多辉煌文物。盖伦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解剖学家,他是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希腊医学的集大成者。他把古希腊精神完整地体现在了医学上,他把希波克拉底奉为他在医学上的英雄,把柏拉图作为他在哲学上的榜样。

图6-13 希罗菲勒(Herophil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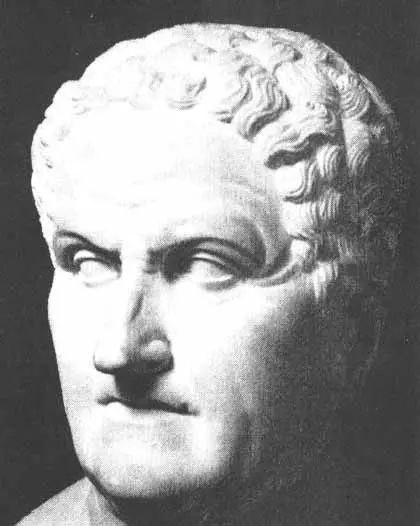
图6-14 盖伦(Galen) 古希腊医学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到公元2世纪的盖伦走过了600多年的历程,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而这个时候,中国医学也基本上从战国时期的扁鹊(约公元前5世纪-3世纪)走到了东汉的张仲景(约公元150-219)和三国时期(公元2世纪-3世纪)的华佗。这段时间中国医学并没有详细的记录,很多基于一些传说,关于扁鹊和华佗也不例外,甚至连他们的生卒年都没有记录。 如同古希腊的医学体现了古希腊精神,中国医学也渗透了中国的世界观。传说和夸张,而不是严谨的实验证实,成了中医的一大特色。关于华夏“医圣”张仲景的记载寥寥无几,除了他的《伤寒杂病论》外,还有晋代皇甫谧(公元215-282)的《针灸甲乙经》序中有关张仲景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看病的记载:“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如果真的有一种医学可以在一个人20岁的时候就预言他40岁会出现的症状和死亡的准确日期,那么确实没有任何医学,包括现代医学,可以与之比拟。但是,这传说显然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这样的离奇故事,加上对其的广泛传播和相信,说明了在中国普遍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此离奇传说,与其说增添了中医的光彩,还不如说从根基上摧毁了中医理论的科学可信度。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科学各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创造了任何其他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科学成就,但这还不是古希腊留给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更重要的是她所创立的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546)和阿那克西美尼(公元前585-525)的自然世界观,毕达哥拉斯的规律观,留基伯(Leucippus,公元前5世纪)和德谟克利特的还原论,欧多克斯(Eudoxus,公元前408-355)和阿基米德的数理方法,欧几里得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博物学方法,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实验医学体系,……这个名单可以继续长长地列下去。 以上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在自然科学领域的贡献,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辨精神”,亦使得古希腊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贡献绝无任何一个其它民族可以企及。 古希腊对于历史的态度采取的是实事求是、忠实记录和认真分析。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图6-15)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395,图6-16)等历史学家,把历史的进程和结果不再归结于上苍的旨意,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历史可以这样结局,也可以那样结局,这并非上苍的旨意,而只取决于人。换言之,是人创造了历史,而非上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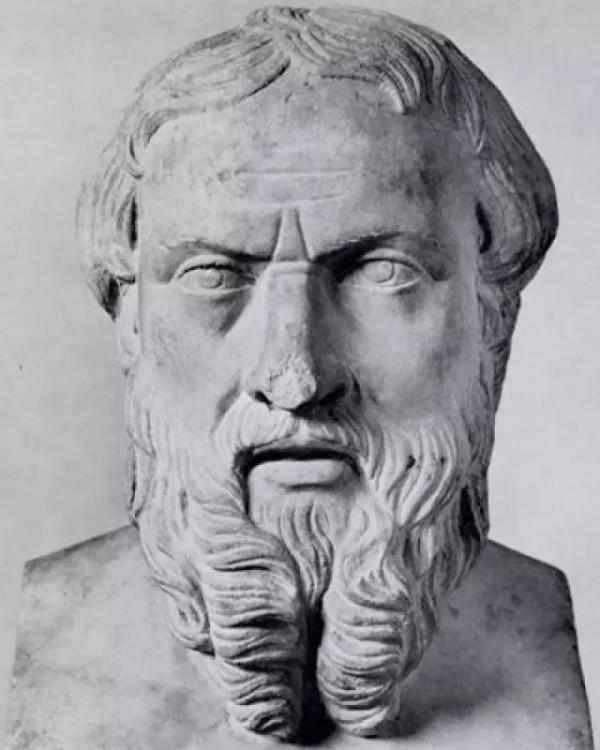
图6-15 希罗多德(Herodot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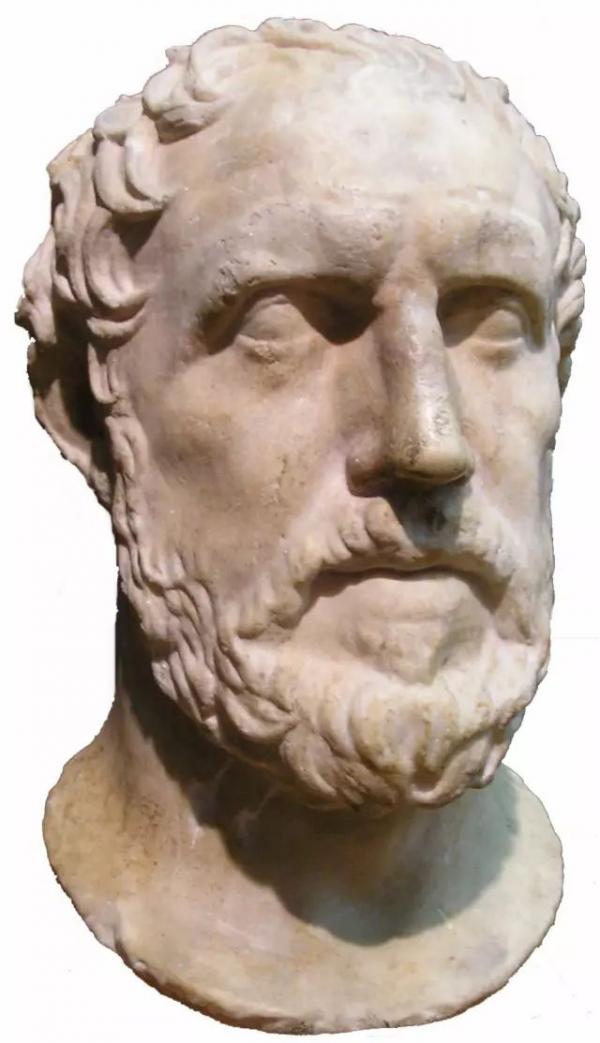
图6-16 修昔底德(Thucydides) 希罗多德对于荷马时期的历史和修昔底德对于古希腊古典时期的历史都采取了一种非常实事求是的方式和态度。尤其是修昔底德,他对历史事件采取了非常冷静的态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终败在了斯巴达的手下,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成了牺牲品。十分热爱雅典和民主制度的修昔底德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修昔底德并没有让自己的感情左右他笔下的历史,他冷静地记载了历史事实,分析了历史事件结局背后的原因。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修史中,神意和夸张都不见踪影,他们没有给神的意志和干涉留下任何地位,也杜绝了轻信和夸张。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修史奠定了整个西方修史的基础。实事求是的记录和客观逻辑的分析,成为了日后西方修史的特征。 古希腊的艺术也浸透了古希腊精神,闪耀着思辨的光彩。至今都无法出其右的古希腊雕塑,体现着真实和理性,一扫人间的恐惧和愚昧。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无一不洋溢着理性和激情。情节的跌宕起伏、对话的充满哲理、批判的深刻和讽刺的辛辣,必然导致悲剧的震撼人心和喜剧的发人深省,让古希腊精神直接在民众中引起共鸣。在下一章中将看到,古希腊的戏剧和剧场是如何平等地将这样的理念传递给了每个公民。 由于思辨精神在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历史和艺术的全面体现,古希腊对于法律和政治的深思熟虑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思辨精神在政治领域的成就必然是一个合理的政府和制度。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普罗泰戈拉在伟大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访问了雅典,伯里克利对其非常欣赏,并且邀请他参与了雅典的海外定居地Thurii(现在意大利南部)的宪法的制订。让哲学家参与宪法的制订,而这些哲学家都是科学家,这样的事实,我们今天听起来都会汗颜。还需要我们对古希腊的思辨精神做更高的评价吗?如果说古希腊社会是基于思辨精神的社会,那绝非溢美。政治家对于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敬重,不能理解为习俗,而是基于理性的行为,是一个崇尚思辨精神的民族的必然选择。 古希腊人不相信仅靠上帝就可以将正义带给人类,对于古希腊人来说,神和他们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缺点,也在艰苦地寻求正义。古希腊人需要神在道义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他们把正义的实现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把道义的重担义无反顾地挑在自己的肩头。他们相信,他们肩负着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神也无法分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上对于三权分立的设想很大程度上基于思辨精神:在直言不讳人的缺点的同时,也相信人的能力和智慧,在它们之间,必须有一种平衡和制约。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体现着古希腊的智慧、理性和勇气。柏拉图认为只有合格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统治者,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认为即便如此也必须要从制度上对于权力进行限制。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正是这伟大理性的实践。 古希腊在“思辨精神”指导下的哲学和实践,使得古希腊文明在实事求是和逻辑思辨中成为了人类思想的典范,在与科学和理性的结合中成为文明的指南,最终走向了科学和民主的广阔天地。 今天人类的科学和社会进步被深深烙上了古希腊的痕迹,携带着古希腊的基因。如果没有古希腊的精神传统,科学将不复存在,世界也将面目全非,人类将不可能拥有如今的精神和物质成就。 阿基米德在他的时代并没有找到可以撬动地球的立足点,但是阿基米德和古希腊给人类留下了伟大的思辨精神和理性的梦想。人类今天已经可以翱翔蓝天,过去对人类是遥远梦想的飞翔已经成为现实;人类已经可以治愈绝大多数疾病,很多曾经的不治之症已经成为历史,很多可怕的瘟疫已经绝迹;“顺风耳”和“千里眼”不再是神话,而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昔日可望不可及的“日行千里”已成了今天的微不足道;从时间上,人类已经可以了解遥远的过去甚至宇宙起源的那一刻,也可以预测遥远的将来宇宙的演变;从空间上,人类对于微观的理解已经深入到原子内部,对于宏观的认知已经达到宇宙的哈勃边缘;人类已经踏上了地球以外的天体,阿基米德所说的“立足点”已经找到;人类制造的航天器已经掠过太阳系最外层的行星轨道,向宇宙深空飞去,把阿基米德曾经居住过和扬言可以撬动的蓝色星球远远地留在了身后,那曾经仅仅是梦想中的天国,已经留下了人类智慧的足迹。 对于宇宙、世界、自然和社会,人类从古希腊开始有了一个准确无误的立足点,这就是“理性”,这就是古希腊的“思辨精神”。 我相信阿基米德无意真的撬动地球,而是要告诉我们,人类的理性将战胜无知和恐惧,没有什么比人类的理性更加伟大、更加值得赞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