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來自: 美國,加州 |
註冊日期: 2006-11-01
訪問總量: 56,820 次 |
|
| 點擊查看我的個人資料 |
|
|
|
|
|
|
 | 京華四記 |
| | 那是我小時候的北京城。
春
春極短。成不了一闕獨立詞。
一併破冰,一併桃枝抽蕾。蕊與蕊碰着頭,昵語不斷。一樹,兩樹,閒閒的開綻着,
眺首,又是爛漫又是空靜。三月的風是如意剪,柳梢裁得清巧生水,細緻的可漸漸
入詩入畫。枝枝蔓蔓的長袖,一蘢煙,一蘢綠,點點的善舞舒懷,都似是偷來的江
南。
“春雨貴如油。。。”小學子的窗下,誦聲朗朗。一個冬天的西北風猖厲,灰曠曠
的天,悄然而至的就是絲絲弦弦清彈出的一煙微雨。驚的不敢喘息凝視,生怕又是
一場痴痴的空算。
春天不是讀書天。春遊是天下喜事,總是勝過挖蛹,捉蒼蠅那類灰頭土臉的中隊活
動了。一挎軍綠書包,不必鼓鼓的塞滿鐵皮鉛筆盒,彈弓和田字格本。全換成麵包,
香腸和果丹皮,上衣口袋裡多足幾角零錢。
陽春的繁園舊夢。遊人如織的熱鬧石舫,昆明湖上的煙波點點金,亭廊牆寺上隨手
可讀“XX到此一游”的朝聖語。
只有後海,四角孤檐的佛鈴,懷唱清涼。
說是說的,偌大一座皇城,踏破鐵蹄,也只是人造湖與人造湖。後海,永遠是世人
戲謔京城的一個把柄。
一春。是月余短。象極了少年人的戀愛,無蹤無影的快,懵懂的連藉口都不需要找。
白楊樹一日比一日茂盛有神。打家具的,磨菜刀的,爆米花的,彈棉花的,一圈圈
吆喝喊買的嗓音,隔了幾幢灰樓,仍餘音赤赤的亮耳。
一季的肉票布票,都收在奶奶的大襟袷衣里。管是細盤算,還是粗盤算,都是轉眼
用光。日光長了,春光短了。
初春當了暮春過。任誰也尋不到春深的那條路徑啊。唉,這死短的京城春。
日曆牌上,很快就撕到了立夏那一日。不過是五月初罷,我想象中還是綠油油的壟
上春耕呢。
春,就是這樣。一個惶急的飛瀑躍身,已然無了去處。
剩下指尖微微滾動的珠水記憶。成苔成蘿,且去守了那一階的舊夢痕吧。
夏
夏是懷湍着急逝的雷陣雨的。炸雷和閃電從遠處的雲層里由遠及近的滾過,重兵壓
境,轉眼就到窗前。粗厚的雨柱急跌下來,一座城淹在汪汪的水裡,仿佛瞬間就失
守淪陷一般。然而不等你的驚惶緩過神,天兵天將就偃鑼息鼓了。
雨停了,彩虹就是降書。雲開霽朗,推窗一望,院子裡的五星花,喇叭花,攀藤結
喜,個個珍珠點頭,晶亮亮。
池塘的水滿了,蛙聲翠綠,粗莖的荷葉上,是永遠採擷不起的調皮彈珠。在攤開生
字簿的午後,【王冕學畫】里的那張圖畫是多美啊。卷了頁的語文課本,所有劃橫
線的生詞都曾是我們的惡夢。
家附近的低洼柏油路,潛積成一條小河。細柄葉子作舟,中間戳一個洞,另一柄葉
子作帆,船欄上蘸圓珠筆油;或者練習本上撕下一頁,摺疊成一條烏蓬船,河居者
是一溜巴掌大葉的白楊樹。雨天,捲起褲腳,穿着塑料涼鞋伺機淌水,黃昏的炊香
里,樂顛顛的偷跑回家,挨大人的罵,總是難免的。
然而,夏終究是個暴君,雷陣雨只是一個清涼的過客。
一群夏蟬藏在密葉叢里,不間歇的嘶鳴,象是亂事的糾察隊;天牛是慢吞吞的,卻
偏要把它們從樹上捉下來,比比賽跑,拿它們尋些樂子。
就算挨到黃昏,也仍然象是扣在燜油罐子裡。一把大蒲扇也解不了圍,蚊蟲嗡嗡叫
着群起圍攻,都是四面俯衝下來的小型戰鬥機。
重傷之後,奶奶的蠶皮枕頭和鄉下的涼蓆也救不了一夜的安寧。
三伏天,神降的救兵就是賣冰棍兒的老太太。街頭巷尾,推着一個白箱車,嘴裡的
吆喝聲就是神仙語:”五分錢,巧克力冰棍兒;三分錢紅果。。。“ 悠長又誘人。
所有熱蔫了的小孩都象是被魔棒點到,冰棍車前立刻就排了一條娃娃隊。
不富有的物質生活,倒讓我們輕易的握住了許多細小的快樂。
後來的後來,課本越讀越厚,我們的快樂卻越來越少了。
盼望着長大,盼望着所有成長的煩惱。
那一年的夏天,住在對面灰樓里的寧,開始和高年級的男生泡在一起打群架,成績
單上拖掛着一串紅燈籠。炎熱的午後,他就這樣懶洋洋的撥着自行車的鈴聲掠過去。
“我心裡有一個小秘密,我想要告訴你。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那是我內心衷曲 。。”
黑白港台明星照上的流行歌曲,被他低低的聲音唱成頹唐一片。
小學的畢業照里,他穿唯一的黑衣。我們天真的影像里,那唯一決堤而出的憂鬱。
我搬了家。某個夏天,榆錢樹的葉子仍然在陽光下青寥如舊,輾轉聽說他進了工讀
學校的消息。
那年同桌的他,離我漸行漸遠了。從此,為了三八線和半塊橡皮爭執的往事,在記
憶里都一筆勾銷。
所有的改變是因為夏天。
那一年的夏天過去了。我的童年也結束了。
秋
西風捲袖,秋是沾着些雨點來的。蟋蟀縮在青石縫和凋黃的草葉里,高一聲,低一
聲,瑟瑟的扯緊喉弦,涼意頃刻就壓城了。
天遠了。一竿日影移上了窗,從遒纏錯落的槐樹枝間,篩成細膩的光的蘿蔓,種匝
滿地斑駁的清輝。池塘里,卷卷的青衣蓮蓬,隔着一巷夜雨,都成了蒼蒼老旦。
遛早的老人,手裡提着木架的鳥籠,一擺一擺的從胡同里轉出來,迎面見到同好的,
遠遠的就吆喝一聲:“吃過了您呢?”彼此的口中噴着稀薄的白氣,仙人吐霧一般。
早點鋪子開得早。閒的人,抱着收音機匣子,坐定了,點一碗熱豆腐腦,一根油條,
半個晨時的光景就耽耽過了;急趕的人,抓起剛出爐的糖三角,或是一個白撲相的
豆包,撥着自行車鈴聲,一溜煙就沒了。
秋是叢淡墨的舊事。一勾白月,或是晌午的半枕艷陽,都細仃又拖着短匆的影子。
矮房檐下躲寒的麻雀,四合院裡一棵,兩棵空靜的棗樹,偶然的,一截蛙聲撲通的
跌落在井裡,撈不起。
街上起了白煙,是架鍋的糖炒栗子,一毛錢換半紙口袋,熱脆,好過冷梆梆的江米
條。紙包點心要挨到中秋,細麻繩一系,拎着走遍親戚。月餅是磨刀石,吃一口心
上嘴裡都要咯登一聲,要不得。討饞的是酥皮戳着紅印的豬油點心,一邊吃一邊簌
簌的落,總續有下文。
桑葚紫了,柿子樹紅了。秋是個清瘦君子,然而袖裡也藏了一兩件艷事,無法淡描
成。
郁達夫寫《古都的秋》,念念不忘的是“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
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卻獨獨忘了香爐的紅葉。
或者他就是要避開那熱鬧罷。偏要在那一櫞破屋下啜一杯茶,望一望天白。《菜根
譚》裡所謂說:(酉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
冬
冬是舊體小說。一節節,一章章,迴廊無數。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
寒,門楣階阼不斷。即至立春,以為秧苗綠過半截水塘了,豈知大紅對聯夭夭的貼
出去,正貼在一片冰天雪地的冷臉上。
冬是繁文縟節,還漫長着呢。
一爐炭紅的蜂窩煤球,或是兩三片單薄的暖氣管,都抵不住犀利寒夜的長驅直入。
橡膠囊的暖水袋,碎花布拼成的壓腳小棉被,暗綢底色,鍍亮紅牡丹的暖水瓶,密
密的冷如羅衾如十里雲帳。枕着一夜的夢楫,一夜呼嘯的風桅,驚濤不斷。
天明總是凍醒的。窗上是一層細白籮衣般的冰霜,一苞苞小花朵,紡晶瑩的紗。用
手指瑟瑟的塗開半畝花地,霜珠淌匯成一線水流。窗子外面,是青灰的一頂天,檐
下伶仃着一兩柱冰,一把枯枝卷在西北狂風裡,大風咆怒如揮舞層層刀片,小風尖
刻如揚起千萬細鞭。
行人就陷在一望無際的酷刑里。敦厚的大棉襖,黑條絨棉鞋,頸間重兵圍守的脖套,
粗毛線手套里的一雙手,永遠焐不暖。順風走,背後的風沙排山倒海,亂響成一片
金戈鐵馬;逆風走,莽撞的沙粒接二連三的跌進眼睛裡,走一步退半步,緩滯磕碰
如遇時局不利。
晌午有一簾薄薄暖陽,如一碗熱白粥上,凝起的一層油花米脂,少而精貴。一抬頭
的功夫,就散了影子。惆悵之際,滿眼望天望出去,一戶戶,一家家,小陽台上密
密扎扎的懸涼起,冬儲的大白菜,堆堆臥臥,卷卷墩墩,蓬然的一片片,無法收拾
的冬景。
雪夜深窗。一家人,圍坐一桌沸沸的羊肉沙鍋,少不得那幾片翡翠白玉,地瓜寬粉
條,細孔千篩的凍豆腐作湯底。黃燈之下,舉箸杯飲,瑣事叨叨如蘿如煙。一屋裊
裊的溫暖縈懷繞梁。細聽窗外沙沙風雪,小扣柴扉,莫不又是一程“風雪夜歸人”
般翻湧如浪的故事。
鄧雲鄉在《燕京鄉土記》裡寫:“京華憶,最憶是圍爐,老屋風寒渾似夢,紙窗暖
意記如酥,天外含吾廬。”莫不若此。
江南冬有窄窄的一船山水,沿岸人家,一樹嗡嗡的鳥鳴如籠。而京城的冬,鵝毛筆
揮毫即入詩,鋪天蓋地。對於孩子們,雪趣無數。堆雪人,打雪仗,昆明湖上滑雪
車,溜溜冰,踉蹌的摔一跤,不辜負這凍天凍地的三尺冰。
燕山雪花大如席。臘月深重如深宅深鎖,所有盛開的春事還在深深更漏的遠山更遠
處。
奶奶的廚房裡卻一日比一日熱鬧。臘八粥,青黃紅綠的熙攘在粗藍陶瓷大碗裡,親
密黏膩如一些小情侶,三三兩兩的露着頭;腸衣洗淨了,灌進肉餡,一節一節的扎
起尾巴,粗繩系起,晾在廚窗外,冷風一吹,懸梁刺股一般;刺猥饅頭排排兵似的
列在篦席上,手底一轉一點,兩顆咕碌碌的紅棗眼睛,立時傳了神;一張麵皮里裹
成蔥蘢美滿,油里翻滾一下,就是一碟金黃脆的春卷。
廚房裡轉一轉,口袋裡就多一點零食。面排叉,油梭子,彩色蝦片,變魔法一樣。
街上象熱油上的鍋,漸漸熱烈了。木炭鐵桶上一圈嘶嘶熱透的烤紅薯,香氣從街頭
傳到街尾;一架自行車旁圍攏許多孩子,擠出來的興沖沖,高高的舉着根冰糖葫蘆。
只有校門口空空,賣關東糖的鄉下人,也蹬着車回家過年了。
過年就像翻童話書,早晨從冰凌冰宮的夢裡醒過來,枕頭底下壓着一件花衣裳。乖
乖的在大人面前講兩句吉祥話,衣兜里的壓歲錢就已經鼓鼓。
廚房裡轉不開人,探着頭望一望:柿子椒是青紅燈籠,小黃瓜吊着碎花綴,蒜苔齊
刷刷,精神的綠制服軍人,紅肉鮮魚,碟碟罐罐。小孩子最討人嫌,奶奶自會拿個
搗蒜罈子,遁過來。三十晚上吃餃子,缺不了這味料。
一掛瀏陽小鞭,紅艷艷的年就開場。此後二踢腳,滿天星,雙龍戲珠,煙花璀目。
地上絮絮落落鋪紅一片,東揀西揀,又許多未開膛的。中間一折,聚成一堆,一根
香點過去,刺花嘶嘶酥酥的又是瞬即一場。
更小的時候,過年夜還有紙燈籠提。彩色皺紙上描山水花鳥,一根竹杆拎着,肚囊
里插只紅柄細燭。三五個小孩,頂滿天星斗,嘻鬧不到半條街,搖搖晃晃的一個閃
失,總有人懊喪的舉着一根空竹梢回家。
年過了。春還是深深庭院深幾許,滿眼只是西風吹雪。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海看柳。柳梢間薄綠初上,
春意漸長。回過頭去遙望冬,重重山,重重水,千重門外啊。
一本細細蜿蜿的小說合上了。錦繡或是凜冽,在幾十年後的某個冬夜裡蒼蒼念起。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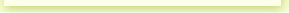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