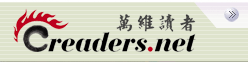期末大考结束后,我舒舒服服地潇洒了好几天,一直等到第四天才上网去看成绩,我越来越觉得胸有成竹,理当稳操胜券,因为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Dr.H 会给我B。进了网页一看,果不出所料,两门课都拿了A,这学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虽然我以前在教育学院和其它系所修过的18门课全部都拿到A,但《英语史》的这个A对我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这天又收到Dr.H的邮件,让学生自己到她办公室外面的盒子里去拿回批阅过的考卷和论文。我立马赶去了学校,到楼下时,四处一片静悄悄的,已是假期了。在美国考试分数是严格保密的,哪怕是个根本无关紧要的小作业,老师发考回时都要折起来,亲自递到每个人手上,搞得神神秘秘的,不像我们在中国时全班甚至全年级的分数和排名都要大张旗鼓地张榜公布,用以表扬先进,刺激后进。但期末时就不一样了,基本上都是学生自己去拿考卷,大家得在办公室外的盒子里好一阵翻找。我估计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老师不可能等着学生们一个个去拿,二是反正最后成绩已定,得什么都无所谓了,再好再歹也无法扭转乾坤,三是别人知道自己的成绩也无关紧要,反正期末过后,大家就各奔东西,绝大多数同学这辈子都不会见面了。所以有些人的考卷和论文就那样在外面放上整整一个假期。
上楼一看,盒子里满满一堆试卷、论文、作业,估计大部分人都还没来过,好些学生可能早已离校回家。一份份往下找,绝大多数都是拿A减或B,也有好几个C,甚至有一个F,估计这家伙可能惨了。很让我吃惊的是最牛的Carrie两样都只得了A减,但有两个同学都得了A,几乎翻到最后才找到我的考卷和论文。我两样都是A,而且是正宗的A,没有减号,倒是有点出乎意外。
回家后我仔细读了一遍Dr.H对我论文的评语:她首先称赞我写了一篇很棒的关于中文中英语外来词的短论文(excellent short paper), 接着对我所阐述的关于英语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第一语言的原因分析给与了两方面的评价:一方面她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英语比其它的语言更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从而一直保持有向前发展和升华的动力。虽然德语和英语算是同源语,但如今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我自己学了一年德语以后便彻底投降即是一个证据。另一方面,Dr. H也指出我可以从未来的角度进一步思考,有哪些方法可以使英语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尤其是同时扮演输出者和借用者的双重角色。原因是跟其它很多语言相比,英语是一种相当难的语言系统,特别是其读音和拼写的不一致性。我自己也体会到法文、俄文、德文,甚至马来文都有相当严格的读音、拼写规则,而英文的规则常常是有法不依,太多例外,常常让人不知所措,只能死记硬背。比如“ough” 有7种可能的读音,而读音为[sh]的拼写居然可以达到14种不同的形式!
Dr.H的最后一句话是: Great work this semester---good luck---keep in touch! 看到此,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整整四个月的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正应验了那句老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仔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想当初完全是一种上了贼船下不来,无可奈何而为之的情形,但最终却能得到这样的结果,不由得感叹有时候人的潜力真是不可估量啊!如果不去闯一闯,哪里知道刀山火海之后,也会有一片鲜花烂漫的瑰丽风景呢?这也好似人生,艰苦的经历常常能成为那些成功者所拥有的无价财富。
不过自从写了这篇论文后,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甚至是一种深深的失落,或是不甘。众所周知,虽然也有不少的中文词汇融入了现代英语, 比如说kung fu, tea, ginseng, kowtow, litchi, 等等, 但相比之下, 其数量仅仅是中文中英语外来词的零头的零头. 也就是说, 英文主要是扮演的是输出者的角色, 而中文更多的是扮演借用者,这种语言的强势与弱势一目了然. 当年“日不落帝国”的船坚炮利,使工业时代的强势语言变成了英语,如今美利坚的繁荣强大使英语更上一层楼。但我们想想看,全球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仅有3.5亿, 而中文为母语的有多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