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飞向自由 |
| |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杜克正看着那个鹰出神。
他叹了口气,看了下时间,已经过了晚上九点半。店里只剩下一对情侣在最里面的包间说话喝饮料。他拿起一张抹布,开始帮着小工做清洁。
杜克的小店坐落城市东郊,在老工业基地的家属区里面。一眼望去,全是80年代修的那种六层宿舍楼。本地的年轻人基本上都离开了小区,剩下的大都是杜克父母
辈的退休老人。还有一些把房子出租给做生意的,到处显得陈旧而冷清。这里曾经是盛极一时的西部地区最大的工业基地,电子机械纺织等大厂一个挨着一个。鼎盛
的时候,十几万工人加家属,总有好几十万人。现在大部分厂已经合并迁走,地盘都卖给了开发商。唯一只有杜克原来的厂还在,不过厂名改了公司,除了传统的动
力设备外,增加了不少新产品。
几分钟前,
那个叫小苏的女人给他打了电话,说要见面聊培训的事。没多久,杜克听到急急而轻盈的脚步声,一定是她。小苏是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以前也在杜克曾经工作过的动力车间,刚刚调到厂工会。工会最近为退休老人组织了一些活动,包括杜克被拉去当老师的艺术讲座。
杜克微笑着迎了上去,说道,“小苏,晚饭吃了没,要喝点什么?”小苏身材不算高但很匀称,穿了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剪裁得很合身。她的头发刚好齐肩,衬着略带椭圆的脸型,显得很恬静温柔。进门的时候,她脸色有点红扑扑的。
小苏说道,“我不想吃。这样吧,给我倒杯茶。我就站会儿,不耽搁你几分钟。”
趁杜克进去倒水,她认真地看了下店面。服务台在进门的左边,台上放了一个小名片盒,名片里面写着杜克的名字和订餐电话。此外还有一部电话和计算器,一个点
餐本。服务台背后空间很局促,也就够两个人并肩站着。站在服务台后面,要很小心才不会碰到后面墙上挂的玻璃橱柜。橱柜中间一格放着几包烟。下面一个格放了
几瓶酒,都是剑南春。最上面一格,是关公的铜像,拿着大刀。旁边还有个翅膀张开泥塑的老鹰。店堂中间被七八个像火车包厢一样的茶座占据。墙壁上拉着电线,
看样子好久都没有粉刷了,有些泛黄的印子。墙上贴了不少明信片,有天山,长白山镜泊湖,日月潭,阿尔卑斯山等等风景。有些明信片的旁边,甚至还看得到顾客
写的一行行小字。
杜克出来,把泡好的茶放在台子上,很浓郁的茉莉花茶香味在空气中里飘散开来。水很烫,杯子外面细心地垫了套子。他又拿了几个巧克力放在桌子上。小苏顺手拿了一个,剥来吃了。
杜克看着她一身的工作服,问道“今天你加班,还没有回家?”
小苏道“是啊。累得够呛。”
他问道,“最近怎么那么忙?”
小苏道:“生产那边今年据说想提到二十万台,比去年翻一倍。我们的高温假都取消,改发钱了。我呢是在排演迎七一的节目。”。
杜克显得很有兴趣的样子,道“什么节目?”。
小苏有些得意,“保密!你要想知道,到时来看呗。”
杜克不再追问,说道:“车间领导还是田佑军吗?我听说他提公司副总了。“
小苏道,“对,田总高升了。现在管车间的是刘进步刘主任。“
杜克说:“原来这小子上去了,不过也差不多。我记得他原来是团委书记。蒋仪群呢?“
小苏道:”蒋仪群出国了,她娃儿在加拿大读书,她就跟着去陪读了,不过她老公还在铸造分厂。现在管生产的主要是刘进步。辅助他的是陈兵,北航毕业的,我的学长。“
杜克说:“哪个陈兵,我不认识”。
小苏说,“你可能不认识,他来厂也就四五年吧。我听刘主任说你离开厂都不止十年了。记得我在车间的时候,以前用的一个操作规程还是你翻译的呢。我问刘主任,他说你是当年到美国培训的第一人选。后来因为你没去,他才去的。”
杜克说,“是啊,十二年了。”
小苏有点兴奋,继续说道,”我今天来是给你说个消息。你这几次的讲课,大获成功。是老王厂长给现在的领导提了建议,说要拨点钱支持,上面已经同意了。这样你也就不用老免费了”。
杜克笑了下。说道,“感谢老王厂长。不过其实没关系。这些听众都是以前我的叔叔阿姨,都是老辈子。他们不容易,给他们退休生活做点事我很高兴,他们捧场我也有光嘛。不用管我。我的生意还行,过得去。”
本来她想说,“你总要成家的嘛。”,话到嘴边,忽然脸有些烧,没有说出口。结果只是说道,“这次就是田总批的,今天他亲自把我叫去把文件给我。他签字的时候还说,哪天不想干了就到你店里来打工。他说很羡慕你自由自在的”。
“我羡慕他还差不多。在台上当大领导很风光啊,要啥有啥。我这是像井底之蛙,啥也干不了。”杜克说。
小苏仔细打量着杜克的脸型,忽然觉得他挺直的鼻梁显得很男子气。她换了个话题:“你讲课都不看讲稿!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呢?你现在还画画吗?”
杜克说,“艺术史大部分是高中大学里面自己看的,那个时候年轻,记得牢。而且现在讲起来,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体会大不一样。发现以前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忽然想通了。至于画画嘛,早就没画了。”
小苏说,“为什么?”问完她突然觉得自己冒失,有些尴尬。
杜克却不介意,半开玩笑的说,“画板都砸了。”他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砸了画板,然后把油画颜料都挤出来,涂了整整半面墙。妈妈在隔壁抹眼泪,不敢过来劝他。不过他从来没给别人提过,他有些奇怪为什么会告诉小苏。
小苏不再继续问,她的表情看起来像知道了答案。她肯定听人讲了那次事故,杜克想。
她低下头,把双肘靠在服务台上,漫不经心地把玩耳朵旁边的几缕青丝,好像在想什么重要事情。如此近距离,杜克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不由得站得笔直,他的双腿僵硬地靠着后面的墙上,嗓子居然微微有点发干。
两人都没有说话,有些冷场。杜克仰头喝水的时候,头碰到了那只鹰,顿时有了主意。说道,“嘿,你看我这只鹰,怎么样?”
说着他取下来,递给她。
小苏抬起头接过来,说,“不错啊,你捏的?”
杜克说,“不是我,我的初中的美术老师。刚退休在家,正在学。我去看他,就送了一个给我。”
小苏说,“你肯定是他的高材生吧。”
杜克说,“其实他的学生中间,画得好的很多,有些还得过国家的大奖。相比之下我获得奖真的就不算啥了。不过我一直最喜欢他。现在我们很谈得来,像老朋友一样。”
小苏把鹰翻来翻去的看,看到下面有一行小字:“艺术即自由”。她睁着一双很漂亮的大眼睛看着杜克。杜克解释道,”这是我老师的座右铭,读书时他就这样教我们。“
小苏把塑像握在手里,好像要带着飞的意思。说道,“你知道吗,你现在名气大了,大家都知道杜老师了。”
杜克点点头,说,“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小苏也没有看他,继续抚摸着老鹰,哼了一声。
小苏说得没错。现在走在小区,很多人以前叫杜老板的,或者小杜,一夜间都统一改成杜老师了。他本来人缘就好,这下更成了社区的名人。这让他觉得暖洋洋的,
好像心里有块冰在慢慢融化,宛如一夜春风吹过冰冻的小河两岸。有时晚上关了店,就算没有课讲,他也开始在网上看看类似的文章,脑子在想如果怎么讲更合适。
上次去的时候,美术老师也问他是否还在画画。今天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要送这只鹰。
小苏又问道:“你有没有想过把店子生意搞大些,或者做点别的?”
杜克说,“想过,怎么会没有想过。但是我不够有魄力,遇到该投资的时候下不了决心。说实话,最关键的是这个店该怎么做大,我心头无数。我好像从来在生意上都是这样的,比较被动。”
两人又说了几句,把下周五晚上上课的细节议了下,小苏告辞准备离开。
临出门的时候,她道,”杜老师,你答应的,下次给我讲讲以前的女朋友“。
杜克笑道,”我什么时候答应的?“
杜克有一个自由而幸福大学时代,因为他可以想也可以追求也可以做白日梦。不过最好的是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背着画板去外地写生,虽然吃住都很艰苦,但是很
快乐,还可以交不少朋友。他也到广场去画素描。有时还去公园给游客画人像,挣些零用钱。不过,他画的最多的还是他曾经追的那个女孩子。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恋
爱经历,虽然时间不长,而且是女方提出的分手。
和小苏聊的那几个人,都是原来一起进厂的一个车间的哥们。记得刚开店的时候,这些同事经常约着到店里来聚一下,后来渐渐成了一个传统。每当这个时候,人人
都很兴奋,像过节一样,甚至比过节还热闹。他们小小翼翼地谈着厂里的趣闻轶事,谁提干了,谁升官了,谁炒股发大财了,谁和谁在车间的休息室里面偷偷亲嘴等
等。乱七八糟的八卦什么都有。国家的新政策,厂里亏损还是赚钱,外国专家什么时候来,哪批产品又出口了并不是他们喜欢谈的内容。每次这种聚会,杜克更多是
静静听他们聊,心里很感动。
不过,年复一年,大家都开始成家,原来同年龄的朋友都有各自的事情,一起聚的时候就越来越少了。有些朋友也早就辞职下海,出国的也有。老面孔越来越少,新的越来越多了。
而自己的小店,平静,数年如一日。比起他的同事,他变成了事业的旁观者。有时在店里没事,他不由自主会去想像这些同事们的生活。比如今天他们又在策划什么
新产品,或者新的市场策略;也许在谈什么重要合同,在度假村和客户打高尔夫球,晚上在某个豪华的会所高谈阔论。这一切好像和他都没有关系,这让杜克感到淡
淡地失落。
他也看到年复一年,人们走进来的时候,谈的主题都不一样。这两年好像大家更多谈出国旅游,要不就是谁又买了新车,换了新房子。手机每年都在换,屏幕越来越
大,不说话的时候花在低头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多。电视上的选秀娱乐节目几乎占据了所有频道,除了他所在的这个区,到处都是新的楼盘一天天的成长起来。还有
新的高速公路,高铁,大桥。这些都好像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也看到新一代年轻人自信成熟的表情,特别极其发达活跃的商业头脑,和对高档商品的熟悉和品
味,跟自己那个时候的确不一样。只有自己所在的小区,好像时间停滞在了最风光的八九十年代,然后就越来越破旧下去。
他经常做同一个梦。他成了一个囚徒,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面。或者有时又是在汪洋中,他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上,呆呆地看着周围的人冲浪。冲浪的人大声地笑着,
一边随着海浪上下起伏。但每当这些人伸手来拉他,他的双腿却像被捆住一样,一步也走不动。醒来后他又如释重负的想,这个笼子也许就是店子吧,虽然平淡,但
是真实。至少不用每天面对着自己不喜欢的人陪着笑脸,或者担心什么时候有人会在自己背上踢上一脚。
难道笼子里面更自由,笼子外面有更多面具和约束吗?杜克想,那可真够讽刺的。这个世界有彻底理想的地方吗?
但有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就是他内心始终有座没有喷发的火山。虽然覆盖了重重的白雪,这个火山却从来不是真正的休眠,只是一直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合适的火苗。
杜克又把那张抹布拿起来,开始仔细地擦墙上明信片上的灰。
他一张张地取下来,用布轻轻擦干净,然后又仔细地用图钉订回墙上。每天的清洁工作中,他最喜欢的这个部分。特别是今天,一边回忆着和小苏的对话,他做得认真而愉快。
等到那对情侣出门,杜克才意识到应该该关门了。刚走到门口,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太从外面走了进来。杜克一下就认出了她。
老太太小声说道“小杜,帮我煮碗面可以吗?”
杜克道:“伯母,怎么这么晚还没吃?”
“我今天一天都在外面,错过了吃饭。回去不想麻烦我家老头子,他这几天心脏也不太好。正好出租车停在你店的门口,想着就在你这里将就吃了算了。”
杜克答应了,他回厨房自己下了把面。他站在厨房门口,一边看着锅里,一边看着老太太。她看起来穿得很得体,白天一定见了不少人。脸色显得疲惫而伤心。她正半闭着眼,不知在想什么。
不一会,杜克把面端过去的时候,说,“我看到新闻了。事已如此,您和伯父更要保重自己。”
她点了点头,说道,“他姐在跑上诉这个事,让我们不要管。”
“应该上诉,就是没作用,至少表明我们的态度。”杜克说。
她平静地说:“谢谢。他只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你看他做的都是小事,一点都不出格,他们居然给他安上‘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其实他很务实,甚至连理想主义者都算不上。但还是容不下他。你知道他在庭审完了,怎么对我说的?”
杜克叹了一口气,“他们不会报道的。”
她说道:“他扭过头来对我说:妈妈,不要难过!他们关不住我的心的,我是自由的!”。
杜克鼻子有点酸,说,“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
她说,“不用。支持我帮助我的好人太多了。我很感谢,我欠了好多人情。“她说着像又沉浸在回忆中。杜克也想起了往事。
她的儿子叫宋飞,和杜克从小认识。眼前这位宋妈妈就和杜克的父亲在同一个车间,家都相距不远。不过,他们俩个性格并不一样,所以小时在一起玩的时候不多。
宋飞跟杜克相反,从小没有半点艺术细胞,但是喜欢和人辩论,喜欢看历史和法律之类的书。他对人有时热情过度并且脾气倔强,为此宋飞的父母没有少操心。好在
宋飞很勤奋,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
杜克和他真正的相遇是也就是十多年前夏天,他们俩都还在读初中,被当时的气氛所激动,一帮同学在小区约着就一起到了市中心的广场。他们看着冒烟的汽车,倒
在街角被踩扁的标牌,和探照灯后面的制服。他们看着很多人在火光中奔跑,有些人倒下了,他们也混在人群中没命地跑。杜克心里只有一种惊骇和悲壮的情绪。
很多年来,这种的心情在他心里结了一个壳。那是杜克自己不愿意触及的地方。
一个月前听新闻才知道宋飞被抓了。了解之后才慢慢发现宋飞这几年做的事情,的确让人感动而佩服。杜克知道自己做不到。
宋妈妈早把面推开了,杜克看她没有吃多少,心里有些担心。
她忽然问:”你还画画吗?”
杜克说,“很久不画了。” 他指了下店子,补充道:“店子虽然不很忙,倒是很栓人的。”
她盯着他的脸,又看了下他的双肩,脸色显出又慈爱又温柔的神色,“也是,我理解。不过如果你想画,就把这些事情画出来。这是历史,将来一定会被记住的。”
又说到历史。这让杜克想起前几天的一个事情。一天早上来店子的半路上,他被晨练的老王厂长请到了家里。老厂长也在他的培训班上,因此拿出刚买的画板、颜料
画笔,还有供临摹的书、画册等等都一五一十的挨个向杜克请教,态度十分谦虚,让杜克真有些受宠若惊。老厂长文革前就是厂长,平时极严厉,但是为人非常正
直,全厂都很爱戴他。文革时造反派夺了权,老厂长被打成了走资派,在打倒了四人帮后才平反恢复原职。
后来两人聊着就说到宋飞。老厂长悲伤而感概地摇摇头,没有多说什么,只给他讲了当年自己在农场改造的往事。他说当时和一个中学语文老师,被打成“反对学术
权威”的,住在一个房间。这个老师年龄比他还大了十几岁,民国时期受的教育,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蝇头小楷。老师平时不爱说话。文革中间,白天受批斗,晚上
还要写检讨。其他人都是赶紧写完检讨,早早休息,已养足精神应付第二天的折磨。老师却非常认真,坚持用毛笔写小楷,一笔一笔专心地写,像在写书法的传世之
作,经常写到半夜。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现在看这些小楷都是精品。
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红卫兵小将或者造反派当然更不理解这些字的珍贵。造反派们往往听得很不满意,两三把就把检讨撕掉,命令他晚上再写。出人意料的是,他也不生气。老厂长说,他觉得甚至这个老师的表情很满足,好像在期待再写。
有一天老厂长终于忍不住了。问这个老师说你的检讨写得再好,不还是被撕掉吗?花那个工夫干嘛?
语文老师慢慢的说,我们已经被这个疯狂的时代剥夺了人身自由,他们可以打我,但是他们别想剥夺我的尊严和灵魂。我不是在写字,我是在和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对话,这是我活着的唯一快乐,这是他们限制不了,抢不走的。
说到最后,老厂长说,听说后来还真有人把那些撕碎的检讨偷偷藏起来,文革后一起给了他的后人。如果将来有博物馆,这些都是历史啊,无比珍贵。
现在坐在店里,听到对面的宋妈妈也说起历史,想起故事里面和老厂长共患难的这个语文老师,杜克感概万千。
宋妈妈好像明白了他在想什么。她说,“今天很多人打电话来鼓励我。特别是有个是从贵州,他曾经帮助维权的一个小学打来的。一个小同学给我念他们他们写的信。我听到‘奶奶不哭’的时候,我实在还是忍不住了。”说着,她忽然满脸泪水。
杜克赶紧到厨房去拿餐巾纸。等他出来,看到宋妈妈一头倒在桌上。杜克顿时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全身的血都在倒流。
等112的来了后,带头的警官在店里给她的丈夫打了电话。杜克问什么问题,警官说,“不知道,医生说像中风。我看她主要是情绪不好加上劳累过度。”这个警官也是本地片区,从小这一代长大,也认识她和杜克。“唉。”警官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所有的人离开后,四周都安静了下来,杜克把大门从里面锁上,一个人坐在屋子中间看着空旷的店堂。
他突然觉得头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以前他从没有意识到,不光他在笼子里,其实在孤岛外面冲浪的这些人,双手也是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着,只是在一个更大的笼子里转悠而已。而宋飞,就像一只想带领大家冲出去的仓鹰,虽然翅膀打湿了,但仍然不屈地在拼命飞翔。
杜克想,每个人的心中,不都有这样一只鹰吗?
从窗子望出去,外面又下起来了大雨。这时杜克心中的鹰开始砰砰乱跳,慢慢变成了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是以前从来没有体会到的,他感到,这就是他期待了半生的火苗,终于升起来了。
杜克一分钟也不能等。他站起来,快快地在店堂里走来走去,终于在墙上发现一个前不久刚刚贴的手机的海报。他把海报小心的取下来,大小刚好,他很满意。接着
去厨房找了一个擀面的板子,掂掂还不算太重。擦干净把海报翻过来贴上去,没有夹子,只好用胶带纸两头绑好。他拿着这个回到店堂,心情兴奋地像小时候妈妈带
他第一次去上课。
他把那个鹰的塑像拿下来,放在桌子的中央。又寻思着怎么配一个背景。正好在墙上找到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画面正中是一个优美的栈桥,坐落在一个峡谷上面,蓝
色的月色洒在桥首,有种梦幻的感觉,让人感到时光的久远和灵魂的净化。他把明信片放在鹰的后面,用个杯子立着。然后把整个店子的灯光全部打开,霎时间全屋
明亮耀眼。不过他的注意力,始终都全在这只鹰上面。
杜克在椅子上坐下,把刚做好的临时画板放在自己的腿和桌子之间。他摸了下光滑又洁白的表面,是那么地亲切熟悉。他伸出左手拿起笔来,很费力地才把笔杆握
住,然后下意识地在右手袖子上去擦。直到碰到空荡荡的袖管,不禁让他自嘲般苦笑了下,不过今天他不会再次停顿,曾经困扰的伤感情绪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
又把笔杆横过来,眯着眼睛往前看,好像在捉摸这只鹰的透视比例。迟疑了几秒钟,终于歪歪斜斜地画出了第一笔。好了,他想,总算开始了。
开始很生涩,但是杜克一点都不在乎,他一笔都不停。他所要的就只是一笔一笔地画下去,犹如那个语文老师笔下的小楷毛笔字。慢慢地,鹰的形状出来了。他越来
越流畅。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任何景物,在他笔下流动的,只是这几十年他一直在找寻,一直想倾诉的东西。
杜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奇特而满足的微笑,他仿佛看到自己长出了一对翅膀,从屋顶冲出了小店。在蓝色的月色中,他起伏翱翔。飞过道路,飞过排着队的汽车,
飞过一排排的路灯和一栋栋的大楼;他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一路划过广场的地面、古钟楼的尖顶和连绵的树梢头,安静而流畅地像在谱写一首乐曲。天色好像越来越
亮了,他看到儿童在看着他奔跑,看到其他的飞鸟都在后面跟着。接着他穿过田野,越过大河,掠过群山。抖落掉翅膀上的雨滴,他开始加速,后面广袤的山川原野
越来越小。他往上直接穿过厚厚的云层,看到了太阳就在上方。他笑着,坚决而直接往太阳飞过去。他在慢慢融化,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消散在了金黄色的万道霞光
之中。他感到温暖,他感到轻快,他感到自己无处不在。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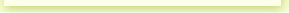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