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来自: 芙蓉之国 |
注册日期: 2008-05-03
访问总量: 2,983,062 次 |
|
| 点击查看我的个人资料 |
|
|
|
|
|
|
 | 唠叨唠叨几种野菜(下) |
| | 3)米蒿、野豌豆、紫苏、水芹菜、鹅莉菜
五月槐花飘香之际,也是米蒿和野豌豆上市之时。在我印象中,名字带个“蒿”字的野菜有很多种,只是各地的叫法不一致,若论到底有多少种蒿可供食用,估计是很难说清的。我曾吃过的是一种叫做米蒿的植物,有的地方也称它为白蒿。还有一种大名鼎鼎的蒿称为“藜蒿”,不知是不是米蒿的别名。这些蒿通常都有一种类似于茼蒿之类的清香辛辣气味,只是米蒿更浓烈些罢了。那些喜欢这种辛辣芳香气味的,就能将米蒿清炒了吃得津津有味,我就不成,我充其量只能接受茼蒿那种不很浓的气味。若论吃米蒿,我只能吃将米蒿剁碎后搅拌在糯米粉后做成的粑粑,而且只能吃半个,再多吃就是受罪了。这种米蒿在野外能采到,但是不是特别多,所以有些对米蒿情有独钟的,就在自家院子的墙角旁种上一小片。这种野蒿生命力很强,不用施肥也能窜得老高。又想起来艾叶,形状个色泽和米蒿都有些像,只是不知植物分类里两者算不算近亲。艾叶在民间主要作熏香用,据说它能驱蚊去毒,其辛辣芳香比米蒿尤甚。据说民间也有将艾叶捣碎和着糯米粉做成粑粑吃的,我算是服了。
(野豌豆-- 网络图片)
另一种吃过的野菜是野豌豆,这里我在网上找了一张图附上。我们这附近野豌豆特别多,出门不多远随便拐到某个角落,就能采上很多的野豌豆嫩苗尖。野豌豆尖味苦,不怕苦涩的也可以清炒一盘慢慢享用,不过我是不成的。根据别人的推荐,通常我将野豌豆尖采来,洗净,在沸水里浸泡5-10分钟,然后切碎,在太阳下晒干,做成雪里红。野豌豆雪里红只剩下清香,苦涩味基本上觉察不出。拿去炒肉,自然再妙不过,根本不下从商店里买的雪里红。
还有一种野菜就是紫苏,好像华东例如苏州一带叫做白苏。正宗的紫苏叶是紫红色的,也有的是绿色。紫苏在我们这附近的野外是采不到的,只能自己种植。紫苏生命力似乎很强,稍不慎就到处乱发,好在它也容易拔掉。紫苏叶辛辣味很强,因此通常是做调料而不是主菜,在我们老家通常是做鱼时拿来去鱼腥味,通常清炖新鲜活鱼时可以撒上一些紫苏,不过紫苏最“正宗”的吃法是用来做“糍粑干”的调料。这里糍粑干并非指糍粑或者糯米年糕,而是指鱼的一种烹饪方法。通常是将活鱼用盐(外加酱油葱姜蒜等)腌上10来小时,然后将这种半干半湿的鱼放平底锅里用小火煎,大约五分熟时再撒上紫苏,起锅时紫苏那种香味是一般人抵挡不住的。
水芹菜估计很多人吃过。我不肯定水芹菜算不算野菜,因为据我所知,国内的菜市场一直能买到它,有的农家也应该种植有水芹菜,只不过在野外潮湿的地段也应该能采到它而已,尽管在北美我似乎没发现哪里有采的。和紫苏差不多,在北美若要吃水芹菜,基本上只能靠自己种。水芹看着有些像西洋菜,其实味道比西洋菜强不少,至少是我觉得如此。西洋菜青味浓郁但香味不浓,水芹吃后却令口齿生香。水芹在中国栽培的历史够长的,最著名的记载莫过于诗经之泮水篇:“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思乐泮水,薄采其藻……”,以至于芹藻都成了有才学的代名词。正所谓“菜之美者,云梦之芹”,水芹和荠菜一样,我相信大部分同学和我一样都喜欢吃。
最后说个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菜:“鹅莉菜”,这三个字是不是这么写,我不知道,不过某位安徽籍贯的奶奶这么称它,我就这么写来着。当我问这几个字如何写时,安徽奶奶答道,因为鹅喜欢吃这种菜,所以称为鹅li-4菜。至于li-4字如何写,她也不知道……鹅莉菜野外到处都是;而且大家的房前屋后,说不定也长有鹅莉菜,特别是空调机旁或者屋檐水槽旁草坪的grass难长到的地方。在初春或者仲春的雨后,鹅莉菜一发就是一大簇。安徽奶奶说,鹅莉菜不苦不涩,从尖部处两三寸的地方掐断,洗净后用大火爆炒,就是一盘味道不下豌豆苗的鲜嫩鹅莉菜。这种野菜确实像豌豆苗的味道,只是青气味重得多,吃在嘴里感觉怪怪的。又想起就算鹅喜欢吃这种野菜,但兔子为啥不喜欢吃呢?这种野菜不popular是有原因的---自然,鹅莉菜已经被心狠手辣的我打入了冷宫。
4)荷梗、菱角、鸡菱梗
最后来段回忆,说说曾经津津有味地吃过、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荷梗、菱角以及鸡菱梗。荷花别称水芙蓉,从南国广东到北国黑龙江都有,就无需多说了。以前舅舅家有个小荷塘,种有荷花,每逢夏天,就是我们到荷塘边拔荷梗生吃之时,那些靠岸边的荷梗就最先成了我们的牺牲品。通常将荷梗揽住后,我们就顺势将它往上拔,除非少数折断的,一般都能拔出个大约一尺来长的白色荷梗来。这段白色荷梗是埋在泥底下的,洗净后生吃,清脆可口。在夏天,荷叶就是天然的遮阳伞;待荷叶晒得打蔫时,我们就将它制成帽子戴在头上继续抵挡骄阳,我们继续在烈日下暴晒,一个个黑不溜秋的。当然,拔荷梗时若有不慎,也有滑入水塘将衣裳弄湿的可能。偶有胆大不怕水脏的男孩子会背着大人们,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然后从污泥里掏出一大段藕根(见图,图片来自网络)。这种藕根直径大约1到2厘米,长大后就是莲藕。莲藕北美的亚洲市场都有卖的,价格从$1.99-$2.99/磅,倒不是很贵,只是那质量就不敢恭维了。初夏后南方的菜市场到处都有这种白色藕根卖。父母和亲友都知道我喜欢吃藕根,因此上次回老家我就吃了不少,大饱口福。比藕根更馋人的就是清香无比的莲蓬,六月份的长沙市场上就有新鲜莲蓬卖,价格一般视质量能卖到2-4人民币。小时候吃莲蓬,那苦味的莲心是一定要剥去的,现在吃莲蓬,那莲心竟是舍不得剥去,我总是和着青青莲子一起细细地咀嚼品尝,那苦味随后就化作津味甘甜,扑鼻的清香。记得前年我在Kenilworth Aquatic Garden游玩时,我还禁不起诱惑偷吃了两个莲蓬。Kenilworth 的荷花莲蓬密密麻麻,实在是太多了。
(Kenilworth Aquatic Garden 里的莲蓬)
有些纳闷,那时能干的舅妈怎么想不起用荷叶包糯米做糯米鸡吃呢?糯米饭里即使没有鸡肉猪肉可放,也可以加点豆类和酱油的。
南方长有莲花的水塘一般也同时长有菱角,甚至还有鸡菱梗。人工特意养殖的菱角一般称为红菱,很甜,大的差不多有乒乓球那么大。当然更多的是野生菱角。舅舅家附近野生菱角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较大,成熟后是深褐色或者深棕红色,如蚕豆一般大小,末端有两个很能扎人的尖角。这种菱角有一个很不雅的名字,记不清是叫猪婆菱还是叫鸡婆菱。另一种称为米菱,有四个扎人的角,乍一看就形如汉字的“米”字。这种菱角更小,除去四根菱刺,它比黄豆是大一些,但也没大多少。可能是因为这点,米菱通常只限于孩子们吃闹着玩儿,而猪婆菱则可以像红菱一样将皮剥去在集市上卖钱。在九十年代初,一斤猪婆菱角肉大约能卖两人民币,现在怎么说也得几十了吧。像我们手脚笨拙的,用小刀切一颗猪婆菱可能要一分钟,还得小心翼翼地莫切了手指,而那些训练有素的农家女,一晚上哗啦哗啦地据说能切出四五斤菱角肉。
  (鸡菱梗) (藕根) (鸡菱梗) (藕根)
采野菱和采藕根是不同的,虽然各自都烂熳得如一首童谣。采藕根必须下水扎猛子在污泥里面掏,采野菱则简单得多,因为菱角是浮在水面上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一根很长的竹竿,竹竿上绑一把镰刀,直接将菱角苗从水面下一两尺的地方割断就成了,因为菱角通常长在靠近水面处的地方。如果找不到长竹竿或者镰刀,那也没什么,用一根绳索系上一两斤的石头(or whatever),往菱角处扔,然后快速收回石头将菱角苗扯断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猪婆菱,其次是较嫩的米菱,最不受欢迎的就是老米菱,因为它不只是四个菱刺又硬又锋利,而且菱角皮也很硬,只能用牙齿咬,但稍有不慎那菱刺就会伤到手指或者牙龈,许多毛孩子痛得“哎哟”一声叫,只得恨恨地作罢。
很多有野菱的水塘还会有鸡菱。鸡菱和荷花是两种植物,鸡菱古时候叫做芡,其果实叫做芡实,很多药店都有卖。亚洲食品店通常有“菱粉”和“芡粉”卖。根据字面意思,菱粉就是菱角果实研成的粉末,芡粉就是鸡菱果实研成的粉末,只不过现在菱角和鸡菱卖得很贵,商店橱窗里的菱粉和芡粉无非是只加了少许真正的菱角和芡实粉末而已,要知道现在一斤去皮的芡实要卖一百人民币呢。鸡菱可能很多同学没见过,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果实像一个鸡头(见附图,图片来自网络)。鸡菱叶就如同大一号的睡莲叶,总是漂浮在水面上,只是上面长满了刺而已。鸡菱的茎,鸡菱的果实其实也是锐刺密生,总之鸡菱全身都是刺,全家都是刺。鸡菱除了果实外,鸡菱的茎,俗称鸡菱梗,像藕根一样也是上等的美味佳肴。因为这,采鸡菱和鸡菱梗时就得用长竹竿加镰刀,从水底处将鸡菱梗割断,不能用绳索加石头将鸡菱梗拦腰截断,否则就是浪费。
也许这世上最美丽最烂熳的歌谣就是写与江南女的采莲小曲和采菱小调,历朝历代文人都留有无数。像越女采莲这种形象都几乎成了历代文人解不开的心结,以至李绅都斗胆将浣纱女西施装扮成了采莲女西施。忽然想起了西洲曲,那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歌谣:“……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可以前哪里领会得这等温柔烂熳?那时只知在岸边拔荷梗,用石头绳子采野菱,连划到湖心的小船都没坐过,那不知愁滋味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永远地遗失了。
附注:总算罗嗦完了,有些出乎意料自己的耐心,最开始就准备码一两千拜特的。其实几乎所有的野菜都是中草药,包括这里提及的莲子,芡实,荠菜,水芹菜等。现在问个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因为猎奇才吃野菜?我们到底是在吃野菜,还是在吃中药?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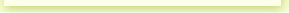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