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文學代表民族文學 ——論以金庸為代表的武俠文學之民族性(下) 馮知明 內容提要:中國的武俠文學能夠成為民族文學的代表,既是由其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性所決定,也是由其自身文學特點如通俗性和包容性以及現實意義的客觀要求所決定的。 關鍵詞:武俠文學 民族文學

三、武俠文學的通俗性及大眾意義 1、武俠文學的通俗性 從正統文學的觀點看,武俠文學是一種不入流的文學現象。但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出於對近代小說社會功能的某些誤解。黑格爾曾經指出,小說是近代市民社會及市民階層的產物。中國的傳統小說,一向具有兩種類型。一種可以稱之為雅文,產生並流行於士大夫及社會上層階級中。一種是俗文,這種俗文,無論是唐代敦煌的變文,宋代的話本和元明以後的章回小說,都的確與中古城市市民的宗教、文化、精神生活具有深刻的關係。
《漢書·藝文志》謂:“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這是關於中國小說起源常被引證的一段經典論述。我們可以從中注意到,在這裡,一方面指出了小說的起源的通俗性——來自市井閭巷的街談巷語、道聽途說。這正是小說作為通俗文學的起源。但另一方面,這裡又指出,這種俗文雖不足以見重於君子(“君子弗為也”),但耐人尋味的是最後一點:小說俗固俗,但“必有可觀者焉”,所以“亦弗滅也”。〔18〕
武俠文學恰恰也具有上述的兩點特徵。一方面,由於它的通俗性,似乎只能棲身於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流,而一向不見容於文學正統的殿堂。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不能不注意到它何以也“有其可觀者”。因而不但“弗能滅也”,而且竟擁有那麼多讀者。 在武俠文學的發展歷程中,俠客已有文學之傳統,文學便有俠客之懷抱,不拘小說詩詞,無論歌曲舞蹈,皆有以“俠”為題材,或者以“俠”為點綴的佳作。曹植的《白馬篇》描述幽并遊俠兒的英姿,寫遊俠兒在抵禦外侮中的表現;李白有《俠客行》詠戰國時的侯嬴和朱亥;近代名家張恨水寫《啼笑因緣》,出版商明確指出若要大眾喜歡,須加入幾個俠客,因此張恨水特意加入了天橋的武師關壽峰、關秀姑父女。 縱觀各類文學樣式,能夠成為當時文學代表,成為經典的莫不是最通俗的。唐詩宋詞如今等比較陽春白雪的文學,在當時社會中是廣為傳唱的歌詞。著名的文人作好新詞後,很快即有人傳抄至青樓歌苑中,供歌女們演唱,或者交給家裡蓄養的樂妓,供家宴上“聊佐清歡”,有些像現在的流行歌曲。像柳永這樣科場不得意的文人,甚至要靠為歌女填詞謀生。真正流傳到現在的是當時流行歌曲中最經典的罷了。其他如四大名著就更不用說了。小說的來源本來就是話本,如果沒有高度的通俗性,如何能流傳至今?通俗並不等於庸俗。誰敢說魯迅的東西不夠通俗?在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在語言習慣大變革的環境裡,那些半文半白、今日看來語法似不通的文章不是最流行的通俗作品麼? 2、武俠文學的大眾意義
與傳統武俠文學相比,20世紀中葉興起的當代新武俠文學,顯然具有更強的市民意識及商業性特徵。這兩點,都是由於20世紀小說社會功能的轉變。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近代類型的工商業城市在中國初次興起。在這些近代城市中,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傳播工具——新聞報紙及刊物。近現代中國小說的空前繁榮,實際上也是這種新的傳播媒介的一項產物。我們可以注意到,晚清小說名家如林琴南、李伯元、吳沃堯、曾樸的作品,最初都是在當時的報刊上發表的。而20世紀以來的各類武俠文學,如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古龍、諸葛青雲的作品,以至當代的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在成書之前都是以連載形式首先刊布在京、津、滬、港等通商巨埠的報刊上的。
報紙連載新武俠文學,是為了吸引市民讀者。這種商業性的市場需要,勢必強迫小說作者在寫作中滿足它。因之,他們在思想觀念上必須符合市民的心理。在趣味和格調上,必須遷就市民的審美習慣。在價值觀上,必須適應市民的評價尺度。而在情節上,又必須不斷地推波助瀾、出奇制勝、花樣翻新,以便吊住市民的胃口。 但是事情也還有另一方面。在20世紀的中國小說類群中,新武俠文學顯然是最富於傳統精神和情趣的小說。傳統文化太古老了,古老得有些讓新生代的年輕人望而生畏,有沒有一個文學的中介把這些古老深奧的文化通俗化,深入到大眾中來?就好比《紅樓夢》裡如果只有詩詞,那麼一定不會得到如此多的國人喜愛,只有在裡面把傳統文化的各種形式和小說結合起來,同時也讓別的文學樣式得到了全新的鮮活的生命力。 這一點科幻小說做不到,推理和言情小說做不好,歷史小說或許可以,但是狹窄的閱讀層面和被專業過於拘束的創作模式,在這方面也差一些。最好的媒介只有武俠文學。詩詞歌賦,談禪論道,武俠文學可以別開生面地引入進來;琴棋書畫,乃至古戲俚曲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因素,都可以自然而然融入武俠文學之中。其中字裡行間出現的唐詩宋詞,杏花煙雨江南,冀北西風瘦馬的意境,所表現出來的都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並非僅止武俠。 特別是金庸這位對中國傳統文化浸淫甚深的作家,在他的作品裡,我們處處可以體會到它帶有濃烈的中國傳統味道。譬如它的主題,往往圍繞着尊師重道、殺身成仁、捨身赴義、忠孝節義、急人之難解人之危、理之所在、身不由己等傳統價值觀念去設計情節。通過書中的懸念引人去追索,當人面臨忠與孝、情與義的尖銳矛盾時,他究竟如何抉擇與棄取?書中的思想意識,常常滲透着中國哲學的特質,如儒家的忠君、愛國、求仁、尚義的進取精神,同時又往往伴隨着道家以退為進、佛家無我無相的境界。道、釋兩家在新武俠文學中,往往以奇人異士的面目出現,其武功修為、人品層次甚至往往高於主人公本身。在金庸的小說中,武功原理的發揮,又往往藉助於中國的儒、禪、道哲學而施展,甚至幾首唐詩,也可以發展為一套精妙的劍術。 成功的新武俠文學中的“武功”描寫,往往也具有深邃的民族文學底蘊。新武俠文學裡的搏鬥場面,絕不是為打而打,為斗而斗,以嗜血為快樂,以殺人為目的。相反,斗的目的是“求仁”,是為了救世度人。早就在幾千年前,《詩經》中的戰爭史詩,就表現出這樣的特點:不注重直接具體描寫戰鬥場面,而是集中表現軍威聲勢。如《小雅·采芑》寫大臣方叔伐荊蠻之事,突出寫方叔所率隊伍車馬之威,軍容之盛,號令嚴明,賞罰有信。他雄才大略,指揮若定,曾北伐獫狁揚威,荊蠻因此聞風喪膽,皆來請服。〔19〕《詩經》戰爭詩中強調道德感化和軍事力量的震懾,不具體寫戰場的廝殺、格鬥,是我國古代崇德尚義,注重文德教化,使敵人不戰而服的政治理想的體現,表現出與世界其他民族古代戰爭史詩不同的風範。在《左傳》等體現儒家思想的史書中,也有諸多類似的描寫。時隔幾千年,能夠讀懂《詩經》,體會這種理想的人是極少數,讀武俠的人卻遍及全世界,但是這種“求仁”、不為殺而戰的精神同樣在新武俠中表現了出來,並潛移默化到武俠讀者的思想中去。 一種優秀的民族文學應該是能最大程度、最充分地對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加以繼承的文學。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種真正的民族文學不是一朝一夕的興盛,而是需要時間來檢驗,是能在中華血脈中代代相傳改進的。在歷史的長河中,許多文學樣式在波濤的浮浮沉沉中,或是戛然而止消失不再,或是雖然仍然存在,卻影響漸小,逐漸淡出文化視野與舞台。而武俠卻充分利用武藝和武德展現了民族精神中積極向上的一面,使文化色彩充溢於字裡行間,雅俗共賞,實現了對民族文化傳統的傳承和發展。 四、武俠文學的開放吸納性以及輻射性 
在我國古典小說中,“武俠”是與“言情”“神話”鼎足而三的一類,並伴隨中華文化千年的發展。《太史公自序》中對遊俠風範大加讚賞:“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20〕奠定了古之俠者的傳統形象。在文學家略帶理想性的筆墨下,塑造了一批“布衣之俠”形象。這一類俠客,很大程度上帶有文學家理想化的人格特徵,然而卻與當時世俗中“豪暴之徒”加以區別,為後來武俠文學的創作起到了導向作用。從東漢到明清這段漫長的歷史中,武俠文學不斷吸收民間傳說、志怪小說、傳統武術、言情、公案等元素,極大地豐富其內容與形式,並形成獨特的風格,在文壇上公開占有一席之地。 武俠文學本是一盤地道且原汁原味的中國菜,在煎炒蒸煮剁椒油淋的烹製中加入了來自他方新的創意與食材,吃的人越多,口味的分化就越細緻,於是花樣也就力陳翻新更加多變。在這個過程中,武俠文學展示了驚人的開放吸納性。 古希臘羅馬文學最負盛名的便是它的英雄史詩,雄渾博大氣勢非凡,充滿了驚人的想象力與對武技人力的充分肯定。《伊里亞特》裡通篇輝煌的冷兵器戰爭,極富先知性地奠定了戰爭這一文學最喜歡描述的經典題材之一。肉搏毫無疑問是當時人解決戰鬥最直接也自認為最光榮公平的方式,武俠文學裡也不乏各種規模不一的大小戰爭,從文斗到武鬥,從刀槍劍戟到飛針金鏢暗器甚至靈光內力劍氣,地點也紛呈多彩,不拘廟堂江湖青樓賭坊山頭街巷。武道的精魂在各式戰鬥中飛揚,人們的想象力在神乎其技的比拼中發揮至極限,人類的身體潛力也在肉搏中被想象力運用到極致。其實自新文化運動開始,西學漸進,武俠文學家們就不再滿足於舊武俠文學單調、程式化一板一眼的武功描寫,開始着重於在武中融入舞的概念,繪聲繪影於白描中潑墨而起,大大增加了比斗的藝術性觀賞性與娛樂性。 武俠故事從早期舊派小說開始,主角多要經歷一番刀光劍影鐵馬金戈,於是家破人亡之後流落江湖,遇異人鑽山洞揀寶藏學秘籍,間或談幾場小戀愛,最後寶器一揮消滅仇人揚眉吐氣成為武林終極大俠,如果忽略掉武打江湖這些武俠文學的明顯特徵,完全可以將之和歐美類型文學中的各種奇遇記、歷險記等小說並提。 各國的民族文學總是相通的,與武俠文學中的愛恨情仇,家國恩怨異曲同工的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的主題就是寫的主角阿基琉斯因仇恨而起的衝冠一怒,正如史詩第一卷第一句所說的那樣:阿基琉斯的憤怒是我的主題。因憤怒與仇恨所起的戰爭不僅席捲了凡人的生命,連天上眾神也深陷泥潭無法自拔。一部小說里可以包含眾多的要素,但是最流行最受歡迎的要素往往就是共同的那些。 金庸的十五部小說各不相同,同樣我們也能夠從其小說中看到學習其他文學樣式的成果。比如他筆下那堪稱驚世奇才的武林天驕金毛獅王謝遜,一生悲慘淒絕被仇恨的火焰不斷吞噬,悲憤怨毒半瘋癲的復仇經歷,就與美國小說名著《無比敵》里捕鯨船的船長亞海勃找大白鯨無比敵復仇的執念可以一比。《三劍樓隨筆》中金庸自己也兩次談到了《無比敵》,“為什麼說謝遜是從《無比敵》來呢?金庸介紹這本書的內容說:“故事是說一個捕鯨船的船長亞海勃找大白鯨無比敵復仇的經過,他曾被這頭白鯨弄得遍體鱗傷,還失去了一條腿,因此他如痴如狂的追蹤這頭山一般的白色鯨魚,他這種瘋狂的復仇欲望傳染給了全船的水手,終於造成了一個大悲劇……這正是謝遜和成昆的故事。”〔21〕但是金庸所吸取的,並不是《無比敵》的故事,而是使這個故事感動人的感情。金庸指出,這本小說反映它的作者的環境與心理狀態:“曼爾維(作者)由於接連的失望與挫折,對於社會與周圍的人懷着一種憤激之情。”這種憤激之情、“極度憤慨與拼命以赴的精神”,給予《無比敵》磅礴的生命力,而金庸就偷取了這一點火種,點了謝遜的靈魂。”〔22〕謝遜的靈感雖然來自《無比敵》,但經過金庸巧手創造後卻有着濃厚的中國韻味。甚至連結局都有着極大的不同,隱隱也透露了兩種文化植下的烙印。《無比敵》里故事最終船長亞海勃與大白鯨決戰,捕鯨船被掀覆,船長與全體水手葬身海底,所有人都同歸於盡。在強大的命運前似乎誰也不是勝利者。雖然亞海勃那種接近於瘋狂對命運的強烈反叛因這個結局給讀者刺去了驚艷一槍,但金庸卻顯然更贊同中國文化里的“恕”字,“謝遜指着成昆說:“成昆,你殺我全家,我今日毀你雙目,廢去了你的武功,以此相報。師父,我一身武功是你所授,今日我自行盡數毀了,還了給你。從此你和我無恩無怨,你永遠瞧不見我,我也永遠瞧不見你。”謝遜終被愛心與佛法感動,懺悔了自己的罪孽,放過了成昆,也在對仇恨的寬恕中獲得了自己的重生與心靈的平靜。 提到經典又能稱得上悲劇的武俠人物,金庸筆下不得不談到的還有一個,就是“南慕容,北蕭峰”里的蕭峰。他一直在掙扎着反抗命運強加給他的東西,卻在掙扎中一步一步離既定的命運越來越接近。這與古希臘索福克勒斯所寫的悲劇《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的亂倫悲劇有異曲同工之效。俄狄浦斯本是一個正直、誠實、勇敢的人,卻在命運的作弄下違反自己的本意,不自覺地做出了殺親亂倫的醜惡事件來一樣,他們都戴着命運的鐐銬起舞,未來卻無法預測無法擺脫,至死方休。 而從古龍的《楚留香傳奇》和《陸小鳳》中,我們又依稀找到了阿拉伯神話中的影子,女騙子的計中計行騙生涯,船王辛巴達的七次輝煌航海記錄等等,是如此相似。 正是因為武俠文學的吸納性,才能有它的輻射性。在影音占據主導地位的買方市場,武俠亦不再只局限於油墨書香的方寸之地,電視電影電腦的迅猛興起,各種武俠電視劇電影遊戲的問世,使得武俠文學迅速向外輻射延展。金庸經典的一再重拍各種版本的PK較量如火如荼,《臥虎藏龍》在奧斯卡和國際影展上獲獎,《仙劍奇俠傳》《天龍八部》等網絡遊戲的風靡無不印證了這一點。動漫方面也有香港版本製作的精美《神鵰俠侶》,央視近年來最走紅的古裝情景劇《武林外傳》就是以江湖為背景,客棧為主題展現各類小人物的嬉笑怒罵,其中雖不乏反諷隱喻,卻也足以證明武俠這種形式的深入人心。 武俠文學就像西方中世紀的騎士文學,有着它神幻浪漫之處,也有着它自定的套路規程,當然也有着不斷吸納融解的天性。你可以責備它的某些脫離現實之處,卻不能否認它的獨特生命力亦來源於一些本民族的閃光璀璨的東西。在越來越趨多元化的今日,武俠文學要尋求發展,除了繼續挖掘本民族文化的古典精髓,也需要不斷開放接受來自他方的新穎元素。同時也必將在開放吸收與吐納輻射的循環中繼續獲得自身揮灑的更大空間。 五、武俠文學代表的國民性以及對當代的警醒、教育和引導意義

1、中華民族的國民性與俠義精神的交融 國民性,即一個國家的人民由於生存的自然環境所決定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社會心理、社會意識,由此產生出自己穩定的、獨特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形態。這種結構形態反過來又使國民的社會心理、社會意識定型化,形成牢固的社會風俗、習慣傳統。兩者交錯影響,經歷歷史積澱,就形成為國民性。國民性包含國民的政治意識、自我意識、價值觀念、社會交往準則、最普遍的個性素質、心理特徵等。國民性是一個國家民族最主要的內在特徵。每個國家的民族特性,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它對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主體文化綿延完整的國家,幾千年的積澱使中國的國民性十分複雜。林語堂在《中國人的國民性》一文中認為,中國人的優點在於儉樸,愛自然,勤儉,幽默,而弱點在於忍耐性,散漫性及狡猾性。“這些都是一種特殊文化及特殊環境的結果,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來,散漫放逸是由於人權沒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於道家思想。”〔23〕複雜的社會環境造成“明哲保身,淡漠國事”的處世教條。 然而與林語堂的這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批判相輔相生的,卻是國民對於傳統文化中的英雄與俠義精神的肯定。無論是唐傳奇還是宋話本,活躍於民間的深受老百姓喜愛的劇目中,總是能夠看到“俠”的身影,在國民眼中,“俠”是重義輕生,捨己為人的代名詞,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格。尤其在中華民族亂世多於治世的歷史上,俠義精神更是社會中公道與良心的代表。明人陳子龍說過:“人心平,雷不鳴;吏得職,俠不出。”〔24〕正說明了強暴與不公的產生,使平民百姓期待遊俠的產生,成為賴以生存的社會力量。 2、武俠文學所代表的國民性 梁啓超提出了“小說改造人心,人心改造政治”的觀點,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25]的口號,揭示了小說在國民性改造中的重要地位。小說雖然走的是低端路線,但它具有“淺而易解”“樂而多趣”的藝術特點,容易被廣大的國民所接受,能夠在故事中潛移默化地升高國民的思想境界,故此被梁啓超稱為“小說界革命”。 在傳統文學中,武俠類或涉及俠義內容的文學通常是以小說或類似小說的形式流行於廣大百姓之間的。在《清代筆記小說類編·武俠卷》的前言中認為“在我國古典小說中,‘武俠’ 是與‘ 言情’ 、‘ 神魔’鼎足而三的重要一類。”〔26〕 而與其他作品中相比較,武俠中的人物多為販夫走卒,貼近民間,反映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與一些精英文學走在截然不同的道路上,能夠更真實更深層地反映中國最廣大階層的最普遍的個性素質、心理特徵,這也是受其受眾廣大的特點影響的。 在近代的歷史形勢下,由於西方文化的傳入,社會意識形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也相應地反映在武俠文學中。陳平原說:“在介紹及表現中國文化這一點上,武俠文學自有其長處。”〔27〕中國文化於此時的變化,以及相應的國民性的變化,都淋漓盡致地反映在了這一時期逐漸形成的“江湖”體系中,“在江湖世界中,人類社會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經濟鬥爭,一律被簡化為正邪善惡之爭,鬥爭形勢也被還原為最原始的生死搏鬥。”這就好比是成人的童話,“用俠客縱橫的江湖世界,來取代朝廷管轄的官府世界,這使得武俠文學中不能不帶虛擬的色彩。”但是這種虛擬的色彩又是現實社會的倒影,充分體現着武俠文學創作的當時當代的政治意識、自我意識、價值觀念、社會交往準則等,是時代的鏡像。如金庸《笑傲江湖》與《鹿鼎記》就影射着“文革”中的“個人崇拜”與“大革文化命”情境下各種人物的心態,具有當時國民性的代表意義。 由此可見,武俠文學隨着時代的推進,其代表的國民性以及表現國民性的形勢也在發生着變化。從單純的謳歌俠義精神到夾雜着對社會心理、社會意識的批判諷刺。正是因為現實的不如人意,“追求不受枉法束縛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此乃重建中國人古老的‘桃源夢’;而欣賞俠客的浪跡天涯獨掌正義,則體現了中國人潛在而強烈的自由、平等要求以及追求精神超越的願望。”〔28〕亦即在“予一人”的專制僵化的體系束縛下和宗族式的道德標準壓抑下,渴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在武俠文學批判人格與社會意識局限的同時,逐漸彰顯出來。 武俠文學以關注人性為第一要義,這是其國民性的根本體現。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後記中說“我寫武俠文學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在《多情劍客無情劍》的代序中,古龍說“只有‘人性’才是小說中不可缺少的”。在同類作品中也可以看出當時大多數武俠文學家們在作品中對於國民性格中較為典型的部分的書寫,而不僅僅是在文字與技巧間的提升。而由於人性的滲透與進展,武俠的世界不再僅僅是以往般單純透明的輕生重義,可以說武俠在人性上的進境,使其社會影響力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更多。 國民性中因封閉性而造成的猜疑、自私、圓滑、殘忍、懦弱怕事等精神殘疾,從嚴復、梁啓超、孫中山到魯迅、胡適再到柏楊、龍應台,幾代人痛心疾首地指責的國民性弱點,在武俠作品中都曾有所批判,但與教條式的當頭棒喝相異,武俠文學更注重人物在社會以及自身弱點中的痛苦掙扎,天人交戰後,在逆境中的升華,在國民本性中挖掘其公平、正直、忠誠、守信等潛在的優秀品質,使國人在閱讀的過程中產生深深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敲擊在深層的民族文化心理上。 3、武俠文學在新時代的意義 湯哲聲在《大陸新武俠的關鍵在於創新》一文中提出“第三次創新運動是一次‘文化融合’”,並說明“這一批在新時期成長起來的作家,人性追求和個性解放直接影響了他們人生觀和文學觀的形成,……將自己的觀念表現出來,將自認為最有價值的人生‘活法’展現出來”〔29〕這種對於個性解放的追求也正反映着當代國民性的嬗變。 冷成金認為:“文學的發展又是由民族文化運作的方式決定的。”〔30〕現今的中國社會從整體上追求的是一種法制健全的社會形態,公平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上,然而胡小偉在《俠義、正義與現代化》一文中認為:“一個現代化社會,我們把它只說成一個法治社會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道德層次的建設,人文科學用原是走‘社會正義’的,所以並不是每個人看了以後在實行中間如何這麼學習,而是要培養這種道義精神。”〔31〕而金庸本人也認為“武俠文學反映的追求個性解放、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互相幫助等,在當今時代依然有着積極意義。” 這種對於個性解放的追求,正是中華民族在新時代中融合新的外來因素,整合出的具有較強的兼容性的綜合文化的代表特徵。正如陳平原所說,極大的兼容性是武俠文學的特色。“全球化的視野必然給予我們新的感受。對於‘俠’這個純中國化的問題,全球化視野將展開怎樣的思考?俠的基於歷史人性的自由和正義,我們看到,悄悄地便成了更加廣泛的和平主義,突破民族界限和體制界限,而對武俠有了更加廣泛理解。” 因此,武俠文學因其思想性以及所反映的國民性的變化,在當今社會有其更廣泛的時代意義。在“天涯社區”上,有人是這樣指責當代中國人的“鼠目寸光,見一點蠅頭微利,蜂擁而上,淺嘗輒止,小富即安,為爭奪公共資源酣斗不止,挖空心思去轉移財富而不是創造資源。……犬儒主義盛行,逆來順受,信仰危機、生存危機籠罩下的中國人,沒有大師,沒有經典,只有多面人格,只有平庸,階層分明。……虛偽自私,妄自尊大,隨地吐痰扔垃圾,拖沓的生活節奏,損人利己視為能耐。”〔32〕誠然,這種說法可能有些誇大,但不能不說真實地反映了部分國民性,這種複雜的國民性,基於舊的社會價值體系被打破,與新的社會價值體系尚未建立健全的間歇期,要總結起來是非常困難的,但其根源卻是源於利益平衡的不安定性,而大陸新武俠的江湖卻正是這種基於我國國民性的社會的反映而構造的,鄭保純在《論大陸新武俠的當代性回應》中提出,“他們的江湖,不如說是由強弱不同的公司組成的一個共和國,決定江湖運作行動的,有除暴安良,也有愛國鋤奸,但決定性因素卻是利益與生存的衝動。所以這種江湖是一種結構性、平衡性很強的江湖……可以權且將之稱為由諸多因素混雜並發揮作用的後江湖。”〔33〕 因此在這種趨勢下,俠客不再是金庸、古龍、梁羽生筆下那種僅僅是正義的化身,大陸新武俠已經意識到了“俠客不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工具,而是可以寄託形而上的思考的本體,通過武道的修習與追求,通過江湖上的行俠,可以實現對自由的超越。”〔34〕這也是後江湖時代在中國社會重建價值體系的過程中,眾多作家在創作武俠文學中對於社會的反映與思考,更加關注國民中的個體性的發展,更加注重國民的內省,從而探索新的道路,在小說中潛移默化地影響着閱讀者的社會價值觀,由此,武俠文學以一種理想化的,類似於成人童話的手法,在反映現實的同時,實現着其在此時代對於引導國民性的新的道義之責。 結語:在當代中國文學集體低迷時,當代德國著名的漢學家顧賓先生用很情緒化的語言稱我們的當代文學是垃圾,不得不引發我們的反思。“……這個要看中國人﹐因為最看不起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不是我們外國人﹐是中國人自己。問題就在中國本身﹐中國人根本不給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文學什麼地位……很多中國當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國模式寫作。如果沒有外國文學,也許90%的中國當代文學都不會存在,因為沒有東西可以模仿。”〔35〕 我們引入大量西方式的文學觀人文觀,大量的本土文學作品翻譯化,而丟失了中華文化的根本,放在西方價值體系內,被人稱為“垃圾”就不足為怪了。今天我們在這裡復興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學式樣,建立我們的標準和評價體系,其先鋒軍,當數中華民族特有的無法複製的武俠文學。 武俠文學趕上中華文化復興的歷史關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們要讓整個世界都能看到,我們不僅有李小龍、李連杰和成龍,也有金庸、古龍和正在蓬勃發展的新派武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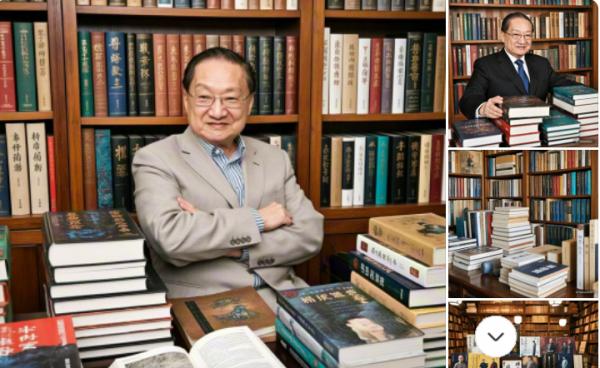
參考文獻: ①吳躍農:《新時期鄧小平第一個接見的香港同胞為何是金庸?》/《黨史縱橫》2004年第7期 ③金庸:《北國初春有所思》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 〔3〕楊叛:《回歸民族文化》/《今古傳奇·武俠版》2008年2月末,總第169期 〔4〕羅立群:《俠士、武士、騎士的文化異同及其文學比較》 〔5〕孔慶東:《中日武俠小說對談》 http://user.qzone.qq.com//622008504/blog 〔6〕溫瑞安:《九疑——應和馮知明武俠文學中九問》/《今古傳奇·武俠版》2008年3月下,4月下,總第171期,174期 〔7〕羅立群:《俠士、武士、騎士的文化異同及其文學比較》 〔8〕金庸:《神鵰俠侶》/廣州出版社2002年版 〔9〕溫瑞安:《俠義的根本在神州》 http://news.tom.com/2006-07-20/000N/13633283.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