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许良英 许良英老人家1920年生人,今年九十有二。老伴儿每年回去都要看望他们老夫妇,去年回来说,许伯伯犯了次心脏病,但很快恢复了。她去的时候许伯伯虽然还虚弱,不过精神状态不错,仍谈笑风生。我听后欣慰。但老伴儿又说,他们二老每日相互照料,生活上虽然有儿子每个星期来看望两、三次,但看来需要有人时刻在身边照应。看到他们生活极其俭朴,真有点心酸,好在两位老人精神上都很乐观。耄老之人能做到精神矍铄,很是敬佩。我们家虽然和许伯伯家关系非常近,可我怕他。老先生骂起我来一点不顾情面,劈头盖脸;我在他眼里不成器(的确如此)。我是越被骂就越敬佩这位老人。他胸襟坦荡,一生都在追求真理。打住!这种口气有点不吉利。就让我在这儿说点家常吧。不过有关跟政治沾边儿的事情请有兴趣的读者在网上查资料(多得很,他可是相当有名的中国不同政见者),这里不赘述。 家父和许伯伯同是浙江大学的同学,都是浙江人,先后加入地下党;建国以后都在中科院工作,1957年都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我们两家几十年来一直来往密切。不过许伯伯比家父骨头更硬!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拒不“认罪”。我老爸成为“右派分子”后“认罪”得到宽大处理――到安徽某地“思想改造”三年,回来后成为“摘帽子右派”,仍在原单位干活,当个普通编辑勤勤恳恳。但许伯伯被定成“右派”根本不服,嘴里三个字“我没错”。他本该被发配到东北某地“劳改”,他坚决不去。好吧,被“三开”啦,开除党籍、干部队伍和公职,而且还因“态度恶劣”被定为“二类右派”。他只能被遣返回乡,当了普通公社社员。妻子也离婚了。他妻子是我母亲的好友,也是浙江人,刚“解放”时遇到许伯伯;许伯伯这书呆子立即死命追求,不顾一切,说好不容易遇到志同道合者,绝对不能放弃。然而结婚后,我们的王阿姨(我们对许伯伯妻子的称呼)总觉得许伯伯太倔强,生活中总是吵吵闹闹。大概他们那时还年轻,不懂得相互谦让吧。许伯伯孤身一人遣返回老家,王阿姨便和他顺理成章地离了婚,自己一人带两个孩子生活。 后来我想,幸亏许伯伯拒不“认罪”,不然去了东北“劳改”非被虐待致死不可。可这位书生如何在农村“挣工分”生活?许伯伯的同学们,包括我父亲都拿出些钱来接济他。许伯伯在老家当社员的时候和科学院另外一学究(也是浙大校友)共同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我小的时候总能见父亲书桌上有许伯伯和那位学者翻译的手稿。不过从来没讲许伯伯。 “文革”伊始,许伯伯当然跑不出“牛鬼蛇神”的圈子。被批斗后他就喝“敌敌畏”农药自杀,绝不受辱。当然没死成。他后来对我妻子(当时是他的住院大夫)讲述了这段经历。许伯伯说,没死成被救过来可真受罪,不断地被灌,然后一个劲地呕吐。“啊哈,苍蝇吃了我的呕吐物都死了。这‘敌敌畏’还是真毒呀。哈哈哈!”您看看这位老人,就这么乐天! “文革”期间,大约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许伯伯和另外一学者翻译的《爱因斯坦文集》被上海某研究所的“造反派”们以集体名义发表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剽窃!许伯伯闻讯勃然大怒,他通过老同学们资助的钱奔走于北京上海之间为他和另外一作者争权利。那个冬天我第一次看到了许伯伯。他很瘦,一身不太整洁的棉衣棉裤,戴个栽绒帽子。他说话浙江口音很重、很快,我常听不懂。他来找我父亲接洽事情绝不废话,不喜欢聊天,所以总是来去匆匆。他的不通人情世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 有关《爱因斯坦文集》剽窃案实际上是不了了之。因为几年后“文革”嘎然而止,《爱因斯坦文集》重新出版,译者当然是许良英和与他合作的学者。 “文革”刚过,百废俱兴,一切事情都积重难返。许伯伯在众同学(有些已经是高官)想办法让许伯伯在某出版部门谋个临时工的位置。这样他便可以在北京合法居留,也可挣些钱果腹。巧了,刘宾雁此刻也在那儿干临时工。这是他们认识并交往的开始。 1970年代末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个急速变化的岁月。我从“上山下乡”的地方丧魂落魄地返回。在好心人胡耀邦的提议和邓小平的首肯下,“右派平反”(其实我现在对此有看法)。许伯伯政治“平反”后重回科学院工作后,他面临复婚的问题。王阿姨的意思是“我们是好朋友”,许伯伯则强烈要求复婚。但王阿姨不接受许伯伯的“风风火火,动辄发脾气”。许伯伯生了病,王阿姨去看望;事情峰回路转?可王阿姨不吐话。 这可不成!许伯伯的老同学们开始“围攻”王阿姨。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现在老俩口依然相濡以沫。 是不是许伯伯脾气改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许伯伯永远是许伯伯。嗯,他对我也太不客气了。我刚返城时相当反社会。动辄和父亲那帮老头儿老太太辩论,对他们每每表现出对他们执着的嘲笑;许伯伯也在其中。有一次许伯伯问我:你信仰什么?我不知为什么答成“‘克己复礼’”。许伯伯大怒,“脑子一盆浆子!读过几本书,还摇头晃脑!装模作样!不学无术!啧啧啧。”当时骂得我父亲都脸上无光。 可许伯伯竟然是我的婚姻介绍人。1985年许伯伯因眼疾要做手术。但术前查出心脏不好,且常有脑供血不足;于是住进神经科病房治疗。恰巧,有位女医生(当然后来是我妻子)正在神经科住院部干活。她在周末对她母亲讲,病房转来个特有意思的老先生;他的心永远朝气蓬勃。很早以前有部电影叫《夜半歌声》,男主角唱过首激情的歌,他竟然把这首歌在一盘磁带中连录八边,并一遍遍听。 女医生的母亲询问了许伯伯的名字,原来竟然是她的“老上级”!许良英在解放前夕是杭州市中共地下党学运领导人之一。而女医生的母亲当时就在杭州一所高中里成为中共地下党,上级就是许良英。 女医生的母亲忙去医院看望老上级,最后提出自己倔强的,老大不小的女儿当时还没对象,不知道许伯伯“有没有办法”。许伯伯当时认为自己可没办法好想,因为他从来对这种事情是个外行。但忽然想到,他的二儿子就是他介绍的对象,而且很成功。 事情是这样的。许伯伯的好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好友托许良英照顾一下。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后来许伯伯想,干脆让这个女孩子做我的儿媳妇吧。就把这意思和儿子讲了。许伯伯的二儿子吞吞吐吐,说“我们还不怎么认识呢”。许伯伯想都不想,“就这样定了。”后来许伯伯和我讲:“他们(儿子和那位姑娘)谈朋友都不讲话的。一起在屋里坐着没一点声音。每人抱一本书,看呀看,看得累了,就抬头相互笑笑。我真没见过这样搞对象的。怎么搞?怎么搞?”嘿嘿,搞得挺好嘛。 许伯伯急“老下级”所急,一下子想到了我。“这小子脑子一盆浆子,但心眼还不错。”于是托老伴儿王阿姨来“介绍对象”。我和妻子就这样认识了。现在许伯伯想到介绍对象这事情就自豪地说“我介绍对象的成功率是百分之百”。他一共就介绍了两个,一个他儿子,一个是我。 许伯伯现在宣称自己不再是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他说过去一直是,即便被打成“右派”也没有改变初衷。他说,他本以为自己不会看到“中国大陆的解放”,认为自己会壮烈地死去。当时他公开的身份是研究生,导师是王淦昌。为了掩饰自己不学习,许伯伯常在桌子上放些尼采的书。王淦昌见到这些书相当的恼怒,但也无可奈何。他不知道自己的学生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尼采的信徒”。许伯伯说,“文革”之后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六四”之后彻底决裂。“我可能还会修正自己的思想。但一生追求真理不会改变。”他总是这样说。 多可爱的老人。我想起1969年春节,父亲的秘密档案被非法查阅,当即成为“国民党特务头子”入狱(他当时“卧底”)。马上我们被“扫地出门”,仓皇搬家时,要住进我们家这几间房子的“造反派”拿着一个清单反复核对。那上面都是公家家具的清单,发现少了个钢丝单人床。但我们搬家时除了几平板车书籍,其他几乎一无所有。事情后来被父亲翻出“谜底”。1950年代,许伯伯来我们家作客,看到这钢丝单人床没人睡,就要立即搬走,说自己的儿子还没个床睡。我父亲劝阻,许伯伯不以为然,就这样把床搬走了。 我还想起方励之先生躲起来的那段日子,许伯伯斥之为懦弱行为,并毫不隐讳地批评。 那年冬天,他向一老同学索求一个取暖炉子;对方刚一犹豫他立即扬长而去,搞得人家不知所措。 啊,许伯伯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什么不同凡响的人,但他绝对真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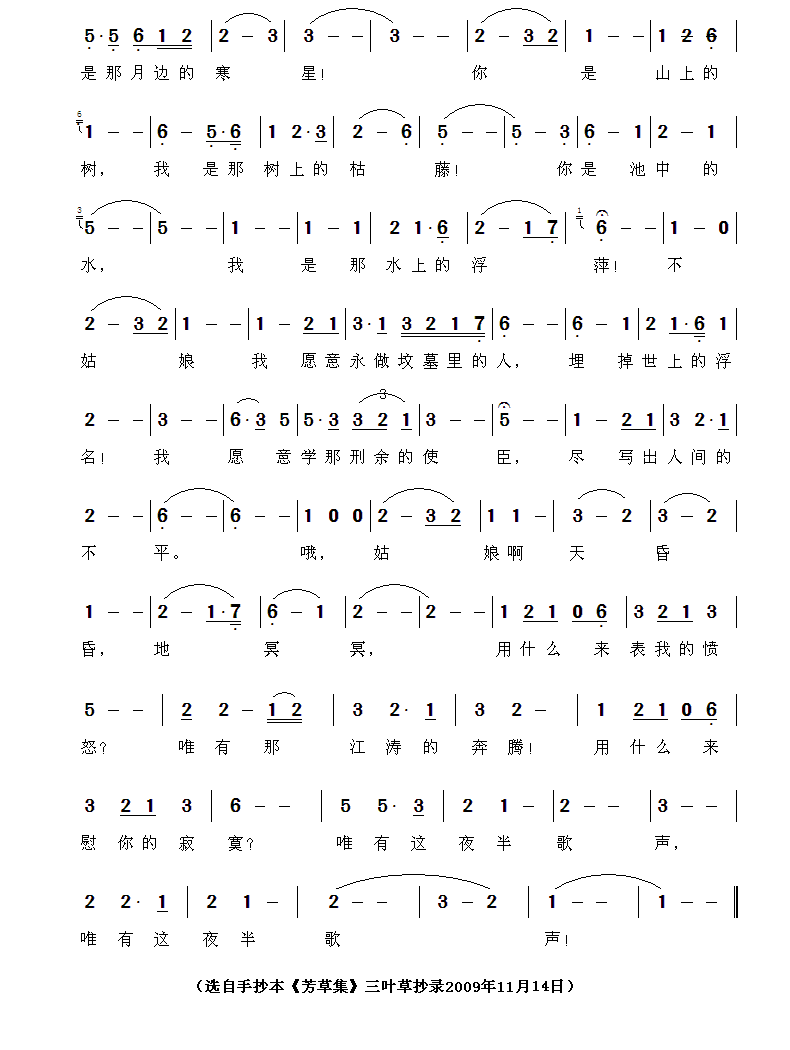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