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通向自我的道路——侧记19 范学德
我们的旅游大巴在群山中前行,大山沉寂。但车内,陈瑞琳主持的“巴士论坛”气氛火热,一个接一个人发言。几个人讲话后,我有所感,要求也讲一讲,拿过话筒,我说了以下的话。 大会上我在限定的五分钟内主要讲了一件事:对于我来说,写作是我走上上帝的一条路。现在可以讲下一件事,写作同时也是我通向自我的一条路,走入我的过去,我的现在和未来。 因此,我,这就是我写作的立足点,什么群体、民族、世界,这些对于我来说都太大了,尽管他们与我息息相关,但也只能在与我的关系中去观察,去思考,去书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要摆脱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对我的束缚,我就是我,一个自由的独立个体,我只能从此出发,并且,走我自己的路。 我被那些意识形态害苦了。从小到青年时代,雄心太大了,动不动就想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解放全人类,要振兴中华,但在那时候,除了身边的黄种人,我甚至都没碰过一个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长大了更发现,只要领导一句话,你就连人民都不是了。 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就要超越人际关系,进入天地关系中。德国有句名言,据说是黑格尔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当我真正地仰望星空,举目望天后,我才明白了,我这个从古至今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它是我的主赐给我的。除此之外,世上所给与我的一切价值,都无法构成永恒的价值。) 我的自我是复杂的,多面的。简单地说,在我的灵魂里面,有一个黑暗的我,也有光明的我,它们一直在争战之中。写我,就不能不写那个黑暗的自我、罪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件事令我深深困惑,就是许多老干部和文化人、知识人,他们纷纷讲四人帮怎么迫害了他们,但却没有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迫害别人的?在1957,还有更早,你们是怎么样检举、揭发、批判、斗争别人的。 成为基督徒后,我更意识到,说别人容易,那你范学德自己呢?难道你没有主动地参入十年浩劫,成为那些罪犯的帮凶?我不能说没有。因为当年上中学时,我也参加过批判牛鬼蛇神的学习班,并且一次由于无意失手,用温热的炉钩子烫了文革前的副校长一下。 我问自己,毛没有摁着我的手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帮我举起炉钩子。我做的,是我做孽,是我犯了罪,成了黑暗势力的同伙。 于是,我不断反省,忏悔,认罪。在世纪之初前后,我集中精力写下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一开始在台湾的《宇宙光》杂志上连载,后来结集在美国出版,书名叫《梦中山河—红小兵忏悔录》。全书的焦点就在一个问题上,我是怎样参入了这场浩劫,为什么会那样?我写出我的忏悔。承担起自己的罪责。 由此,写作就是悔改,它是我通向我的罪我的一条路。 我还要写我的赞美和爱。 疫情开始后,我眼中看到的都是黑暗,很可怕。那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上帝,你还在爱着我吗?或者,像古代诗人的询问:主啊,求你显出你爱我们的凭据! 每日散步,我走进了自家附近的大野地里,有时一走两个多小时。在途中,我看到了日出日落,看到了青草死而复生,鸟儿唱着歌飞翔,小龙虾群挤在一起,是做爱吗?求爱的加拿大雁欢叫着在空中起舞。雁宝宝跟着爸爸妈妈在小池塘里漫游,小鹿似乎熟悉了我的味道,在距离我三五米的地方吃草,它们居然还吃蒲公英,懂得药膳。小乌龟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伸出头来看我,但不会像某些我的东北老乡那样问:“你瞅啥呀!”我们就这样相互注视着,风过,阳光过,但时间静止了。 这一切让我感悟到,我被爱着。就像两首古老的赞美诗所唱的那样:“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仍在掌管。”“清晨复清晨,主恩日更新。”于是,我漫步,我欣赏,我祈祷,我赞美,言辞不足以表达时,我情不自禁地歌唱,偶尔还会舞蹈,只为你歌,只为你舞。 回到家里,我写作。 2023.7.15记事 完成于2023.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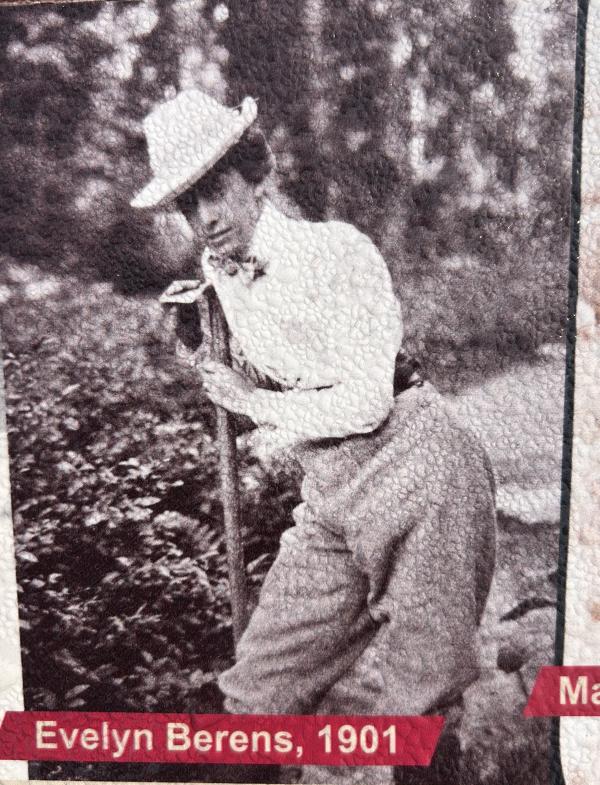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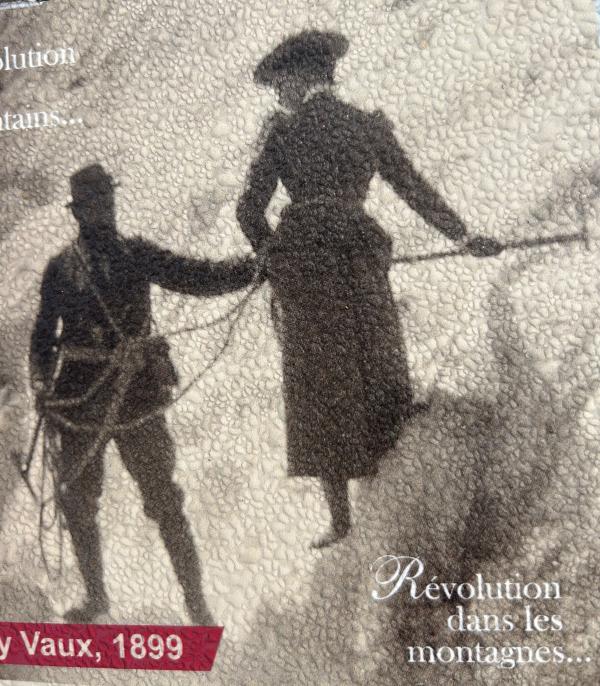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