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16
作者:范学德 | 图:作者亲自拍摄
导读:一生,一死,野草居然如此自我了断,自杀,一直令我着迷。
上午芝加哥北郊下了场大雨。中午时停了一会儿,下午又下了一大阵子。把个天和地都洗得干干净净,蓝天爽,绿地爽,连落在地上的玫瑰花瓣,也爽。车道上的脏东西都被冲走了,路边的小沟成了小溪,哗哗地流,到拐角处,慢了下来,汇成个小池塘,水一时下不去。 黄昏,我载孩子去小镇里的文化艺术中心学钢琴。孩子开始学琴时,我到琴房旁边的爱德勒公园中散步,公园里有一个露天游泳场,还有几块大片的草地,与小树林或连接,或隔离。我沿着树林边的沙土路走,走了不到半里路,拐进了一个小树林中,再往前走不远,路被堵住了,一棵大树横在路中,旁边还有一棵小树,大树有两人抱着那么粗,被摔成几块断片,树心,空了,就剩下了黑乎乎的一层表皮,但那表皮也够厚的,至少半尺。看来,这棵大树早就死了,只是今早的大风才把它刮倒。它倒了,砸断了旁边的几株小树,把附近的野草和野花砸个稀巴烂。

走不过去了,回头走。顺着一条小路,往另一个公园走,这个公园叫独立园林公园 (Independence Grove),特大。与爱德勒公园接在一起。黛斯普蓝河,从两个公园的旁边流过。 黛斯普蓝河涨水了,水面灰乎乎的,几根小木头在漂流。走了几百米,到了公园西侧的外面,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遮住了流在林间的黛斯普蓝河,也遮住了独立园林公园,眼前出现了一大块空旷的荒野,上百亩的坡地上长满了荒草。高处,大树连成了墨绿的一线,低洼处,集满了水,蛙声阵阵,还夹杂着小鸟欢快的叫声。
茫茫的野草抽穗了,穗子好像古代将军头盔上的翎毛,在晚风中轻轻地摆动,这一动,那黄褐色的草穗就连成了海,金色的太阳照在金色的大海上。看近处,草穗如浪,略微弯曲地摆动,望远方,一排排的浪潮,此起彼伏。 还有一些野草正在自我交战之中,新叶已有半尺高了,但旧枝还硬撑在那里,摇摇欲坠。新叶嫩绿,旧枝枯白。这些旧枝都挺高的,是这些野草去年抽的梃,一个冬天过去了,现在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杆,它已没有任何生命了,但还不肯倒下。 眼下已经是暮春,它们倒下去的时候就要来到了,再有一两场风雨,它们就会倒了,成为新叶的肥料。 更多的是另外一些枯草,一两尺高,入冬后,很快成了焦黄色,细细的,在寒风中哆嗦。雪稍微大一点,就压弯了它们的腰。有一些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断了,垂在那里,风一摇,它摆来摆去,仿佛断肢。春天,一个早上起来,一看,这些枯叶都断了,一些嫩绿的新芽,从野草的根部长出来了,迷人。 一生,一死,野草居然如此自我了断,自杀,一直令我着迷。 猜不透这谜。

回头走。刚走到可以看到黛斯普蓝河的地方,我突然站住了,五六米处远的河中间,一个小家伙正逆着水向前游,是野鸭子?不是,它的头像老鼠或者松鼠,啊,肯定是水獭,没错,是它。河中心的小岛边,正有几根木头弄到了一起,它干的事!水獭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加速逆流而上,头露出水面,两边的水,向东西分开。不一会儿后,它钻进了水里,只在水面上留下了分成东西的那么一片水,水不断地向东晃动。水獭又露面了,向小岛继续前进,直到消失在小岛旁边的几块木头之中。 回来的一路上,一会儿我想着野草的自我了断,一会儿想着水獭逆流而上奔向自己的家。 载儿子回家时我问儿子,这个文化艺术中心有多少学生,他说,有三四百吧,我也弄不清楚到底多少,回家上网查查吧。再往前开了一段,就要到一块天主教的墓地了,黄昏时,那里经常有野鹿出没。我对儿子说,注意,看看有没有鹿! 隔了一会儿,儿子说,爸,两只鹿! 两只小鹿站在树林的边上,西边的太阳落山了,余光洒在了鹿身上。 2007.6.4 芝加哥 2017年7月修订
(此文收入了我在中国出版的《细节中的文明——寻找美国的的灵魂》一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当当网等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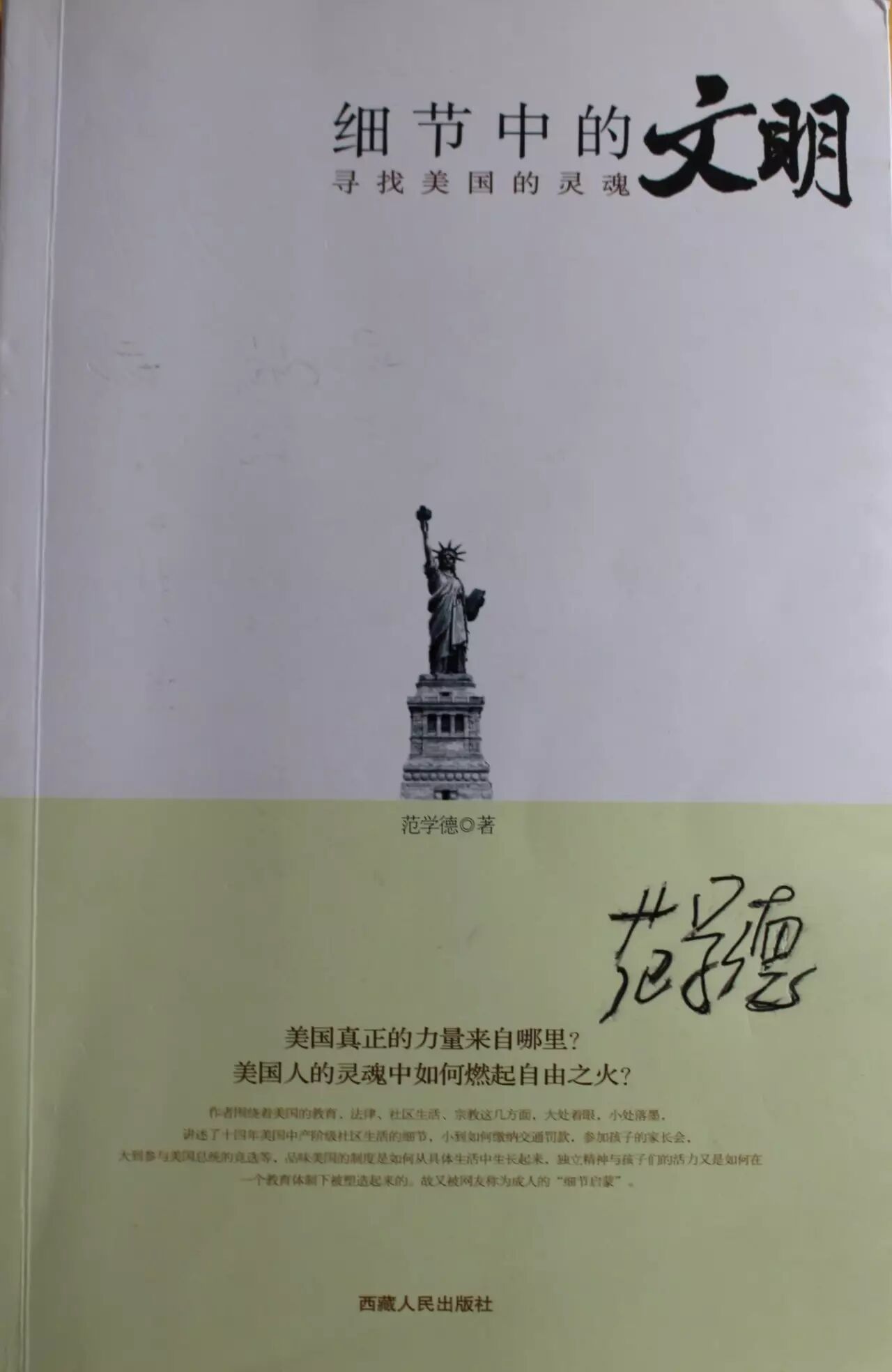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