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礼拜天,我去活水福音教会布道,当天发了一篇文章:“病毒,别狂傲,明天我要去传好消息。”
文章发出后,一位名叫“徐见明”的网友留言:“建议您下次布道务必带上口罩,避免成为超级携带者。” 看来,让我感染上新冠病毒他还不满意,还盼我“超级携带者”,害其他人。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恶意”、灵魂的病毒。
我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恶意’具有某种群体性、季节性,在最近我公众号后台的留言中,我甚至看到了他们语言的一致性。” 以上的话,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杰作的旁证!

舍斯托夫曾经这样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不仅在俄罗斯文学,而且在世界文学中,都是一部最有名的作品。”(注一)
在我看来,也许应该说它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一部中篇小说,并且,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人类哲学著作中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因此,它才能被视为存在主义最宝贵的文献之一。
罗赞诺夫说:“《地下室手记》的每一行都是重要的,几乎不能把它归结到通用的公式里;同时,任何一个思考的人都不能不去讨论其中所发表的见解。”(注二)
1864年,《地下室手记》在俄国出版,二十三年后,尼采看到了该书的法译本,他异常兴奋地说:“一种血统本能(否则我何以名之)直接呼叫出来,我的欣喜超乎寻常。”(注三) 罗赞诺夫认为:“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并且最详细地批评了这样一种思想,我将其概括为理性专制主义,这种主义就是这样一个愿望,即借助理性建立人类生活的如此完善的大厦,以便它能给人以安慰,结束历史,根除痛苦。对这个思想的批判贯穿着他的所有作品。”(注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判是以反思人开始的。 “我是谁?”这是人生存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首要问题。
古希腊有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
那么,我到底是谁?《地下室手记》一开篇就问了这个大问题。 “我是谁?”答案:“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注五) “病人。”对人的这个定义令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福音书,那上面记载了耶稣的一段话,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注六)
“病人”与“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明白地说,但看他的整个小说,他所谓的“病人”,就是“罪人”。

《地下室手记》的开场白是“我”的大段自白,其实,整个《地下室手记》,就是“我”的自白书: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是一个不漂亮的人。我相信我的肝脏有病,但是,关于我的病,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在我体内骚动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请教医生,绝不——尽管对于医药我有某种敬仰。再者,我极其迷信,非常迷信以致敬仰药物(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致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拒绝请教医生是出于恶意。这,或许是你不懂的。好,就让你不懂。当然,我无法解释这种恶意所伤害的究竟是谁,我十分了解,不去请教他们并不就是‘惩罚’了他们。我也十分了解,这样做除了自己之外,伤害不到任何人。但我仍旧由于恶意不去请教医生。我的肝脏很坏——好,就让它坏下去。”(第23至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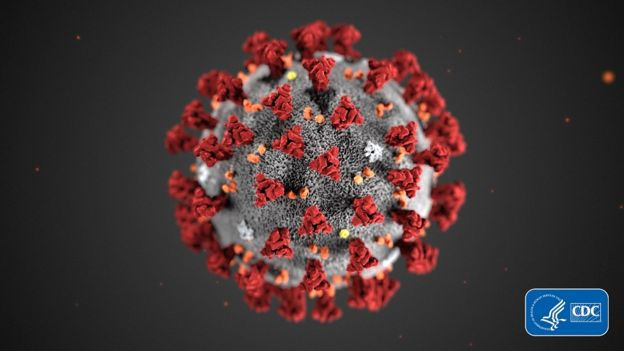
为什么说这个“病人”就是“罪人”?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不仅肝脏有病,心里也有病,这个病的名字叫“恶意”。
“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
“恶意”,这就是“罪”、心灵的病毒。 耶稣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又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注七)
在人里面的,在人心中的这些恶念或者说恶意,就是“罪”。

但正像一些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的专家所看到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双重视力的人,他除了那一双的“天然眼睛”之外,还有一双“超自然的眼睛”,这双“超自然的眼睛”使他能够直视人的心灵,看到人心中不为人的意识自觉到的深层的心灵活动,包括超理性的活动和下意识的活动。并且,在精神的一切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看到了正面,也同时看到了反面,不仅看到了生,也看到了死,更看到了“生就是死,而死就是生”。(欧里庇得斯)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断地解剖或者说述说“我”的心灵,并且是用相反的话来述说。于是,刚刚承认自己“心怀恶意”的“我”,立即又说:“我根本不是一个恶意的人”。 “先生,你知不知道我恶意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好,整个的症结,真正的毒针所在的地方,使我不断的,即使在真正发怒的时候,内在里仍然羞耻地感觉到我根本不是一个恶意的人,甚至连刻薄都够不上,我只不过是随便吓唬吓唬麻雀,并以此自娱。”(第24页) 人最可怕“恶意”就在他以为那是“善意”,并且这是“我们的善意”,而这善意却否定人心的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刚才当我说我是心怀恶意的公务员,我是在扯谎,……事实上我无法使自己成为心怀恶意的人。每一刻我都十分清楚,在我心里有许多因素与这个互相冲突。我感到它们在我心中我心中嗡嗡作响——这些冲突的因素!我知道它们在我心中嗡嗡作响已经整整一生,它们要找一个出口,但我不让它们,我不让它们,我有意的不让它们。它们折磨我,直到我感到羞愤;它们驱使我,直到使我痉挛——折磨我,到最后,是何等折磨我!好啦,先生,现在你以为我表现某种忏悔了,以为我要要求你某种原谅啦;我可以确定你会以为如此……然而,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我根本不管你以为什么……”
(第25页) 简单地说,恶意与善意,不存在于彼岸,只在“我”心。它们彼此冲突,相互敌对,并且从生到死,一直争斗不息,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战场就在那看不见的心灵最深处,敌军与我军都是我自己,不过一个是善意的我,一个是恶意的我,这两个“我”同居一室又彼此反对,“我”反对的正是我自己。保罗这样描述这场战争:“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注八) “我不仅不能变成心怀恶意的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变成任何一种东西……不懂如何恶意,不懂如何仁慈,不懂如何成为无赖,也不懂如何做老实人;不懂如何成为英雄,又不懂如何做得个虫豸。现在,我就在这个角落里生活,以这种恶意的无用的自慰来嘲弄自己:一个聪明人决不会一本正经的把自己弄成任何性质所确定的东西,只有傻瓜才干这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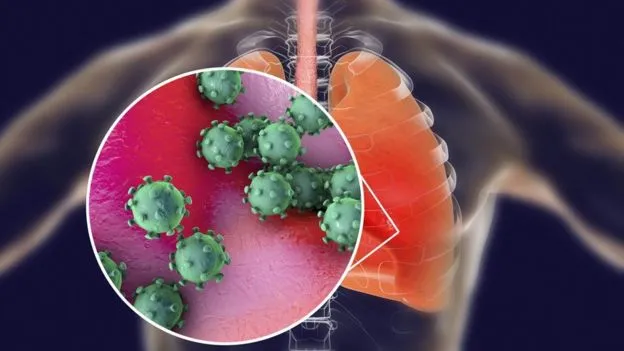
是的,在十九世纪作一个人,必须并且非常应当非常显然的成为没有个性的生物;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性质确定的人显然是受限制的东西。这是我四十年的信条。 现在我四十岁,四十岁,你知道,是整整的一生;四十岁,已经老得不能再老。比四十岁活得更长,是颟预的,卑鄙的,不道德的。活过四十岁的是些什么人?回答我,要诚实。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蠢货和臭皮囊。我对着所有的老年人讲这个话,对着他们的脸——所有可敬的老年人,头发银白,可敬的老者!我对着全世界的脸讲这个话!我有权这样讲,因为我自己要继续活下去到六十岁!到七十岁!到八十岁……好,让我喘一口气……”
(第25至26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将人性固定化,确定化。
人性不是一个物体,不是山川,不是河流,也不是飞禽走兽。人性不是“任何一种东西”,不是“任何性质所确定的东西”,人性,个性,这一切都在生成之中。
显然,这样的思想与时代潮流相反对,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要求的恰恰是人要成为并且必须成为没有个性的生物。
但是,人要成为一个自己,如祁克果所说,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人。
(待续) 2020.4.2 于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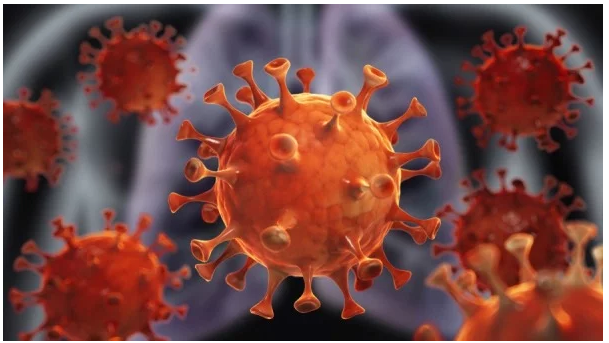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