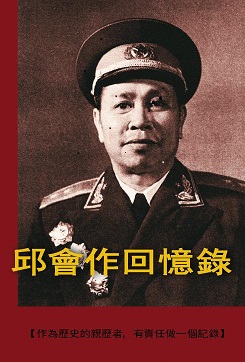
从“九一三”到9月23日十天的时间,对林的问题怎样处理,毛主席、周总理、叶剑英等人是费了脑筋的,因为在党的历史上,林的把柄是很少的。我考虑当时处理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暂缓“处理;二是以“反革命”处理。结果是采取了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就是抓住林彪“外逃”二字做文章。这在当时是最简单、最顺手的办法,但又是极端错误的办法,我说的错误并不是完全针对我们几个人,而是说主席为了他的文革,为了江青一伙,政治上完全失去平衡。从而为他自己变成孤家寡人创造了条件。虽然,抓我们的时候,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来,可是中央文件发布的“林彪反革命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等,有大量的谣言都是出自这几个家伙之手。
林彪决不可能是反革命,但又“外逃”了,怎样解释?这不仅是后来,就是现在很难说清楚的。林彪为什么会“外逃”?我认为是叶群、林立果不惜牺牲林彪的一切,为了自己的私利造成的。一是,对林彪封锁一切消息,林彪本人什么也不知道;二是,叶群把林彪控制起来了,他的女儿和工作人员都不能接近林彪;三是,叶群采取恶劣手段把林彪作政治“礼品”送给苏联。与其说林彪是外逃的,还不如说林彪是叶群的玩偶,被她架走的。我的看法以后会得到证明。
1971年9月13日到9月24日,整整十天的时间了。在这十几天时间,我的脑子整天都是嗡嗡响的,像做梦一样。但不管怎么想,把我关起来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待到24日约8时半进了人民大会堂的北门,我的谜梦才醒过来。
23日晚上,我还在给主席写检讨报告,刘秘书就来向我报告了第二天的外事和内事活动。笫一件是:早6时去东郊机场送李先念出访越南;第二件是:下午有外事活动,主要是谈军事援助问题;第三件是:早8点福建厅政治局会议。对早8时福建厅的会议,我倒稍微愣了一下,按惯例政治局会议都是晚上开,为什么改在早上开?但我又想,这是非常时期,可能有紧急事要处理,也就没有多去想了。
对周总理安排的活动,我向来是一不请假,二不误时,24日我早早就起来了。我如同过去一样,带上警卫员小朱坐车按时向东郊机场去了。虽然没有睡好觉还有困意,但在北京秋高气爽、凉风宜人的季节,很快也就精神了。
我到东郊机场贵宾厅之后,来的人还不多。因为今天有外宾,我还是选择了一个适当的位置坐下。为什么要坐在适当的地方呢?这是吃过苦头的。大约是1968年的什么时候,也是在东郊机场贵宾厅的外事活动。那天我去得稍晚了一点,除了挨着主宾席还有两个空座位之外,其余都坐满了。我看着主宾席就不敢去坐,另外找了一张凳子坐在别人的后面。周总理来了,他看到还有一个空位子,两眼一扫看见了我。他走到我跟前,二话不说,把我拉去同他坐在一起,并且还说:“我又不是老虎!”我只好推托说:“我是抽烟的。”总理说:“你尽管抽就是了。”此时,全厅的人都笑起来了,我真难为情。
我坐下之后,服务员照样送茶来,烟就在茶几上可以随便抽。我一边喝茶,一边抽烟,所看到的一切,都同过去是一样的。不久,李德生来了,他挨着我坐下了。李德生是一个开始红得发紫的人,我当然不会主动问他任何问题。但他还是主动问起我来了。
“你们总后的常委会开得很好嘛,中央的第一号简报就登的你们的会议情况。”李德生首先这样说。
“第一号,第几号还不一样,号数不起任何作用!”我的回答,其中略有意思。
李又说:“这也可以看出你对毛主席、中央的态度嘛!”
我只“嗯”了一声。没有同他细说下去。接着,我补了一句:“我准备发动总后的常委对我搞揭发。”李德生对我说的“揭发”一词没有做正面回答,他只说:“能搞起来吗?”又说:“即使搞起来了,也只能说些柴米油盐的事,这有什么用?”谈话稍停片刻,李又问:“你们总后常委是怎样分工的?你哪有多少时间管总后的事,日常工作是谁管?”
“家里的工作由张池明政委抓总。”
此时,周总理来到了。我们的谈话也就没有系统谈下去。从事后来看,李德生同我谈话是有目的的,他在做调查工作,我是一点也没有在意。
总理来了之后,不久起飞时间就到了。临去机坪时,李先念忧虑地跟总理说:“我很担心主席和总理的安全。”因为我坐在旁边,总理听到这个话,有些尴尬,他顺手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一边拍着我的手,一边对李说:“你放心去,一会政治局要开会,研究今后的工作。”
在停机坪上,我和总理并排站在一起,记者拍了不少的镜头。送走李先念后,总理主动对我说:“8点钟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的指示。”我回答说:“知道。”
总理又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你还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说:“那我也不回家了。”
总理说:“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我们抓起来,随即笑着对总理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总理说:“那好吧,到大会堂,我们先谈一谈。”
上了汽车之后,我又抽起了烟。小朱劝我不要再抽了。车开出机场不远的地方,司机告诉我说:“后面有随车。”我说:“让开,让他先走。”过了一会,司机又说:“停了,不走。”我们边走边停了三次,随车都跟着走。中央办公厅规定,政治局委员都要有随车,我也没有起怀疑,其实,大祸巳经临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相反,我还想过总理说的“向你们传达主席指示”,很可能是福音,给我们卸包袱的!
人民大会堂北门有内外两重门,门与门之间有个短过道(其他门也一样)。我一进外面的一道门,在过道上就有警卫干部一把把我拉到旁边的小房子里去了。我以为是有紧急电话呢,一进小房子就搜摸我全身,我来不及说话,搜摸我身上的人就说,今天要检查一下。我进到里面的二道门时,看到警卫员小朱的后影,有两个人把他连拉带拽地向西走去。至此,我一切都明白了,解谜了!然后两个人把我押进了福建厅(我1992年从西安到北京,跟随我多年的老司机张自贵来看我。在回忆往事时,他说:“当时也把我扣押在人大会堂地下室,我又气又纳闷地对小朱说:‘还敢扣押我们,准是反革命政变了!’”我看着忠厚、老实的张自贵,笑得肚皮都痛了)。
一踏进福建厅,—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变了。
福建厅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今天可成了法场了。厅内过去的布置是东西一圈椭圆形布置的沙发,对着门是敞口,离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扇屏风。今天的布置是:东边只有两张单人的沙发,南边四张沙发,北边还有两排若干张沙发。厅内沙发后面有若干警卫人员像西安临潼兵马俑的泥人一样,面无表情地站立在那里,每个人手扶着腰上的手枪。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在北面的沙发外站着。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我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还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走来走去。这种场面我有生以来还是笫一次看到,我是一个没有被敌人俘虏过的人,今天倒被自己的人“俘虏”了,这种场面就是让我们“见识见识”。
我被押进福建厅被指定坐在南面的四张沙发靠东面的最后一个位置上。刚坐下,总理的警卫员小高进来对我说:“总理叫邱副总长到河北厅去谈话。” 我刚起身,杨德中立即对小高说:“现在不谈了,等会一起谈。我给总理解释。”过了一会,小高又来喊我。杨德中有些不高兴地说:“告诉你不谈了,怎么又来喊?一会我跟总理解释!”小高边走边嘟囔说:“是总理叫我来的。”
我是第一个到福建厅的,不久,吴、黄、李先后到了,他们进来时,同我的神情几乎一样。
大约9时,总理在杨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厅。看上去,总理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总理和我们之间,这种坐法就是为了“安全”,把总理和我们分开。他是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专门负责总理安全保卫工作的。杨德中这种做法,在我们来看是多余的,在他来看是必要的。
总理坐下之后,首先喝了一口茶,并扫了我们(黄、吴、李、邱)一眼,即开口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这几天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电报,你们都看了。上海、陕西、天津的意见很尖锐,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指江青一伙),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总理的讲话很平静、很客气。
总理说到这里又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话时前后并不很连贯。总理主要指责我们不该跟着林彪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九一三”之后,又久久不表态。总理说:“出事都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的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此时,吴法宪支吾地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5时送出去的。”总理对吴法宪的话没有做任何表示。
总理接着说:“不知你们在想什么?九大时该照顾的都照顾到了(指都是政治局委员了),还有什么想法嘛!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力量(指江青一伙),是好事,这有什么不好嘛!?”接着,总理又补充了一句:“政治局的产生,你黄永胜是参与其事的。”
总理歇了一会又说:“过去有人(指江青)在病中说了几句话,(你们)就怀恨在心,那些问题都可以说清楚嘛!”总理的话是指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对林彪发脾气说:“蒋介石搞了一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一个军党、军国。”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问题。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胜利之后,林彪不能独吞果实,中央文革是出了力的。总理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以后都不同意江青这样提问题。因为主席没有批评过江青这个问题,江青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傲慢。但不知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走背字的时候,江青反而自己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说:“我在患病的时候,说过一些话,可能欠妥,但那是病人说的话呀。”总理当时就批评她:“话不能这样说,不能把说了不适当的话都推到病的问题上去。”现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又变了,有些袒护江青,这完全可以想得通。
总理说:“主席说过,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情况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触目惊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让你们几个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专门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总理接着又重复说:“主席说等了你们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我们都默默无语。写什么呢?难啊。关于庐山会议的检讨,在主席那里已经过关了,主席还跟我们开玩笑。在主席那里检讨过关以后,我们没有犯新的错误,“九一三”的事,的确一无所知。写什么呢?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实际上,我们被关起来以后,主要挖我们的就是“政变”问题。
至此,总理停了好久没有说话。他至少三次拿起茶缸子喝水,一边喝水,一边在想什么。他对着叶帅和其他在座的军委办事组的人说:“大家都说说嘛,只我一个人说?”叶剑英张了一下嘴,但一句话也没有说。纪登奎即说:“今天总理多说一点,我们以后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有呢!”
然后,总理先问了黄永胜几件事,主要问的还是前几天辩认的那封林彪给黄的信,黄完全否认,态度很强硬。总理又问起李必达的事,黄此时有些激动,黄气愤地大声说:“总理啊,我们对江青同志是有自由主义,但是你清楚,在座的也清楚,这是因工作中和江青同志有矛盾给逼出来的。如果是主席批评我,我接受批评。总理您想想,一个秘书有意偷听首长的电话,这样的人能要吗?你们在座的能容忍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总理不好再往下说,从座位上起来,一边说:“你先走吧。”一边走上来和黄握手,并叫吴忠跟黄走。黄快走到门口时,总理又说:“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实,没过几天我们几个人的老婆、孩子、亲属和秘书、司机、警卫员都抓起来了。总理已经不能控制局面了。
接下来,总理问吴法宪:“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总理刚问完,吴就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因为吴提到了军委办事组反江青的事,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李心里认为,反江青算什么错!事情发展到今天,可以说与反江青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今天,不但有一肚子苦水和冤屈倒不出来,反而马上就要被抓了,李激动得不能自己。
总理没有顾及李,马上对吴说:“你也走吧。”并与吴握手。由杨俊生跟吴走了。
总理又坐下来对李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
总理接着说:“张学思是怎么死的呀?”
李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有板有眼地讲了张学思的情况,说是中央专案组直接搞的,办案子和海军没有关系,也没有插手。一听中央专案组,总理就没有往下问了。总理又问李:“听说海军层层站队搞得很厉害?”
李说:“总理的批评是正确的。海军不团结,基本上就是—个派性问题,是有些扩大化,没有控制住。我有责任,我检讨。”
我同李作鹏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相当真诚。但我听到他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可见我们是多背吧。
总理先后问他们三个人的话,问到的都是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和“鸡毛蒜皮”的亊,我听着听着突然脑子里“嗡”的一响,好像开了壳似的。我这时才想到主席早就决定抓我们了,所谓等了十天,不是胸怀大度,而是在收集我们的“罪状”,以此来降服我们。
李作鹏走时,总理也上去与李握手。
总理有些生气地问我:“你怎么也搞进去了?”我没有吭声,也没有正视总理。接着,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给豆豆、林立果找对象的事讲了一下。
总理又问:“盛玉华怎么搞到总后去了?什么忙都乱帮一气。”
我向总理做了检讨。
总理接着说:“你们抓了李必达,连李必达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了。王瑞华同志搞到哪里去了嘛?”
王瑞华是301医院高干病房的护士长,工作表现很好,她是李必达的未婚妻。李必达事件发生后,我没有叫301医院处理她,因为她是九大代表,要慎重一点,就把她送到四医大学习去了。总理几次都问李必达的事,我知道我们要倒大霉了,因为李必达的事是和反江青直接有关的。
我走前总理和我握手,我含着泪对总理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总理那双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说:“好。”我就要离开福建厅了,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双手握住总理的手,从肺腑里吐出一句话:“希望再见到总理!”总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气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我从16岁就认识总理,党把我从一个红小鬼培养成一个高级干部,转眼40年过去了。在文革中,我被造反派多次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伤还没有好又投入到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去了,忙得有时身体都难以支撑,但还是咬着牙干。真没有想到最后反而成了反革命。不过,我向来都有这样的思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相信党是不变的,今天同样不变!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连党都不相信,也就不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人了。而相信党不只在一般情况下要这样,特别是自己处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严重受冤屈的情况下,在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只有这样,自己活着才有信念。
10时多一点,也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人把我押走,由福建厅到地下室,在地下室有预备好的汽车,车门对着电梯口,下了电梯就上车了。
与我同车的有中央警卫团的大队长,我不认识,他坐在前面驾驶室里。我坐在后面,两旁各一个警卫人员把我的手压在坐垫上。车出正阳门往东走,拐向北,再向东,走在去东郊机场的路上。因为警卫战士对我的手越压越紧,我向大队长提出:“应该压得松一点。”大队长即下命令:“放松一些。”我们一共三部汽车,徐徐进了部队的营房,把我关起来了,我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这里是北京的顺义县卫戍区警卫3师师部,我被安置在二连营房中间的一间房子里。房子里有单人木板床一张,小木凳子一张,小桌子一张,旧搪磁脸盆一个,一个饭盒子和一双筷子,一只搪磁饭碗,这就是房间的全部设备了。
进了房间之后,因为太疲劳了,便躺在床上。我眼睛一闭,过去的事活生生地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使劲不想那些,但怎么样也撵不出去。
不久,看管的人给我打来了饭。一个三层的饭盒子,一层是大米饭,一层是白菜,再一层就是汤了。一菜一汤。可是大米饭里,稗子和砂子很多。我的牙不好,我最忌讳饭里有砂子,只要吃上一粒砂子,整个牙都酸了,根本不能嚼东西。于是,我就把开水倒进饭里,用筷子一搅,砂子沉底,吃上面的就是了。这是我在卫戍区的笫—顿饭。
可能是下午5时多一点,又打来了晚饭。除了米饭换成馒头之外,菜同上顿是一样的,打饭的人对我说:“这是招待所打的饭。伙食不很好,你忍着吧。”我只看了一下盒子里的饭,一点也没有吃,就放到桌子上去了。—天没有进几粒米,看管的几个人有些着急了。站在我旁边的人说:“你不要过于焦急,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会解决的,还是要吃饭,要注意身体。”我抬头一看,同我说这番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送我来的中央警卫团的大队长。接着,他这乘机又悄悄说:“我们快要回去了。总理都把话给你说清楚了,你不要忘记总理说的话,时间不会长。你还是要吃饭,不然总理是不会放心的。你还有什么话要我带回去?”我向那位大队长表示感谢之后,请他回去后向总理转报三点。第一点,请总理放心,我不会胡想,也不会胡为。我决不会做那种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周总理的事(指自杀)。第二点,我对自己的问题心中有数。第三点,我很惦念我的妻子、儿女。我永远不会忘记总理在福建厅对我们的家属问题所说的肺腑之言。在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就认识了总理,以后又多次长期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能够经常得到总理的教导,真是三生有幸。我在大会堂对总理说过:“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我坚信到底,也请总理记住我的话。
押送我到顺义的那位中央警卫团的大队长走了之后,我就上床躺下了。大约到了7时多一点,我就向看管的人要了安眠药。过去,服“速可眠”很管用,吃了之后至少可以睡六小时,可是今天服了安眠药一点作用也没有,翻来复去总是不能入睡。
由于睡不着,我就要来纸和笔,向总理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回忆我同总理的关系。我同总理的关系确实是不寻常的。信写好之后,我看表巳经早上6时了,我第二次要来了安眠药,这次睡了五小时以上才醒来。我脑子比较清醒之后,把写好的信又看了一遍,我立即醒悟到,目前写这样的信完全没有必要,有可能给周总理造成困难,便立即把信撕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