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莱辛曾为你心碎
(瑞典)茉莉
对于真正的文学英雄,不管什么奖项都无足轻重。2007年,八十八岁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外出购物回来,发现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家门口就像拍电影外景一样热闹,已令年老力衰的莱辛不堪其扰,她更不愿辛苦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了。

不过,为表示对瑞典文学院的尊重,莱辛还是在12月7日之前,把一篇长长的获奖演说辞送来了。
笔者在瑞典听了二十几年的获奖演说,有几年是现场聆听,因此知道,获奖者大都要赞颂瑞典,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然后谈自己的文学启蒙、创作所受影响及其文学经验,或许还发表高超的政治观点以及对世界的美好展望。即使是倨傲不驯的获奖人如鲍勃·迪伦,本人不来领奖,却也在演讲稿中大谈歌曲与文学之关系,说明自己的歌词竟然与莎士比亚的剧本有同等的文学价值。
这些俗套,莱辛是半点也没有。瑞典有句话说:“哪个牙齿痛,舌头就会去舔那里。”这位老太太送来的演讲稿,没有感谢没有自夸,只是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一个劲地舔着那个令她几十年疼痛心碎的牙齿——津巴布韦。
成长于津巴布韦白人殖民家庭的莱辛,年轻时因谴责白人种族主义,被白人政权长期封杀。到穆加贝上台,莱辛才被允许重回独立了的津巴布韦,但黑人掌权的国家使她更为焦虑与绝望。这一类诺奖作家被称为“欧洲白左”,无论意识形态如何,他们不变的本质是反专制与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他们的文学,因此深切感人。
@ 极度贫穷小国对书籍的渴望
莱辛的获奖演说《远离诺贝尔奖的人们》,一开始就以充满了深情的语调,将我们带到遥远非洲的那个小国,那是作家度过童年与青年大部分时光的地方。演说中的一段风景描写,是莱辛难忘的童年记忆:
“我心里充满非洲的美好记忆,我不时回想起那里的情形,一幅幅画面浮现在眼前。夕阳西下,橘色的、金黄的、紫色的晚霞涂抹在黄昏的天边。蝴蝶、飞蛾和蜜蜂在喀拉哈里沙漠芬芳的灌木丛里飞来飞去。……”
可惜这样温馨的回忆太少了。在长篇演讲中,莱辛絮絮叨叨所说的多个故事,大都是关于津巴布韦的贫困。那里贫穷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而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里的人们对书籍的强烈渴望。
在获奖演说里,莱辛谈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回津巴布韦的经历:“我站在门口,远远望去,穿过风卷黄沙的云层,眼光落在一片树丛中,……。”不只是被糟蹋的大自然令莱辛心疼,在独立多年的津巴布韦,那里学校的困境更令莱辛不忍目睹。
莱辛去学校拜访一位“援助非洲”的英国教师。那教师说,他必须经常把粉笔放在口袋里,否则就会被偷窃。学校没有地图或地球仪,甚至连教科书都没有,更没有练习本或圆珠笔。凡是遇到莱辛的津巴布韦人,全都害羞地向她讨要书本。其他的学校连粉笔也没有,教师们用棍子在地上写字,用石头在地上的灰堆里写写画画,比如“2X2=”之类的算术。一位黑人作家说,他靠读果酱瓶子上的标签自学。
从非洲回到英国,莱辛去了伦敦一所非常好的名牌学校演讲。津巴布韦风沙尘土中的简陋学校在她心里盘旋,她想,那里的一切对伦敦名校的学生是多么陌生。在对比了两个有天壤之别的学校后,莱辛说:她敢肯定,伦敦名校的学生,将来总会有人会得什么奖的,而诺贝尔奖不会来自津巴布韦,因为写作有必要的前提,作家不能出自没有书的房子。
莱辛还告诉我们,在津巴布韦的一个贫困村庄,村民们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了,可他们却谈论图书,谈论如何得到图书和教育问题。在穆加贝时代的通货膨胀下,从英国运来的一本好的平装书,普通津巴布韦人得花几年的工资。如果有人带上一箱书去一个村子,会得到一箱感激的泪水。

以女作家擅长的抒情手法,莱辛描写了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那女人在印度人店里看到一沓纸张,立即饥渴地阅读起来,原来那是一本被人撕烂做包装纸的书——俄国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然后,可怜的女子顶住水罐,一路穿越黄尘跋涉回家,梦见给她孩子提供的教育。
@ 从谴责白人殖民到批判黑人政权
听莱辛这样讲故事,人们会觉得这只是一个亲切仁慈的老太太,在关心非洲穷人的教育。但是且慢,千万不要把从反殖民反男权的阵营里冲出来,立志要创造正义新世界的左派斗士莱辛,错看为好心啰嗦的邻家老太。
在莱辛写这篇获奖演说时,今已辞职的独裁者穆加贝正在台上威风,整个津巴布韦都在关注这位从那里走出来的诺奖得主,看她在全世界面前说什么。斗士本色不改,莱辛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毫不客气地把津巴布韦人民的贫困归咎于:“穆加贝的恐怖统治”。
她伤感地写道:“一九八○年津巴布韦独立时,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真是一窝会歌唱的鸟。他们是在旧称南罗得西亚,在好得多的白人教会学校里喂养大的。作家并不是在津巴布韦造就的。在穆加贝的统治之下很难造就作家。”
这位昔日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的作家,竟然就怀念白人在殖民地创办的教会学校来了。笔者记得,南非的曼德拉、津巴布韦当年的游击队领导人、此时的总统穆加贝,都曾在白人的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在抨击穆加贝残酷统治的同时,莱辛指出了昔日白人政权在传播文化上的功绩。她说:“有人说,有什么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我不认为这句话适合于津巴布韦的真实情况。我们应当记得,这种对于图书的尊重和饥渴,不是来自穆加贝的政权,而是来自在它之前的那个政权,白人的政权。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对图书的渴望,从肯尼亚一直到好望角,无处不可以发现。”
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又退党,莱辛当然知道马克思的一个观点: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有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破坏了殖民地土著的经济基础;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津巴布韦在黑人解放的后殖民时代,从公认的“南部非洲面包篮子”变成悲惨的饥饿之地,这是昔日反殖民的女作家始料未及的。因此,在莱辛晚年的诺奖演讲中,她给昔日的白人政权做了一个苍凉的手势,作为纪念。
@ 当年左派是唯一有道德力量的人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当年莱辛等欧洲左派反殖民主义就反错了。殖民主义是一种人压迫人的不平等制度,过去的欧洲殖民者几乎不把非洲土著当作人对待,因此,人们希望非洲国家能够独立,自立平等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像莱辛这样生性正直的人,在那个时代几乎不可能不成为左派。她出身于一个英国殖民官员家庭,父母于1925年来到当时的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希望能靠种植玉米致富,还希望向落后的非洲转达“文明价值”。当时白人殖民者高高在上,垄断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命脉。
待莱辛长大后,她发现那是一个被警察控制的小国,非常令人厌恶。她感觉到,活在一个少数人压迫大多数人的社会是多么糟糕。生活死寂狭隘、丑陋而又沉闷,于是她参加左翼组织,积极投身反殖运动。在笔记里,她解释说:“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这个镇上唯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种族隔离看作洪水猛兽。”
莱辛的早期作品因此带有浓厚的社会政治批判色彩,她竭力鞭挞种族隔离制度,表达对非洲殖民地黑人悲惨遭遇的同情。因此,回到英国的莱辛,有三十几年时间被禁止重返津巴布韦,直到白人政权倒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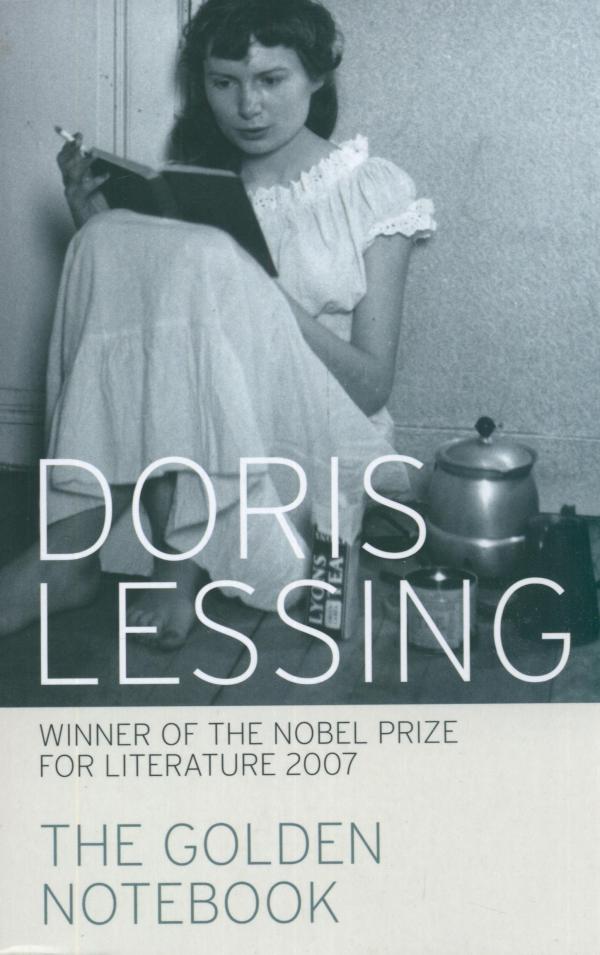
笔者曾与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为何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都是左派作家,右翼作家却寥寥无几?答案很简单,因为诺贝尔留下的遗嘱是,要褒奖那些“创作出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而人文主义理想一定是要同情弱者、有博爱平等精神的。
@ 永不变的是反专制及人道精神
如前所述,昔日支持非洲反白人殖民的是莱辛一类的欧洲左派,今日谴责黑人总统穆加贝的也是他们。表面看起来他们似乎改变了观点,其实其欧洲自由左派的本质从未改变。他们反对一切专制——不管是白人的种族压迫,还是黑人的专制统治。
作为中国人,我们要看到的是,当今在欧美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呼吁的,大都是莱辛一类的自由左派。但是很奇怪,近年来,海内外华人网络主流舆论一边倒地,指责挖苦“西方白左”和“圣母婊”,即使是自己受惠于西方左派所建立的国际人权机制的人,也加入这种批“白左”的大合唱。
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欧洲人的基督教拯救意识,缺乏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难以理解欧洲人对殖民历史的反思,更混淆西方左派与中国毛左的本质区别。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所产生的理解问题,莱辛被中国文人视为“具有浪漫情结的理想主义者”,她反殖民主义的经历,被视为生命中的偏激段落。实际上,莱辛政治上的选择并不天真,而是来自她对非洲生活的真切认识,也来自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以及反专制的自由精神。
尽管莱辛本人不信教,但是她从小读的是天主教教会学校。如同传教士一样,她的父母来到非洲,都曾希望向落后的非洲转达“文明价值”。她的母亲还曾雄心勃勃地,要用爱德华时代的文明改造当地野蛮土著的生活方式。他们都失败了,充满了挫折感和幻灭感,女儿莱辛因此认识了现实真相,开始反省白人殖民的功过,并发现非洲的悲剧——以黑人自己人的奴役代替了白人的奴役。
@ 送给非洲的最后一批礼物
几年前,94岁的莱辛去世。在漫长的人生中,她一直关注津巴布韦的政治腐败、艾滋病、乡村企业、丛林中消失的动物等各种问题,但她没来得及看到津巴布韦的最新变化,没听到津巴布韦人民今日的笑声。即使莱辛能看到穆加贝下台,她也不会特别欣喜,因为她知道,新任总统曾是穆加贝的左右手,由一条鳄鱼取代吃人的鲨鱼,津巴布韦的前途仍不容乐观。
纵观一生,莱辛把自己在非洲几十年的忧伤变成了世界级的文学作品:一些自传性散文小说,四部回忆录,还有不少诗歌和戏剧,最终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予她的颁奖词写道:“她以怀疑主义、激情和想像力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她登上了这方面女性体验的史诗巅峰。”
在死神到来时,莱辛留下遗言,向津巴布韦公共图书馆捐赠自己的3000本图书,这是她送给非洲的最后一批礼物。这个捐赠图书的工作她已经做了几十年,并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组织,尽其所能地搜集书刊。在整个获奖演说中,她没有一句话感谢颁奖给她的瑞典,只是提到她的组织曾获得瑞典的资助:“如果没有他们的资助,我们的书早就送完了。” ……………………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Sunday, November 26, 20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