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童话世界招魂 ---读张郎郎《大雅宝旧事》
茉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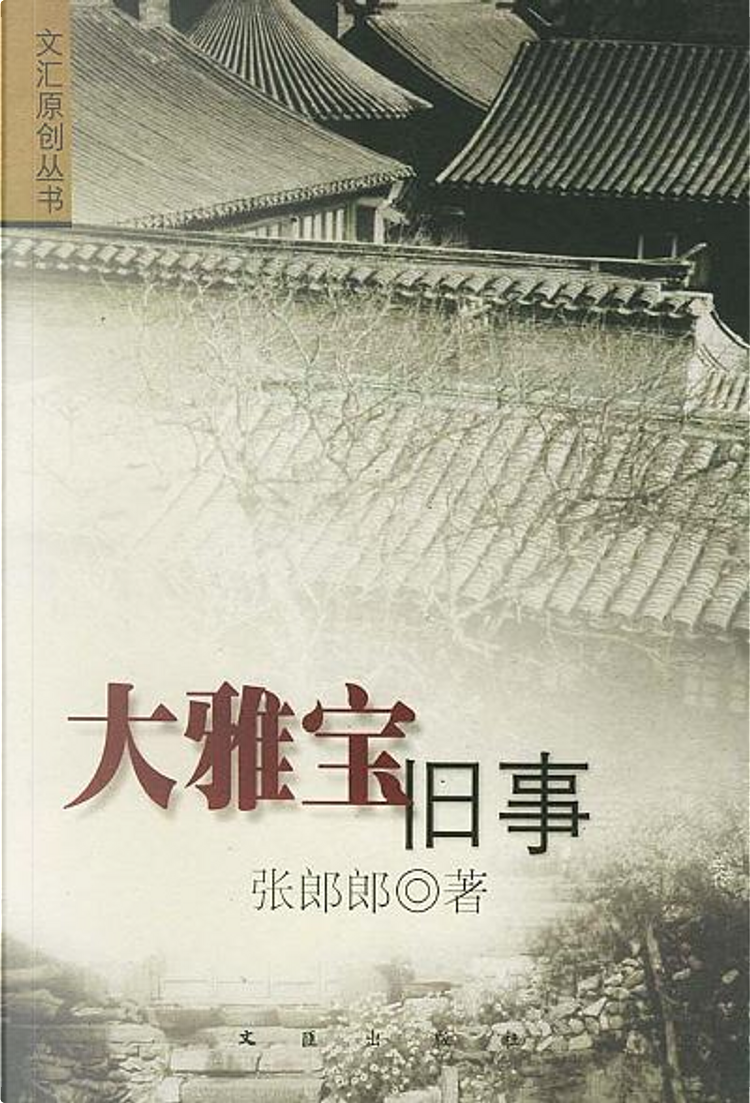
我们都喜欢读童年故事,原因无他,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愿意长大。事实上,在我们成熟甚至沧桑的外表下,或多或少保留了一点童稚的心愿,谁不愿意无忧无虑、享受被人呵护和疼爱的特权呢? 怀着好奇之心,我读了张郎郎的童年回忆--《大雅宝旧事》。这是郎郎的北京胡同系列的第一本,描绘的是1949年以后,郎郎一家居住过的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中央美院艺术家们的四合院生活。 至今不肯承认自己已老的郎郎,以他顽童式的神奇语言,为我们叫开了那座四合院的记忆之门,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重返他的童年时期。透过他诗一般的温情笔触,那段逝去了的甜美岁月,那个不平凡的人间乐园,那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方式,画卷般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 特殊年代的“孤本童话”
这是一部特殊年代的历史评传。对于文学,昆德拉有这样的看法:“只有在历史之内,一部作品才可作为价值而存在,而被发现,而被评价。”郎郎的《大雅宝旧事》超越了我们通常读到的童年回忆,进入了一种深入探询历史的境界。作者追忆“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的生活经历,细腻而具体地写出大雅宝胡同奇异有趣的人和事,道出不少著名文化人的生活细节与坎坷命运。 想要写出大雅宝胡同故事的,不只是郎郎一个人,早就有被郎郎称为“黄妈妈”的黄永玉夫人,说她要写一本小说,就讲大雅宝孩子们的故事。多年前,著名画家黄永玉就满怀深情地说:“大雅宝胡同二号,不是一个画派,而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 然而,最终以当年这个院子里一个孩子的视角,写出大雅宝那“有意思的生活”的,却是当时人们认为比较迟钝的孩子郎郎。按照郎郎自己的说法,他是要和那些说新中国只有苦难家史的人“较劲”,要讲一个绝对的“孤本童话”。虽然郎郎一不小心掉进童话世界的时候,我还没有在湖南乡下出生呢,但比郎郎年轻的本人,却有一个苦涩而半饥饿的童年,因此,郎郎那美丽的孤本童话,正是由众多孩子的悲哀童年垫底的。 郎郎的“孤本”之所以“孤”,有其特殊的时代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在建国初期,在严酷镇压如我家父辈之类的国民党人之后,给愿意忠诚于新政权的文化人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无产阶级铁拳”尚未对这部分人士露出太多的狰狞,暂时地让他们保留了一定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或受过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影响,或留过洋,耳濡目染了西方文化的精华。加之地位和待遇都较为优厚,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因此,他们就在京城的一个胡同里,享受着一种被郎郎视之为“童话”的艺术生活。 如果我们了解郎郎家后来在政治运动中的苦难命运,了解郎郎自己在文革中坐大牢并押解刑场“陪斩”的经历,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异国他乡流亡多年的郎郎,非要写出这个孤本童话。传记往往是人们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郎郎需要回顾童年,才能把这一生认识清楚:自己之所以压根糊涂了几十年,原来是心理上一直没有从幼年的童话里走出来。他小时候老以为自己是别的星球上的一个王子,被送到地球上来经受磨练。 正因为有那么多童话故事做心理底子,后来这孩子经历了现实的九劫八十一难,尽管他没有力量去对抗世上的不公平,但他总有办法苦中取乐。他坚信厄运只是一场游戏,噩梦是暂时的,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就如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他仿佛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在此书中,郎郎不但为他那无限珍贵的童年存档,同时,也为时代和历史存了档。
@“最后贵族”的优雅与风华
今天已经年近花甲的郎郎,身上有一种令人们惊讶的文化气质,真诚而聪颖,善良而幽默。读了《大雅宝旧事》,我们才知道,这种气质,来自那个胡同优雅氛围的熏陶。在物质发达而精神粗俗的今天,痞子犬儒文化流行,京城的四合院被推倒,精神的废墟上只剩下钱币的气味和喧嚣,郎郎笔下的那种雅韵,是无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 此书所追忆的人与事,时间多在中共建国的头几年,书中的人物,大都是当年投奔中共的热血青年,以及一批追随新时代的著名文化人。他们觉得当时的新中国除旧更新,一切都欣欣向荣,进入社会主义理想境界了,于是,他们意气风发,忙着为新中国做贡献,设计国旗、国徽。配合毛泽东的前进步伐,这些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们,立志创造“启发人民政治觉悟”的新中国美术。 这些追求革命的艺术家们,尚未预料到革命将会吃掉自己的孩子。虽然郎郎的父母曾在延安领教过共产党“肃反”的残酷,但善良的人们以为,那只是我党一时的错误,只要纠正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在建国后一派盛世景象面前,他们又重新做起艺术之梦来了。 在小郎郎的眼睛里,这些杰出的艺术家,岂是一个“雅”字了得?郎郎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任何事情都说得有趣,写得活灵活现。于是我们看到那一代著名艺术家的日常风采。 每天清晨上学,郎郎会看到画家李可染等人的画室里还亮着灯,那是艺术家们趁夜深人静潜心作画的时候。中秋晚会时,李可染会在四合院葡萄架下拉京胡,孩子们会跟着黄永玉的手风琴唱歌。中央美术学院的晚会上,孩子们看到,老舍朗诵诗作歌颂北京的春天,郁风阿姨翩翩起舞,赵树理打鼓唱山西梆子,李苦禅虎虎生风耍弄关公的青龙偃月刀,---。 而郎郎的父亲张仃,更是一个艺术大儿童。他在延安时就热爱毕加索,因此被指责为“传播现代派歪风”。后来听说毕加索也是共产党员,张仃就把毕加索的油画挂在窑洞里,因此被华君武取了一个“城隍庙加毕加索”的外号。后来,他终于有机会,代表“新中国”的画家,在法国拜会了毕加索。 当时,这些想在新中国里大展宏图的艺术家,最感兴奋的一件事情,是筹备恢复三十年代上海摩登杂志《万象》,想把它办成一个图文并茂的文艺杂志,他们相信自己会办得比官方杂志好得多。他们希望献身艺术,干干净净、不卑不亢,以画画、写文章来养活自己。1956年夏天,一个以吴祖光为首的十人筹委会成立,办起了《创刊号》。 这个风雅也太大了一点,大得超过了我们湖南农家出身的领袖的容忍程度。幽默闲适的《万象》杂志尚未问世,反右派运动就已开始,不少作者被打成“反党右派”,这些尚在梦游的天真艺术家,终于尝到了共产党“绞肉机”的厉害。一代优雅风华,从此夭折陨落。他们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精神贵族”。 四合院里的人情与童趣。
《大雅宝旧事》除了让我们一睹昔日艺术大师的迷人风采之外,还让我们重温了过去时代美好的大院人情。在郎郎笔下,那个大院里的艺术家个个真淳厚朴。他们共聚一处,既给生活注入艺术情趣,也享受了融洽的人情之美。对比今天人们的自私、孤独和冷漠,人际关系的功利与险恶,那个昔日的大院,仿佛是中国土地上的一块温馨飞地。 郎郎在书里,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那时的人情味多浓啊,人们随意串门子,自己画的画儿,朋友来了说声喜欢就可卷走。有什么新鲜菜,东家给西家送,西家给东家拿。就连大名鼎鼎的齐白石老爷爷,到了春节,也给院里的孩子发压岁钱。这家的孩子,搬个板凳就到那家窗户下听音乐,那家的孩子,被这家的叔叔带着去吹笛划船,---。 那时候,大院里的孩子一个个玩得不亦乐乎。郎郎几乎回忆了大雅宝胡同所有的逗事儿,坦白交代了孩提时代的恶作剧。对于这些小土匪,弹球儿、拍洋画儿、逮佬儿赢三角什么的,只是游戏小儿科而已,更刺激的是爬到房顶上去偷枣子,和国际友人在胡同里踢足球。除了逮蜻蜓、招蝴蝶、沾知了之外,他们最重要的活动还有斗蛐蛐儿。兵多将广的他们,雄赳赳地带着蛐蛐儿,不但和其他胡同的孩子斗,也和大儿童黄永玉的蛐蛐斗,最后只得乖乖地拜倒在黄叔叔门下。春节的狮子队里,郎郎参加伴奏,他以为自己是“会吹魔法笛子的牧童”,因而乐不可支。 在那种良好的环境下,孩子们潜移默化地接受艺术熏陶,自我成长起来。例如,他们自作主张办壁报,画漫画,用透明的硫酸纸临摹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他们从大人的雕塑工作室里得到胶泥,学着用模子扣泥人。在大人创作的时候,他们会安静收声,聚精会神地观看。胡同里经常有小蘑菇、面人汤一类的民间艺人出现,孩子们向民间艺人买手工艺品,也和他们交上朋友。 这些故事经有说书天赋的郎郎一描绘,立刻趣味无穷。大雅宝的孩子,不像今天的少年儿童那样被“催熟”。他们的家长自己喜欢自由,因此不强迫孩子们去适应社会,也不去逼他们为了高分去做枯燥的重复性练习,他们的活蹦乱跳的个性被家长尊重,因而能够自己教育自己,不仅仅从书本获得知识,更是从玩得发疯的游戏中,获得了精神的活力和创造性。 据说从大雅宝出来的孩子,长大后个个都很精彩。这一点我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信奉的一个“绝招”就妙不可言:“把玩儿的事情,当正经事来办,一定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正经的事,要和玩儿一样,一定不会伤了身子骨。”看起来耽于玩乐的郎郎,把童稚时的每一件逗事儿都描写得淋漓尽致,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发掘其中的乐趣所在。我想,经历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已经患病的郎郎,在执笔撰写这一切时,一定是在悲哀的眼泪里伴着响亮的欢笑,充满了对童年岁月的感谢之情。
@ 像月亮一样完美的童年残缺了
不管大雅宝的家长们是如何呵护孩子们纯洁幼小的心灵,他们童年时看到的那些唱着歌飞过胡同上空的鸟,是再也不会飞回来了。 天公妒人美。继孩子们欢乐的童年故事之后,却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续集。要完全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还需要等待郎郎的胡同系列之二、之三、之四。但在这本《大雅宝旧事》里,他已经在对胡同生活的描写中,预告了这批文化人日后的悲惨命运,一叶知秋,光是这本书所透露出来的历史真相,就已经够令人触目惊心了。 首先是延安时期中共对自己人的残酷。在延安窑洞出生,坐在马背上进入北京城的郎郎,从父母和叔叔阿姨的窃窃私语中,听到了不少令孩子惊恐的事情:不少当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遭到严酷的迫害。例如,延安美术学院的石泊夫,被指为“国民党奸细”而抓走,他的太太拉着两个孩子,在窑洞里自杀。 郎郎的父亲张仃也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关押审讯,生孩子后缺少营养的母亲几乎完全失明。父亲的问题更连累了一位仗义执言的朋友。因为为张仃鸣冤叫屈,歌唱家杜士甲也被抓起来。一气之下,杜士甲跳井自杀,幸亏只伤了皮肉。 对那些真心追随中共、帮助中共的知识分子,中共强行给他们“洗澡”,可以说负心负义到了极点。例如,著名政治学家张东荪,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洗澡运动”中,第一个被以“间谍罪”拖出去,文革后死于秦城监狱。著名的热带病学专家李宗恩,曾拒绝胡适等人去台湾的邀请,诚心留在国内奉献,后来被打成右派,死在发配地云南。从法国回来的雕塑家王临乙,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被批判时,被逼着顶铁锨跪在舞台上。有恩于新政权的黄绍竑先生被迫在反右运动风暴中自我了断,虽然那次被抢救过来了,可是他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拂袖而去 当然,中共在建国前后对知识分子的整治,比起后来的反右和文革,还是小巫见大巫。在文化人开始忧心忡忡时,小郎郎也吃惊地发现北京平民的赤贫生活。有一次,他和小伙伴去一个瘸子家,发现那里家徒四壁,那家人饿得面黄肌瘦,女孩子甚至穷得一丝不挂。 《大雅宝旧事》一书结束在一片大字报和反右派的批斗声中。大雅宝中院晾衣服的地方拉起了麻绳,麻绳上挂满了恶狠狠的大字报和漫画。孩子们的天真小脸开始发白,巨大的困惑和震惊压住了他们。这个曾有过无穷乐趣的大雅宝胡同,现在不好玩了。 一帮曾经在胡同里快乐呼啸的小土匪,一个总是在幻想中梦游的小小男孩,他们稚嫩的心,是怎样面对后来一波又一波,一波比一波更凶狠的政治运动呢?在没有看到郎郎的续集之前,我们只知道,灾难并没有因为他们可爱而放过他们,那原本像月亮一样明亮完美的童年,残缺了。
@ 以文字魔力为大雅宝招魂
在文革期间,大雅宝被改名叫做“蓬勃”。在北京市大兴坼胡同之风的今天,据说大雅宝胡同已经缺头去尾了,原来的那个院子是否还安然无恙?我想,即使那四合院的建筑还保留了原状,恐怕也是远离了当年的优美和风雅。后来听郎郎说:那个院子还在,可是找不到当年的丝毫痕迹了。 在文化和人性方面,中国早已不是昔日的中国。历史总是在和人们开玩笑。那些曾经被人强行抛弃的东西,今天却令人无比缅怀。但在一个迅速粗鄙化、野蛮化的社会,无论怎样的怀念和嗟叹,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几十年过去,共产党制度损毁了一切文化和人性的美好。今天,那个会吹笛子的小牧童郎郎,却在遥远的美洲,以他魔法般的文字,为一个质朴、温暖的大院招来亡魂。郎郎的文字接近化境,它娓娓道来,不带一丝火气,于从容宁静之中尽显功力。大雅宝那短暂而美丽的时光,因这样的文字,定格为一个个永恒闪烁的、韵味无穷的意境。 一本迷人的书,一场完美的道别,一部精致而怀旧的蒙太奇电影,一朵由眼泪和微笑浇灌的奇花。对于那个非同寻常的时代,这本传记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证词。来自一个孩子的纯真记忆,此书不但具有审美的文学性,更具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我们从中获得一种奇特的审美愉悦和历史沉思。它正是胡适所鼓励的一种传记:“给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 注:《大雅宝旧事》由未来书城出版社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在台湾出版。 (此文原载《民主中国》) 0308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