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诗,磨一根精美的手杖
——傅正明与《英美抒情诗新译》
茉莉
那年我从长沙监狱出来,看见丈夫的书桌上摆着一叠叠涂鸦的纸张。妻子不在家的孤寂时光里,他重读了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叶芝等西方著名诗人的诗歌,发现中国翻译家的译作有些不尽人意之处,于是就自己试着重译。
我不懂翻译,但我知道,在1989年那场血与火的大悲剧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被迫沉默,深感精神压抑的傅正明走向内心的寻求。重译那些优异的西方诗歌,是译者与西方文学大师进行心灵对话,吸收他们的智慧和灵性,充实和温暖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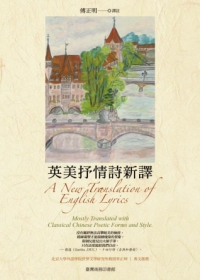
对傅正明来说,在一场社会大风暴过后翻译诗歌,是一种禅修的方式,一种渐修渐悟的自我观照。在痛苦中沉静下来,他沉潜到文学和历史的深处。心中被迫隐忍的愤懑之情,在诗歌中找到宣泄的出口。例如,雪莱的《西风颂》描写西风在大地、天空、海上的宏伟气势,直抒胸臆地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令傅正明产生同气相求的强烈共鸣。
站在王佐良等前辈翻译家的肩膀上,参与自己的人生体验,傅正明在翻译中,对雪莱《西风颂》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雪莱这首绝美的诗歌出现了一个新的中文译本。
“啊,狂野的西风,你这秋神的浩气,
吞吐呼啸无形迹,抖落满地枯萎,
犹如巫师念咒语,群鬼纷纷逃逸,……”
永恒的诗歌使人不再绝望。雪莱的歌声令经历了六四大屠杀的我们倍感慰藉:
“沉睡的大地响起醒世号角,
催促蓓蕾吸清气,如驱赶羊群
觅食新绿,到处弥漫生香活色,……”
流亡对我们来说,只不过是把中国南方的那张书桌,搬到冰雪大半年的北欧而已。在瑞典享有写作自由,傅正明翻译的兴趣更大了。他把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诗文译成中文,并从理论上做研究,出版了《百年桂冠——诺贝尔文学奖世纪评说》。他还去印度流亡藏人社区采风,搜集和翻译了大量西藏流亡诗人的诗作,主编了《西藏流亡诗选》,出版了研究著作《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 》。
常常看到傅正明埋头译诗,沉溺于诗歌词句的推敲斟琢,我想起梭罗《瓦尔登湖》中的一个故事。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想要做一根完美的手杖。他自言自语地说,哪怕一生中不再做任何其它事情,我也要把这根手杖做得十全十美。于是他一心一意、心无旁骛、锲而不舍地开始工作。在制作手杖的过程中,亲友们一个个离开了他。人们老了、死了,而他却在忘我的工作中保持了青春,……。
做手杖的艺术家之所以不老,是因为在全神贯注的工作中,他进入了一种非凡的境界。摆脱了世俗的一切功名利欲,人变得像孩子一样单纯年轻。
夏日的傍晚,我们常在北欧的海滨散步,傅正明常向我兴致勃勃地谈论他的译诗。我爱听不爱听的,他也自顾自地照谈不误。译诗就像散步,人走在一条小路上欣赏风景,走到林间深处,里面出现了更广阔更美丽的风景。诗歌中的激情和美感,给译者的心灵世界洒满了光辉。
年华随风而逝。只有一次生存机会的人,难免受到虚无和孤独感的威胁。我们家这位专心致志的译者,过着简朴的生活,黎明即起辛勤劳作。译诗是一种再创造。除了译诗之外,傅正明偶尔也写作自己的诗歌,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释放了生之烦恼,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平淡无聊。
如同磨一根精美的手杖,傅正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孜孜不倦地磨他的诗歌,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些作为自我禅修的译诗,会有一天公开出版。几年前,傅正明将自己翻译的几首英美名诗贴在网络上,由此引起了一些诗歌爱好者的注意。
首先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发表了《从<西风颂>的两个译本比较看经典名作复译的必要性》,论文作者张世红教授通过对王佐良和傅正明的两种译文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傅译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新的理解,在不少地方作了改进和完善,有所创新。该文肯定了傅正明重译英诗的价值。
而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于2012年6月出版了傅正明的《英美抒情诗新译》,为已有多种译本的英美名诗提供了一种可资比较的新译本,促进译诗的语言艺术走向精致和准确。
英国诗人阿诺德的《菲洛美拉》一诗,把来自希腊的啼血的夜莺称为“可怜的流亡者”。下面是傅正明翻译的该诗中的一段:
“请问,那创伤永远不能愈合吗?
这片馨香的草地
能否把凉爽的树荫、良宵、
芳草、宁静的泰晤士碧流、
月色和露珠当作一块香膏
为你剧痛的心灵和神智
敷贴伤口?”
与诗歌共存的生活,给流亡者提供了一片疗伤的栖居之地,并且展现了一个开阔而神秘的宇宙。为此,沉浸于诗歌之美的傅正明深感幸运。
-------
2012-06-24 中国时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