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红的党旗与《白鹿原》

(瑞典)茉莉 在鲜花环绕之中,遗体上覆盖着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其葬礼可以说是备极哀荣。除了铺天盖地的赞誉之声,各路名流的吊唁致敬,还有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赠送花圈的殊荣。

然而,与这个热闹场面不太协调的是,灵棺里的陈忠实头下枕着一部《白鹿原》。这是一部当代罕见的优秀小说,它所展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倾向,与中共镰刀斧头式的红色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这似乎是一个有点滑稽的玩笑。思考这个矛盾的现象,我们需要认识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学的进步与倒退,了解在中共禁锢思想的专制制度下,身为作家的陈忠实,曾经有过多么不同凡响的思想反叛和与文学追求,又曾怎样无奈地向权力屈服妥协,在精神上阉割自己后名利双收。 ◎ 小说政治倾向与中共针锋相对 早在1992年《白鹿原》出版之初,该书贬低、否定中共的政治倾向性,就被某些党性强的文坛领导人发现了,陈忠实获茅盾文学奖的事情因此受阻。当时,批评者指控《白鹿原》有“倾向性问题”,说作者歪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了地主阶级,丑化了共产党人,有意模糊政治斗争应有的界限。 这些严厉的政治指控,由于当时在文坛享有话语权的评论家陈涌出面说话,而得以缓解。在陈涌确认该书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之后,作者遵嘱对该书做了删改。1997年底,《白鹿原》修订本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侥幸逃过一场政治追究,这本笔力凝重的杰作得以存活了下来。但凡是认真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不能不承认:那些指控《白鹿原》有政治倾向问题的左派党棍是对的,他们以特有的党性敏感,指出了小说的真相。 而《白鹿原》一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其全部奥秘恰恰在于此:出于文学良知,作家拒绝为中国共产党唱赞歌。相反,小说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完全颠覆了共产党文学的话语体系,以赤裸裸的历史真实,对非人性的中共进行了贬斥与否定。 首先,小说把在五十年代遭中共残酷镇压的地主,描绘成代表民族优秀传统的好人。白嘉轩是《白鹿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继承了父亲的族长地位,关心族人的日常生活与生死存亡。尽管白嘉轩有一些旧宗法家族制度的保守意识,但他以“仁义”真诚待人,广施善举。在长期丑化地主的中国革命文学里,此书塑造了一个受人敬仰的正面的地主形象。 其次,小说揭露了中共革命如何无情地吞噬自己的儿女。书中的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关键人物,是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年轻而真诚的白灵在加入共产党后出生入死,结果却在革命根据地遇上红色恐怖,被冤枉为“特务”给生生活埋了。 再次,通过纷繁复杂的历史叙述,这部小说表达出的作者的政治态度与历史观,几乎都是与中共的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例如,阶级斗争是中共的基本理论纲领,但在《白鹿原》中,民国时乡村的阶级并非势不两立,白家唯一的长工鹿三,与地主白嘉轩的关系就相处得十分和谐,令人感动。 中共一贯反儒,曾把儒家当作“四旧”来镇压,而陈忠实的“仁义白鹿原”却真诚赞美儒家文化和传统的“仁义道德”。书中也真实描写农民革命的暴力与非理性,是如何残忍地剥夺人的生命与尊严。 又如,中共总是宣称自己打败了蒋匪帮,是中国的大救星,而小说却借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发表精辟高论,把白鹿原比作一只翻烧饼、摊煎饼的鏊子。国共两党血腥的政治斗争,在小说中的人物看来,只不过是以百姓为刍狗、导致民不聊生的“翻烙饼”而已。 小说里的国民党员有坏人,也有如鹿兆海、岳维山一类的正人君子。而共产党方面却很讽刺,他们的优秀人物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能够活下来并青云直上的共产党人,是白孝文那类踩着别人尸骨往上爬的堕落分子。
◎ 现实主义写作违背作家本人立场 上述基于小说文本分析出来的政治倾向,陈忠实本人是不会承认的。不但不会承认,老先生如活着,还会高调地宣布,他本人的倾向性与笔者所指出的“贬共”倾向完全相反。 1993年12月《白鹿原》出版不久、尚未获奖之时,陈忠实就发表了《毛泽东代表着一切普通中国人的独立人格》一文,热烈赞颂毛泽东的崇高人格、思想、智慧以及其创立的伟业。2012年在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陈忠实又一再强调:“我的《白鹿原》里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如果联系到陈忠实本人的中共党员身份,回顾他长期在农村做基层干部的生活经历,我们可以想象,陈忠实“拥共”的自我表白虽有隐情与某种目的,但却不完全是假话。那么,一个持拥共立场的作家怎么会写出明显贬共的作品来呢? 这种看似奇怪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在西方文学史上上,这种现象被理论家定义为“现实主义对意识形态、对政治观点的胜利”。作家们虽然都会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但一旦他们秉承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真实地观察与描写历史与现实,那么,其作品倾向就可能走向本人政治立场的反面。 恩格斯在谈巴尔扎克的创作时说:巴尔扎克的同情心虽然是在贵族一边,但在作品中却毫不掩饰地赞美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英雄们。以此为证,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 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属于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拜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之赐,陈世忠一度摆脱了中共极左的“革命现实主义”桎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运用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五十年的沧桑变迁,写出了一部中国人的心灵苦难史。

谈到酝酿构思《白鹿原》的过程,陈忠实说自己“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其中的很多场景与细节,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出处。例如,有些小说情节是以关中、西安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被称为“白鹿精魂”的高尚人物,都有其现实的生活原型。例如,坚持儒家文化、处处与人为善的朱先生,其原型是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被中共活埋的白灵姑娘,其悲剧取材于革命烈士张静雯的遭遇。书中治病救人的冷先生,其医生形象来自《蓝田县志》。 ◎ 为获奖自我阉割,高调颂毛 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曾因一部《静静的顿河》成为苏共高官,陈忠实也同样因为一部《白鹿原》,一跃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受过苦,都曾在共产党的基层任职。 有国内评论家说:“《白鹿原》是从《静静的顿河》这棵大树上摇落的一粒种子。”陈忠实之所以能一度摆脱红色文艺之窠臼,与《静静的顿河》对他的深巨影响有关。他的《白鹿原》学习《静静的顿河》,以客观求真的态度,揭露共产党的血腥与丑陋。两部作品都同样遭受过政治审查与批评。

不同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后来为苏共的高压政策辩护,招致作家们的憎恶,而陈忠实成名当官之后,据说还保持了某种农民的朴实和谦虚。但是,从《白鹿原》出版后他的一系列表现来看,这位农民作家在精神上迅速地萎靡下去了,一蹶不振。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获奖,陈忠实修改了《白鹿原》,对作品实行自我审查。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奖的最高荣誉之一。1997年,该奖评委在评议《白鹿原》时出现分歧。陈忠实接受了要他修改的建议,删改了两三千字,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叙述,例如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论,还淡化一些性描写。 拿一本不明不白的修改版去获奖,陈忠实因此受到一些严肃评论家的批评,被指责为“迎合评委”,“对读者的背叛”,“向政治与功利的一次可耻的妥协”。 第二,自《白鹿原》出版后,陈忠实急于澄清自己的政治倾向,他转而高调地赞颂毛泽东,并声称自己的作品是“极力歌颂共产党的”。 第三,此后二十年,陈忠实只是“写写散文,随意写作”,不敢再以小说“妄议”中国政治历史。即使他曾酝酿过一部描写当下乡村生活长篇小说,也一直没有动笔。 ◎ 政治恐惧与科举文化后遗症 至今还有一些文坛批评家不能原谅陈忠实的删书行为,视他为“软骨头”。但我们可以用史学家陈寅恪的“同情之了解” 的态度,设身处地体察对方,把陈忠实的“软骨头现象”放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去看。 即使中共官方如此表彰陈忠实,至今还有左派人士称陈忠实为“反共作家”,指责陈忠实那一代作家“真真切切地颠覆了共产党的历史以及植根于这段历史的价值观。”长期以来,左派们所扣的上纲上线的政治大帽子,该书曾被广电部列为影视禁拍作品的麻烦,都令陈忠实气恼郁闷。他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产生了恐惧心理。 在八十年代中期短暂的政治艳阳天里,陈忠实开始构思《白鹿原》。当时思想解放的作家,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的写作手法,大胆反思历史,调动多种文化资源。这部小说可以归于的“新历史小说”、“寻根文学”一类,具有鲜明的反叛性与冒险精神。 然而,当陈忠实面壁六年,终于在1991年末写完全部书稿,时势遽变。“六 / 四惨案”震撼了世界,也窒息了一些自由写作的中国作家,打断了他们的脊梁骨。审时度势,心怀恐惧的陈忠实不敢把已完稿的《白鹿原》拿出来,他甚至和妻子说,准备不做作家去养鸡。直到1992年的一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传来,陈忠实预料形势将会宽松一点,才敢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并要求出版社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前去取稿。 从反叛到屈服,这对具有传统风骨气节的士人和现代独立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陈忠实既不是士人,也不是独立知识分子,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的乡村干部。文革时上五七干校,他的背包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毛选》,另一本是柳青的《创业史》。未曾吸收过更为丰沛广博的文学源流,又缺乏坚定的自由主义理念支持,陈忠实很容易就放弃自我的独立精神,随波逐流,回归毛时代的意识形态。 从现实功利角度来看,陈忠实也不能不妥协。中国文坛一直就有科举文化后遗症,古代文人以一篇文章中举,由此获得高官厚禄,现代文坛也有“一本书主义”。在海外自由社会,只有一本书的作家往往难以靠写作养活自己,但在中国,写出一本好书就如同中举,能使人登上文坛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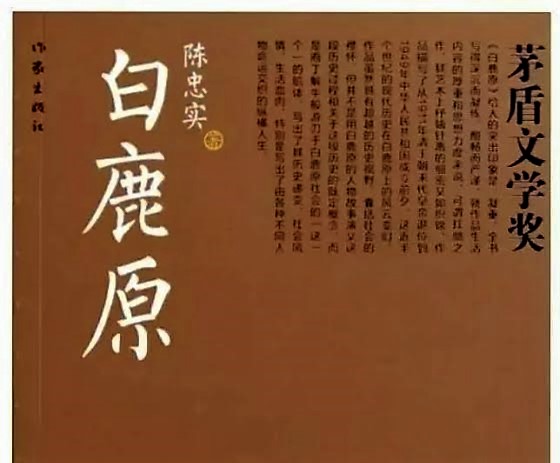
并不把文学当作自身的信念与生命状态,深知“向阳花木易为春”,陈忠实以中国人特有的方式——政治表态和声明,化解了他与中共之间的心结。《白鹿原》大红大紫,巨大的销量,使长期生活清贫的陈忠实跻身于“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 在离开人间时,功成名就的陈忠实是否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满意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里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在回归鲜红党旗的二十余年中,陈忠实不敢再触碰敏感的写作题材,精神上自我阉割了,创作力也因此丧失,他再也没能拿出优秀作品来。 谨以此文悼念陈忠实先生!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6月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