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һЩ���ģ������������������õ������� |
|
|
|
|
|
|
|
|
|
|
|
|
|
 | ��־С˵ �� �ڶ��� �d� ��55-56���T�T |
| | 55
�����Ҹ������簡�����ǻ����ˣ������뿪���ʱ����ֻ�������꣬�����ڻ����뿪���㣬�������߰�������ᣬ���Ѿ����������꣬������̫ƽ���лص���Ļ������ˣ�
�ҿ������㣬���������������ΡȻ�����İ�Ⱥ���ã�������Զ���Ҿ��ϵó����ˣ�ȫ�����ÿͶ������������������������ᣬ�����������������ˮ���������·������ˣ�����������Ļ���ǰ����
������ƽԭ��������������֦�����㽶����ɽ������ߣ����ߣ�Ҳ���գ��DZ���һ��������ɽ����һ����С���ϴ����������ı��������˷ܵ�ָ�����к���
��������ɽ����������
�����ǰ���ɽ����
���Ǿ������¥����
���Ǿ��ǹ���ɽ�ɣ���
�����������������ţ���
��������ţ��������ΰ�Ĺ��̣���Щ��������Щ����Ŷգ��һ���ϡ�ǵ��أ��Ҽ�������һ�����ϣ�ĸ�״�����������������վ�������������µĹ�����ˮ������������������ĵƹ���������������ȥ�����µĺ�ɫ���������еƹ��ճ���������Ӱ�ӡ��������������ţ�����������ˣ���������ֻص����������ֿ��������ţ���֣���ʱ��ĸ��Ϊʲô�����һص��游��ȥ�أ�Ϊʲô��һ��Ҫ�����뿪���ݣ�����ǧ��������ѣ�Ϊ��ʲô������Ϊ��ȥͶ������ô��Ϊʲô��һֱ�����������ҵ��游�Ǻ�����ֱ�������ϣ����Ž�����Щ��������Щ��֣���������ȥҲ�벻���������������Ҳ���ȥ���������������Ѿ����������̾Ϳ��Ժ��游�����ˡ�һ�е����⣬��Ȼ�����ػ��ֳ����Ĵ����ģ���ʵ���ò������ġ�
�����������Ǵ�ɳͷ�����Ƕ�ɳͷ����
һ�����������ĵ��������������г����ˣ�����������IJݵأ���Ư������ʽ������Ļ����Ҵ�����û�����������ĵط�����ͽ�����ɳͷô������ֵ����֣�
���������ϴ�ѧ������һ�����˽���������
˳������ָ�ķ������ϰ��ҿ���һ�����������Ļ�����Ӱ�������������ɫ�����ߺ�ǽ�Ĺ��
�����裡����˵�������ǻʹ��ɣ���
���������ϴ�ѧ��У�ᡣ��ĸ��˵�������ǻʹ�����
��ѧУ����ô��ѽ�����Ҽ�ֱ���������Լ����۾����������ҿ��Ե�����������ɣ���
����ú��ù�����Ϳ��ԣ���ĸ��˵�������ϴ�ѧ�Ǻ��ѿ����أ���
����һ��Ҫ�������������Ѿ�����������У���Ի�ס�ˣ������̾����˾��ģ���үү�����ҿ��ϣ�һ���ܸ��ˣ������˼һṩ������ģ��Dz��ǣ���
���ǵġ���ĸ��Ц���ش�
�Һܲ�����������������Ϊʲô���в������䵭�ijɷݣ���������Ͼȥ���룬���Ѿ�Ŀ��Ͼ���ˣ���������ô��ĵط�����ô�����ij���ѽ����֣���ô��ǰ��һ���Ҳ��֪���أ��ҷ·���һ�����εִ��С�ο͡����˺����źͰ�Ⱥ������һ�ж�����ĩ��İ�����������ҵĹ��磬�ҵ����ĵط�ѽ��
��˽�����ϴ�ѧ�����������֣�����һ��ɽ���Ƶ��Ʒ��ϣ�������һ����ͷ����С�������������������͵�С�������Ƕ�������δ�����ġ�
�����ϴ�ѧ��õ�ѧϵ��ҽѧԺ��ũѧԺ����ĸ��Ȼ����˵���������㽫�����������ҽ�ưɣ���
����ҽ�ƣ�������Щ�Ժ���
���������ҽ������ĸ��˵�������������ر𣬺������ڽ������Լ���������ҽ�����ҵĶ��ӽ���һ��Ҫ������ҽ�������Ծ��˼�����������Զ�����ʧҵ������
���ǵģ��ҽ���Ҫ��ҽ��������������ĸ������ģ�����Ľҽ��Ҳ�Ѿ���ֻһ���ˡ�����������־��Ҫ���ɽ����������־����������������һ�ξʹ���ʮ��ܵл�����������ս�������ˡ��Ӵ��ٲ�����ս����û�ел��ɴ��ˡ��Ҳ��ò��������ɽ����ĺ�Ը����һ��ѡ���ǵ�Ȼ�������������˵�ҽ���ˡ��������ҽ�����Ƕ��ѽ��ĸ�IJ�һ�������κõġ���Ҫ�����ϴ�ѧ��ҽ�ƣ��Ҳ����Կ����Լ�������ɫҽ���Ʒ��������������������ˣ�
��Ҫ��ҽ����Ȼ���������ڲ��dz�һ��ѧ����һ��ʮ����δ��������ѽ����֪��Ҫ����ҽ������������ѧ����ѧһ�������꣡���꣡ѽ����ô���£�̫���ˣ��Һ������̾ͽ����ϴ�ѧ�źã�
�����̣����̣��������ں���
�ҿ�����һ�����ٽ��ߵ���·��·���кÿ��������ӱ������������壬�����С������һЩ��Ư���Ļ�����
����ȸղŵ�һ���ƺ���խ��һЩ����ʵ�������������������Ĵ�ֻӵ�ص�ͣ�������Եú�����С�ˡ�
�ҿ��������Ҵ�δ�����ģ�Ҳ����Сʱ��������˵��ִ����������ϴ������ǵ������ڴ��ִ�֮�䴩��������֮�£������������������Ľ���������Ƕ�ô����С������Щ���ִ����ߴ�Ĵ����������İ�ɫ���ɫ���ϲ�װ壬���ˣ�Φ�ˣ������Ͳ�����ĺ��ߣ������ô��ΰ������Ը��������Щ���ִ����˳����������ˣ���ңԶ�����ȥ������������ҽ����־Ը�ڼ�ʮ����֮��Ͷ�ҡ�ˡ������ұ���������ס�ˡ����ƺ���С�ͻ�ϲ����Ҳ���Ҹ���һ��ˮ���أ�
��������ͷ���������ڽУ���������������ü�˫�ŵ��أ���
�Ҳ�������һ����ͷΪʲôҪ����������ͷ�������Һ�ϲ��������֡��ҿ����ˣ�����ͷ�������Ѿ��������ã�������һ����ֱ�ܳ��Ĵ���·��
ĸ��ָ������·��һ�����ӣ�������˵���������Ϲ�ϷԺ����Сʱ��������������ȥ������Ӱ�ġ���
�����벻�����ˡ�����˵����һ���Ҳ�벻�����ˣ���
������ô��������أ���ĸ������Ц�ˣ�������ʱ��ż����´�ѽ����
�����ţ��������ұ��������Ĵ����ţ����ˣ���ĩ�ؾ�ߣ���������������洩����̧ͷ��������Ÿ���ƽ�ӿ�����ת���µ�ˮ��������Ľ�����ӿ�����������ţ��������еļ����е�һ�����ֵ������һ��ʹ��֪�������ı����ĵط����������ֻص�����������ˣ������Ҳ��ٱ������ҿ��֣�ֻ����һ����п���ĸ�ĸп���Ȼ�������Ű������������뿪�㣬�����һ�Ц�������ˣ�
�����Ź�ȥ�ˣ��ÿ��Ƿ���ʰ���������Ҷ��ʱ�������֪�������Ͼ�Ҫ����ͷ�ˡ�
�����Ļ������ã������ǽ�����ָ����
�ҿ���һ�����Ĵ�¥��һƬ�����IJݵء�
����Ⱥ����Ⱥ���������˷��ڽ�����
��һ��Сɽ��һ��İ�Ⱥ�Ƶ꣡�Һ�ɫ��ʮ�����¥����Ȼ�ش����ڽ��ߡ�����ϡ�ǵã��Һ�С��ʱ���֪�����ˣ����������ӵļ��������������������
��������ͷ����
�������ڣ���
�����̣���
���������¹�˾����
�����ش�¥����
��һ�������ڽУ���������̶����
��������Ư����Ħ���¥���������ǻ�������ִ����Ҽ�ֱ�۶������ˡ��ҵ�һ�ξ��������н����ĸо������ǹ����ˣ�
�������ؿ�����ͷ��һ��������ͷ�ϴ���С���ӽк���һ�������ͻ��ģ�����˷�ӿ��ǰ�����ÿ͵��������С����˾�Ѹ�ٵؽ�һ�Ų�ɫ��ֽƬ�����ÿ͵�Ƥ���ϡ������涼��д����XX�ùݡ���XX���硻�ġ�
ĸ��ǣ����������ͷ���ҵĽŲ���û��վ�ȡ���Щ�ùݵĻ�����̾Ͱ�ĸ��СƤ�������ˡ�
����ã�ס�ҵ؆��ù��������Ǹ����������ǵ����Ц����˵��һ�治�ɷ�˵�������ҵ��־��ߡ�
���������Ҷ�����˵�������Dz�ס�ùݣ��Dz��ǣ�����Ҫ��үү��ȥ��үү������������ǵģ��Dz��ǣ����д�籨��үү�ɣ���
��籨֪ͨ�������ӣ�������ڴ�������������ô˵��֪�����£������̾�Ӧ���������֪ʶ�ˡ�����Ϊĸ�ױ�Ȼ�����һ�������ȴ�籨֪ͨ����ġ�˭֪ĸ�Ĵ��dz���������֮��ġ�
����û�д�籨������˵��
�������ʻ�������������ӆ��������ùݵIJ跿˵�����ȾͰȆ����ȥ�ҵ��ù���Ϣ��������
��һ�ڵ��صĹ��ݻ���������������ˣ������ڲŷ��֣���һ�IJ����Ǵ���Ĺ��ݻ��������Ҵ���һ�ڵ������������ô����˼��үү�أ������Ҫ�Ͽ�ѧѧ���С���Ҫ����Ц������ʡ�˰���
�������ȵ��ù�ȥס����˵�ɣ���ĸ�׳�����һ�£��ƺ��ڿ���Щʲô���ܷ���һ��ʱ�䣬�������ؽ���
��ϵ��ϵ����ϵ�����҆������ǵģ��ǵģ������Ŷԣ����跿˵����һ�溰�ư�������ι���У���ij���λ���ȥ�����ùݣ����ư����������λ̫̫�������ù�ȥ������
�ޣ������Ĺ��ݻ��������ҵļ��绰���Ҿ���������
���ˣ����ϻư����Ժ����������룺���ڵ��ˣ�����������ס�ùݣ�����ͻص�үү��ȥ����Ϣһ���ȥ����������Ҳ�ܺã���ʵ����Щƣ���ˡ�һ���糾���͵��������ܼ�үү�����أ�
56
���ϵ����X��û��һ����������ġ���Щ�߰˲��������ʽ��¥����Щ�����Ĵ���·�����������ˣ�Ư��������������Ŀѣ�Ĵ������У���Ĺ���ͻ�������ֱ���ҿ���Ŀ�ɿڴ��������Ǹ������ӣ���ʵ��ʱ���һ�ж�������Ȼû�ܵ�̫���ս���ƻ�����Ҳ���dz¾ɵ�սǰ��Ʒ�ˣ�����Ҳ��Ǽ�ʶ�٣���������ĩ�س�����ġ�
�ư����������ص�һ���˲�ߵĻ��������Ա�ͣ�¡�ĸ���˳�Ǯ���ҺܳԾ���̧ͷ���濴�����ⴱ�������ù�ʵ���ǹ����ɣ��㿴���Ȳ��������Լ�����ת�ģ��������������÷dz�Ư�����ˡ�����һ�������Ԫ˧��ġ���վ���űߴ��������ء�
���������ǵ��ù�ô��������Щ���ӵ���ĸ�ס�
�����ǣ��������Ǵ�Ƶ�ѽ����ĸ��˵��������ס�������Աߵ��������
�ɲ��ǣ��ҿ����ˣ��Ǵ�¥�IJ����������������Ǵ�Ƶ�������֣�����Ӣ�ģ���С���ӵĿ�����һ��СС����д���������������ɴ�ֱ�롣��
�����Ӽ��ڸ�¥���У��ܾ���խ�ͺڰ����ҿ����������������Ķ�������ĸ���Ѿ�ǣ���ҵ�����ǰ���ˡ�
����������Ҳ����Ķ�ȥ�ɣ��������룬���������ڸ�¥�����еġ��ȵ��ҿ�������ʱ���Ҳ�֪���ҵ��ƶ���ȫ�����ˡ�˭Ҳ�벻�����ڰ˲��¥�Աߵ�������һ��ʯ���̵�·���Ƶ���¥�ĺ��棬�Ƕ���һ������ʽ���ķ��ӡ���ȻҲ������¥�������ɺͽ�����ǰ������ǾͲ��̫Զ�ˡ����������硺�ļ�������д���Ŀ���Ƥ�ϵģ���������������֮�С�
�Ǹ��跿�����������ˣ������˲����ÿͣ����������ȵ��ˣ�����һ����������װ�˺�Щ��������������ǵ����ӡ���������ļ����跿���ܳ����ˣ��������ڵ��к��ÿͽ�ȥ��Ϣ��Ҳ���������ǡ�
���裬����Ϊʲô��ס�����أ�����ګګ����ĸ�ס�
������̫���ˣ���ĸ��˵��������ס���𡣡�
������ʲô��ϵ������ֻסһ�����ѽ������үү����������Ǹ��˵ģ�����
��үү����֪�����ǻ����أ���ĸ��˵��
������ô�籨�ģ�����˵������Ϊʲô�����أ���
����籨����ĸ�������������˵һ�䣬����̾������Ҳ������Ϊ����ۼ��������Ѿ��������ˡ�����ض�����Ǯ�����⣬û��Ǯ��ʲô��Ҳ�в�ͨ���������룬Ҳ�Ͳ������ˡ�
��������Ȼϣ����ס���������Ǵ�Ƶꡣ������ʹ�˵����������������ģ��Ҳŵִ���ݼ����ӣ����̾�����ס��õĵط��ˡ������Ҳ�û������ĸ���������Ϊ�Һ�Ȼ�뵽�Լ�������̫�������ף��������ס����ĩ����ͷ���ù�Ҳ�ܲ����ˡ������ڲ��õĽ��������һص��游���߳�Ϊ��鹫���Ժ��ұض��кܶ�Ļ��������ס���ģ����һ�Ҫס����ߵİ�Ⱥ�Ƽң�ס�����һ�㣡��������Щ�뷨���Ҿ���������������Ҫס���ǵ����ˡ�
��������ķ�����ʵ�ϲ����ܻ������������������ʹ�δס������Ư���ĵط������ݾ����Ǵ�ͷ�������������ù�Ҳ�ǹ�ʹ�����С������������ˡ�
ĸ����˯һ�أ�˵���ϴ��ҳ�ȥ���·������һ�¡�����һ��ʹ���ȥ���游��ĸ���Ҹ��˵ò����ˣ�̫�˷ܣ�����˯�����ˣ����ڴ��������Ӷ��ǿ��ֵĻ��롣
ĸ����Ϊ��˯�ˣ���ֻ��һ�ض�������������в跿Ҫ��ֽ�ͱ�ī���ҿ�������������д�ţ���֪��д��˭����д�˺ܾã��Ű���д���ˡ����ֶ�һ��Ȼ��ŷ�ã�����в跿����
������������һ������ź��룿��������ĸ�Բ跿˵������Ǯ�Ҹ��㣬�����١����������Ȳ�ġ���
���͵�ʲô�ط�����
�����ض౦·����
�����ض౦·һ���ĺŷ��������跿�ӹ��ŷ⣬�ѵ�ַ������������̾�Ҫ��ȥ�𣿡�
��������ǰ�͵�������Ҫ�Ȼ��ŵģ���
��û�����⡣��
ĸ���Ÿ�˭�أ����ڲ��롣�Dz��Ǹ�үү�����̣����ز���������ǰ���ҽ������ҵ�������ڵ��룿
�Ҳ�����װ˯������������������ĸ������ҵ����ʡ�
���ǵģ�����д����үү�����̵��š���ĸ�״���˵���Һ���ֵؿ�������������Щ�����ijɷݣ���֪����������IJ�����Ȼ���Ҿ�������ĸ��࣬��һ���Ѿ���ͼ���ι��ˡ�
������������������ȥ���������Ρ��Ҳ�����Щ���ġ��������������Լ������н��ͣ���ʱ������β�ͬ��������Ȼ�Ǹ���������������Dz��Ը����ҵģ�����ϲ���ҵģ�����ĸ������������ᣬһ��ֻ����Ϊս����һ�к���û�й�ϵ������ս��Ҫ�����ˣ����ǻص��游���У��游�������ʵ��ǻỶӭ���ǵģ����縸���Ѿ��ص����У�����ȻҲ��ͬ���ػ�ӭ�������Ҳ��븸����һʱ�����ܻ�����������������ȷ�ģ����Һ������ʱ����ܾ�Ҫ��һ���ˡ��������۸����ڲ��ڼң��游�Ļ�ӭ��Ȼ�����ҵġ���֪��һ����˵�游ĸ���DZȸ�ĸҪ����Ͱ��ö�ġ�
��үү�������յ��žͻ������������ǰɣ�������ĸ�ס�
�������ա���ĸ���ƺ����ҿ϶���
�ҿɱ������������ġ��Ҳ���˯��ȥ�ˡ��Ҽ��������شߴ�ĸ�����̾ʹ��ҳ�ȥ�Ͻ���Ư�������·������Ѿ������˶�������ϰ�ߣ����ٿ��ǵ��ý�Լ��Ǯ�ˡ�����Ϊ�ں���������̫�٣��ٺ�Ҳ��ò��࣬������ʣ��Ǯ�������ڵ��ó���á������뷨δ��̫���棬���ڵ�ʱ��ȴ��Ϊ�Ǻܺ�����һ���ڡ�
���ðɣ����dz�ȥ���·����� ĸ�״�Ӧ���ң������ǵ����¹�˾ȥ������������үү�Ļ������ˡ���
����Ȼ�أ�ĸ��������������ɵȲŴ�Ӧ����ǰ��ȥ�ġ�
ĸ�״��ҵ����棬��������������ɾ�����·��̫ƽ��·����һ����Ƶ�������ֱ���ӱߵ���һ�ξͽ���婿ڣ��ǹ�������ĵط�֮һ����婿�������ʹ��������ʱ�����������ӳ���һ�η��̸�ҥ��
����װ�ѣ�ִ��ͷ��ִ����婿ڣ���ͷִ���������������֡������������ģ�������ƨ�ɣ�һ·������婿ڣ���ƨ��û��������ƨ�ɣ���
���ڵش������Ĵ࣬������һ�����������������������˾�һ�볪�����ҥ���Ҳ�����婿���ʲô�ط���ԭ���������
�ߵ���婿ڣ�̧ͷ��ʮ����İ�Ⱥ�Ƶ꣬��Խ��Խ��Ľ������Щ���ַɳ۵�����ȴ���ŵ��Ҳ��Ҿٲ���������������Ӽ��ˡ�
ĸ�ױ���˵�ϴ��¹�˾���·�����������婿�����Ȼ˵����ȥ�ˡ�������Ϊʲô��
����û�����𣿡�ĸ��ָ����Զ������ʮ��Ĵ��á�
������������ֻʣ���˹Ǹ��ˣ���������Ȼ�DZ�ս��ٻ��˵ġ�
�������ǵ��Ķ�ȥ���أ�������ĸ�ס������ڵص�ɽҰ���������ˣ���������һЩ����Ҳû���ˣ�������Ǹ���ĸ�ף����Ǵ粽���еģ�����Щ�����ľ����������ܰ����������ӳ��Ա�������婿ڶ���Ǵ�ٻ��ꡣ��ĸ��˵������㵽��һ�Ҷ����ԡ���
���Ǿ���һ����Ľ������ҿ����������֣�������ϷԺ�����ſڹ���������ĵ�Ӱ����ͻ������Ķ��ǽ��۵�����ˡ�Ů�˵ij�ȹҷ�ء�����̹��¶�ۣ���Щ������¶���������ȣ���������������Ů�ˡ��ҿ�����ͷֱ�������϶������ˣ�������������û�������������ǵ����Ρ�����æ͵͵����ĸ�ף�������û��ע����ڿ���Щ�����˵��ͻ����Ҷ�����ûע���ң�����������ǰ�治֪������ʲô���ȵ���ע���ҵ�ʱ�����Ѿ����ٿ���Щ�ͻ��ˡ�
���裬������衷��ʲô��˼������ָ��ϷԺ���ġ������ӳ����һ�Ź�棬��������һ���ֲ�����Ӱ��һ�ѻ���һ�����������Ů�˴��������Ĺ�װ��ȹ��
����Ҳ��֪������ĸ��˵��������һ����Ӱ��Ƭ�������ˡ���
�����ǽ������Ͽ��ⳡ��Ӱ���룿��������뿴��Ӱ��û����Ӱ�ܶ����ˡ�
�����ȿ����ⳡ��Ӱ��ɲ����Կ�����
ĸ�״����߽�����ϷԺ�Ĵ���������Щ���������ڵ���Ƭ�����˺ð��죬��˵��
�����Կ��ģ�����һ����������Ƭ����
����ô�������������ɣ����Ҹ��˵�Ҫ��������
���õģ�������ȥ���·�����
���ǺܺϺ����ģ��Dz��ǣ�������Ư�������ĵ�ӰԺ��Ȼ�ô��Ϻÿ������·���
���������߽�һ�Ҵ�ٻ����ͯװ����ĸ��ϸ�ĵ�Ϊ����ѡ��һ����װ���Ҳ���ϲ����װ��������û������������Ը��ˮ��װ�ģ�Сʱ���Ҵ�ˮ��װ������Ȼ��Ϊˮ��װ���ʺ��ң���ϲ������ϲ��ˮ�֣�һ����ˮ��װ�Ҿͷdz�մմ��ϲ��
��û��ˮ��װ�𣿡�����ĸ�ס�
��û��������ġ���Ů��Ա˵��
��ˮ��װ��������С�����ġ���ĸ��˵��
�Ҿ��ú���Ϊ�顣������Ҳ���ˡ�Ȼ�������кܲ�������Ϊʲô�Ҳ��ܴ�ˮ��װ�أ�
�Һܲ�Ը����õ�Ա�ڲ������Դ��ҵ����·����ڴ�����ǰ���Ҿ�������ȫ��������һ���ˡ��̿���װ����ƤЬ�����O�ӣ�������ᣬѩ�׳��£���ֱ����һ������ӵ��ˣ�Ȼ������������������Ǹ���ᣡ����Ϊ����ˮ�ַ��Ƚ�����һ�㡣����������һ�������������ֵģ���Ϊĸ��˵��
��ȥ��үү����Ҫ�����������룬ƯƯ�����IJ���ѽ���㿴���������Ӷ�ã�үү������һ�����ͻ�ϲ���ģ����μ����ӡ���Ǻ���Ҫ�ġ����Dz��ܴ��ú�����������ؤ�ƵĻ�ȥѽ����
�ǵģ�һ��Ҳ���������Dz�������ؤ��ػؼҡ�
����ô����ʲô�أ�����˵�����������·�ô����
����ҲҪ��һ�㡣��ĸ��˵��
�����ˣ���ƤЬ��������һ˫����ƤЬ������Ʒ�������˼�������������Dz�û���·���
���һ����·�������������Ϊʲô�����·���ʱ����������˵��
���м����·��Ҷ�֪���ġ�����Щ�·��ں���˵����������ϲ��������������������Ե�̫���������Ҳ�������ΪʲôҪ����ʢװ�����������Լ�ȴ���ǜʱ��Դ���Щ�������·���Ҳ��������Ǯ��Ե���ˣ��������롣�Ҳ������ʣ�ͬʱ��ʼ����������Ҫ����Ӱ��Ҫ������������ϷԺ������˵��Ʊ��Ҫ������Ǯ�ġ����ǣ��Һܿ����Լ���ð�ο�������Ҫ����������үү������ʲô�أ�
ĸ������װ���ҵ����µ�ֽ�У������ڰٻ���˾������һ�ء�Ȼ�����ȥ������������������Щ�������豸��ٻ������լ���Ŀ�ij���ͬ�����Ի����ң�ʹ���ۻ����ҡ�������ɫ��װ������������ʦ�߹���������������������һ�����һ���Ϊ���Ǹ���ʿ�أ��ǵ綯������ʼ����ͷ�Ϲ�����ʱ��ʹ�Ҿ��첻ֹ��
�綯�����������Dz����˵��·��������������ڻ�������������ʱ�������ͷ���Լ��ˡ�
�ص����磬ĸ���ʲ跿�Ƿ����л�����û�С�
����û�п���ȥ�أ���á����跿˵������˵������ǰ��ȥ���е����һ�¾���ȥ����
��ǧ��������˰�����ĸ��������˵���������ϻ�����Ҫ���������ŵġ���
��û���⣡û���⣡������������跿˵��
���������ĸ�ײ���������Ȼ���ҿ��Ըо��õ����������ġ���һ������Ҫ�����š���������û������£����������µش��ҵ�����ȥ�Է����Ҵ����ҵ����·���ͷ����ù�����������Ҫ��������Ŵ���ȥ��үү�ģ����Dz�֪ʲôԵ�ʣ�ĸ���Ҵ����á�Ҳ������Ϊ��Ӧ���ȴ�ϰ��һ�㣬Ҳ������Ϊ�ӽ�����Ҿ���Ӧ�ô��úúõġ����Լ�Ҳ�����룬�����ҾͲ������ˡ����Լ���������õ�һ��dz��ɫ���ۣ�����������Ь�ӡ���Ư�������Dz���������˼�˿�����Ͷ������㣬������������δ����������ζ�IJ��ȣ�Ҳ��δ��������������IJ�����������͵ij�ɫ�ڵƵĵƹ����棬�������װ�����Ľ����һ�������ϣ��ҵ�һ��������ӣ��˷ܶ����ŵس�����һ�ٲ������͵ķ��ˣ�����ȴ��Ϊ�Ѿ������������ˡ�
�ڳԷ����У�ĸ�ױ��ֵú���죬����������ŵ�ԣ������ϡ�����ϷԺ��ȥ����Ӱ��
������ӰԺ������������������һ�ν���Ĵ��ӰԺ���ڽ����������DZ���Ӧʲô�˲���Ȼ�����ڵ�ʱ����ȴ�����ǽ��˰�����Ժ��һ��ĸ����û�ϷԺһ���ˡ��⿴��ӰԺ������߲���ƹ��һ����ͣ��·�ߵ�С�������Ǿ��㹻ʹ������Ŀѣ����һ��ʮһ�������꣬������Щ������������Ľ֮�⣬������ʲô�أ�
�Һ��삆�Լ�����ô�������游��������һ�ε�����������Ӱ��ʱ�����ɵ��ǻ���С���������ģ������ҵ�����Ҳ��Ȼ����˼ҵ�Ư��������Ҳ��������ǵľ�ʽ��
���ŵ�ӰƬ�ӡ�����衻�Dz�ɫ�ģ�����ǰ��δ������ɫ��Ӱ����һ�¿��������ס�ˡ�˵ʵ�ڵģ������һ�ο���Ӱ�������������Ķ��Ǻڰ�Ƭ���¸����꣬�Ҳ�������Ӱ��ʲô�����ˡ��Ҵ���û�뵽����Ӱ����ô�õ����ܡ��Ժ��ҿ���ÿ�����ϣ���Ҫ������Ӱ�ˡ�үү�ض��������ҵģ����ܻ�ʹ���ı�����ĥ���������һ���գ�������Ӱ��������˵��Ȼ������ʲô�����ġ�
������衻�Ĺ����ҿ�������Ϊ��ȫ�ǽ�Ӣ�ĵģ���һ��Ҳ������������������ں�ֻ�������С������Ҳ����һ���Ӿ���Ӧ�������Ӱ��̫��Ľ��࣬������û��Ū�����һ����ͷ֮ǰ����һ����ͷ�Ѿ����ֶ�����ʧ�ˡ��ҿ�ʼ�о��������Ӱ���й����������ͬ��ͬʱ�Һܿ�ؾͰ�������ЩѤ�õIJ�ɫ����װ��ʢ������ij��档����ʹ�Ҹж���Ƭ�е�����Ů���ǵĸ��������ڴ���Ժ��������Ů���������Һ����ӡ���Ҿ��úܺ��������뵱�ҽ��������ȥ��ѧ��ʱ���ұ�Ȼ�ᵽ���Ժȥ����Щ���ŵĸ質�ģ���ŵ�ʮ�����ҾͿ���ȥ��ѧ�ˡ�ʮ���껹�������أ����Ƴ���ʱ�䣡Ҳ���ҿ���Ҫ���游�������ҳ���ȥ��ѧ�գ�ֻҪ�ҵijɼ��ã���һ���ϵġ�������Ļ�ϳ��־��ǽ������䳡ʱ��˼���룬���Ϸ��һ�����磿�����Ҳ��������ж౯����Ϊ��̫�˷��ˡ��Ҹ߸����˵ؿ�������ɢ���Ժ߸����˵ظ�ĸ���߳��˴ԡ�
������ֵ����ף��������ӣ�ֻ��һҹ���ҴӴ˾�Ҫ�����������������֮���ˡ������Ƿ�������婿ڣ����ʮɫ����ƹ�����ҫת������·���������طɳۣ�����ĺ���ڿ����л���һ�����ĺ��ߣ��������ƵĴ����ϴ�����͵����֣��齭�����ϵƻ�Իͣ�������У��Ҹж����ˣ�������ʵ�����ǵģ�һ���Ҳ���٣�������������Ĵ��е�һ�����ˡ����ǹ����ˣ���û�п��ѣ���û��ս����ֻ���Ҹ���ֻ��̫ƽ��ֻ�вƸ�����ֵ����ף���Ҹ����ӵ�ǰϦ�������������Ҿͳ�����ô����������������ˣ�
�����ڽ����������������������硣һ·��ĸ�����ҷ����������ֱ����Ӧ�����ҿ���ʲô��Ҫ�ʡ�
����һ�ж����Ҷ�������ģ������ޱȵ��ջ�
�ص����磬ĸ���ʲ跿�����ͳ���û�С�
���Ѿ��͵��ˡ����跿�ش�˵��
�������أ���
��û�л��š���
����˵��Ҫ���ŵġ���Ϊʲô�����أ���ĸ���ŵ������������������û�У���
�������ģ����跿˵�����Ǹ���˵��û������ˣ���
����ַ���ˣ���ĸ�������ʡ�
��û����������˵�����������Ѿ��Ͳ����ˡ���
�����ڣ���ʲô������
�����˺ü����ˣ���
��ʲô����ĸ����ɫ��Ȼ����˲Ұס�
���ǡ�����˭���ˣ������̲�ס��������⡣
��үү�����̣���ĸ��������˵�����������ҵĶ��ӡ������������������������˳����ˡ������ǡ����������˲��ã������㡭����
үү�������˺ü����ˣ������������������Ҹողſ����Ҹ��Ĵ��Ű��������ţ���ͷ����֪����ʼ�ղ���Ϊ�ҿ��ġ�
���ڴ�δ�����үү�����̣����ڻ������������ĸ����Ѿ�̫�࣬��ȵ��긶�������Ļ��࣬�ҵ�һ�е�ϣ�������ڶ��ѳ�Ϊ��Ӱ�ˣ�������һ���������մ��������ӵ��ˣ������˶��ˣ���Ȼ�أ�ħ��ʧ�飬�ӿ��е���������
��������������ǿ��������������ǧɽ��ˮ������Ҳ�������Լ����ұ����ˡ����˵��ڴ���ʹ����������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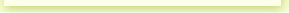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