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һЩ���ģ������������������õ������� |
|
|
|
|
|
|
|
|
|
|
|
|
|
 | ��־С˵ �� �ڶ��� �d� ��74���T�T |
| | 74
��Ϊʱ�ֲ��ã�ĸ���Ұ�ؼ��о�ס���ұ�����Ը�⣬���ڻ����ֲ���ĸ�ļ�ֶ�����⡺��Ѩ����Ĵ������ˡ���ʱ��պ���һ����Ӱ�����ݣ�Ƭ���ǡ���Ѩ������һ����д��Ժ�ĺ�Ļ�ĵ�Ӱ���ҿ�����������������ľӵļ�Ҳ�͡���Ѩ�����ƣ��Ҿͽ�������Ϊ����Ѩ���ˡ��ⷿ�ӹ���ÿһ������һ���ߣ����ܶ������Ǻܶ����ߡ�
�ص����У��ұ���ǰ���Ӽ�Ĭ����˭Ҳ�����ǣ����������ڣ���Ҳ��һ���ߣ���Ȼ�ĵ���Ϊ��һ�㣬������������ͬ·���ˡ��������߶�������������ѡ��Դ���һ�����������ĸ�ӵĶԻ�֮���Ҳ�����Ϊ������ɭ�Ĵ��ù������ҵ����ѣ��ҿ�����Щ�˵��ģ��Ҳ��ٵ�����һ���ң�ֻ��Ϊ����һ���ڵꡣ�Ҷ��κ��˶���������룬�����ҵĸ������ڡ��ҷ����ҵ�ȷ�����������������û��˿�����ϼ���Ѫͳ����������û�����ǵ���խ����������Ũü��û���ǵ����㶸ֱ���ִ�һ��¡���ӥ�ǣ�Ҳû������һ���ֱ������Ŀ������ӣ�û�����ֽ��ڷ����͵ĺ�����ţ�۰㱩¶������û�����ָ�Ӳ���ĺڷ����ҵ���ò�ǿ�Фĸ�ģ����䲢����˶�̫�϶��������Ļ�������ʱ�����滳�ɣ��������ڻ������Dz����п��ֵġ������ҵ���Զ���䵭�����������ҵ��ɻ�������Դ������ŮҲͬ������Զ������û�л�˵����ֻ��Ϊ�������ı�����ˣ�Ȼ���������Խ�Ϊ�º͵�̬�ȶԴ����ǡ��������ǽ����绰����������֮�⣬��������һ���ľͿ��ó�����ί�εijɷ����ڣ����ܾ�������Ŭ����Ҫ��������ʮ�������˼ҵĹ�ʧ����Ȼ�������ɺ�ǵģ�����ȷ�Բ������ǡ������������ҵĵ���Ѫͳ�����ң�Ҳ�����ֻ�Ǵ�ҷ�����������һֻСèС����
��ֻ��һ�����ͣ�һ���ȼ�Ժ���ķ��͡��ҿ��ú�����������ҵ���Į��Ȼ�������ڵ�ԭ��ģ�������Դ�ĸ��̬���ƺ��й�������������ôһ�����顣ֻ�����Ĺ����ס�������Ϊʲô�������ǣ������ҵ��������������������ǣ��������������һ���ܶ࣬�����ƶϵó�����Ҳ��Ը��ȥ��������֮���Ҷ����Ѿ���ȫ�������������Ĺ��Ѿ���������������֪���Dz��Եģ�Ȼ��ʮ�������к�����û��̫ǿ�����ǰ���
���������д��㣬�Ҷ㿪��Щ�ˣ����˳Է����ò���������һ��֮�⣬�Ҿ����ز������Ǽ��棬��������ڷ������ϰ���Σ����ص������ѧ�͵����ϡ��Ҝʱ�Ͷ��ʡ������ר��ѧУ�������и��б�ҵ����Ҳ�г��б�ҵ�������еĶ�����������ˡ��Ҳ��ܽ����κ��˵Ķ��ݣ���Ҫ��ǰ�����������Լ�֧���Լ����������ܿ��Ϻ���ѧУ���ܿ�ͻ��к����Ļ��ᡣ����ˮ�֣����е������������ȥ����ĸ��Ҳ�����̿������������ͥ�ˡ�����ʱ������˭�����ղ��շ���������Ҫ�ˣ��ҽ���Զ��Ҫ�ٿ�����������Ҫ��������Щ�ˣ����������ǿӲ�������������ĸ������ڣ�����Ҳ��Ҫ����
��Ȼ�����ս�����٣���ʲô������̸���Ҷ�����һ�����һʱ��û��ʲô���㣬���������ݵ��˶�û�д��㣬�ң�һ��ֻ��ʮ����ĺ��ӣ����ж����ж������أ�
ս���Ѿ�ȼ�յ��������ˡ���ϣ奲����ڼ��������ϡ���սһ����������������Ȼ�Ƿdz��Ի�ģ���Ϊҥ�����ϸ�ʡҪ�������������������������������ս��������ҥ��˵��Ҫ�����ˣ������ˣ������������ơ�������ô���£������˲���������Ҹ������������ʱ�Ҿͺ���Ϊ�Լ��ij�·�����ˡ�˵���ģ���Ȼ�ǵ��ĵġ�
�����˿���Ȼһ��Ҳ���������б������ǹ����˵���ɫ���ڽ��ϣ��������ڴ�̫�����£�����ҹ���ĵƹ����棬���ٿ�������ææ���ˣ�������������еء��н֡�������ˬ������ɴ��װ�������ػ���ߡ�ȣ�����������һ��ɢ����һ��̸Ц�����������ٶ����˿ڵĴ�Ľֵ�������װ諳��裬���ݽṹʽ������Ʒ���࣬�ƺ���Ӧ�о��У����������·��ͬ��ȷʵֵ��������ǡ��н֡������һ�ֹ��������Ⱥõ���Dz֮һ���롺���衻һ��������
������ս����ʱ�����յ��ľ���֮�£�������ȫû��˿�������ķ�Ӧ���෴�أ����Ǹ����Ե������ˡ���Dz�ij���Խ��Խ�࣬�ij������ֳ��׳��֣�����������賡Ҳ�ҳ��������ƺͻ��ƣ�д��ʲô������ʺ� ��������Ⱥ��֮�����������ϷԽ��Խ���ƣ�ʲ��ʵػ���ʩ�� ����ɽ��槼���֮������к��ٵĶ������ˣ�ʲô�������裬�������صĹ���ƶ����˳��������Խ��Խ�࣬������ҹ������������֮����ɫ���Ϸ������������������������ʳ�Ů�˵�̻��¶����ʱװԽ��Խ����������С������ʽ������һ���ľŵģ���ӰԺ����Խ��Խ��¡�����»������Ǻ��ݿ���Ӱ��ҪԤ�ȶ�Ʊ���������DZ���ǰ���ӷ������������ս����Ϣ��
�������ģ�������������˵��
��������������ʲô��ϵ�������������ѣ���
û������Ϊ�������ء�
��ֽ�Ѿ���Ϊ�����˵���ͨ�е�ֽ�ҡ���Ϊ��Ԫȯ��Ԫȯ������һ����ü��Σ�û����Ը�������֡�ʪ�D�D�����˵���Ƥ������˼��˵��Щ��Ʊ�����ն���̫ʪ���ղ��ŵġ�
�Ҷ������������û��ʲô����Ӵ��ġ�����֪���Ķ���һ�۰�צ������żȻ�Ͻֵ�Ƭ��۲졣ӡ��������������������кܶ�IJt�⡣Ҫ�t�ʱ��������Σ�Ҫ�t�ʱ�ľ��ƣ�������һ��ʮ���꺢�����ܵ��¡����ҵ����У�ֻ�б��ܵض���δ����ս���Ŀ־��ֻ�ж���������롣�������������е���Ժ��������У��ҵ��ľ��ƺ���������һ�־��磬ʹ����붼�кͷ�����Ҳ�����������������ϣ���뿪������У�������ս��û�У�������ѧУ��ȥ��ˮ���ƺ�����Ψһ�ij�·��
���£������żҹ�ȥͶ������ĸ��Ҳ�����ߡ�������ֻ˵�ǻ�ѧУȥ���ߺͿ���ͬѧ���ҵ��ж������൱���ɵģ�û���˹��ң�ĸ����Щ�����ƺ����쵽����ҽԺȥ����������Ҳûע��ҵ��ж���ֱ�������Ͽ���¼ȡѧ�������֣��ҲŸ���ĸ�ס����Լ����˵úܣ���Ϊ�ҵĶ������ξ�Ҫʵ���ˡ�����ѧУ��ʡ����ѧУ�����˻�ʳ��һ�ж�����ѵģ���������Ϊĸ�ױض�����˵ġ�˭֪���������Ϣ�dz��䵭��
����ΪʲôҪ�������أ���������˵���ҵĺ���Ϣ�Ժ�ֻ���䵭���������ҡ�
��������һ�����ı��ѽ������˵�������ҽ����������������������������
������꼸�����ֻ��һ��ˮ�֣���֪���𣿡�
����֪�����Ҿ���Ҫ��ˮ��ѽ����
��Ϊʲô�أ���
����ˮ�ֶ��������ڣ�����˵�����������Ķ������Ķ�ȥ��һ��Ҳ���ܾ�����Ҳû���˸������ܣ���
�����ϵķ��˺�Σ�յ��أ���֪���𣿡�
���Ҳ��£���
�����ܲ�ס�ġ���
�����ܵ�ס������˵�������ܷ�����ô����������Σ�գ��ܱȼ������ºõö࣡��
����Ϊ�㲻��������·����
��Ϊʲô��Ӧ�ã��ж�־���ĺ����ҵ�ǰ�̾����ں����ϡ���
���Ƕ���ֻ������һˮ�ֶ��ѡ���ĸ��˵��
��ˮ�־��õ�������
��ϣ�����������а�ȫ��ְҵ��ĸ��˵������ֻ����һ�����ӡ��Ҳ����㽫��������һ��ˮ�ֶ��ѡ����ߣ�����������ʵ���ϲ��������������ĩ�����á���֪���𣿺�������ʱ��һ����ؼ�����½�أ�ʮ�����ز��˼��硣�����������ʵ�ʱ���٣���籩�꣬���������ʱ��࣬�Ǵ�һ�߲�����ѽ����Ҫ˵�Է��ˣ��ε����������ܶ��������������ģ�Ż�����Ƶ�֭ҲŻ�����ˣ��˿ͻ������������ܣ���Щˮ��ȴҪ������������һ��Ż��һ�滹�øɻ��Щ����̫�����ˣ����������ܹ��������ġ���
���Ҹող�˵�����𣿡��Ҽ����˵���������������࣬��һ��Ҫ������Ҫ�Լ�ȥ�����Ҳ�Ҫ������������Ҫ�������Ҳ���Ҫ����һ��Ǯ�����ٳԷ���һ���ף�����ѧУ�Dz�ҪǮ�ġ���
�������ڶ����Ǯ����Ӧ�õģ��㲢����˭ʩ�Ρ���
�����ǣ����������ģ��Dz��ǣ�����һ�ᵽ��Щ�����оͲ����������������˵�ҷ����̳��游�Ų���Ȩ����ֻҪ��Ǯ������ѧ��ҵ���Բ��ԣ���
ĸ����������Һð��죬˵����������ô֪���ģ���
������ô��֪��������˵��������Ϊ�һ���С����ô����
Ҳ���ҵ�̬������ʹĸ�����֮������˵������֪������Ϊ�˱�����������˲Ʋ��ļ̳�Ȩ����ᰲȫЩ������ô���ҵ����岻�ã���֪�������չ�������ꡣ��ְ�����ʲô�¶�������������Ϊ����İ�ȫ��Ϊ�����ѧҵ�����������������������
�ҵ�Ȼ����ĸ�����⣬�����������ĸ�ӵĶԻ�֮ʱ�Ҿ������ˡ����ǣ���������ȴ���������˼һ�����ĸ��֪��������֪������ĸ�ӵ�̬����
�����ѵ���������Щ�ֲ������Ų�������㽫����Զ��ǰ�̣���Ҫ�����Щ���������˼Ұѳ��ŵļҲ���ֻҪ��ѧҵ�ɹ������������ı���ЩԶ�֪���ٱ��أ���Ҫ����һ�㣬����
ĸ������ĬȻ�����Ϊ��Ϊ�˼Ҳ����ѹ��ء���ʵ�����ں����Ҹ�������֪����֪���ҿ����ж��ټҲ������ҨD�D�뵽������ҵĻ��ͳ�ڶ����ˣ�
���Ҹ�����û���ʸ��һ���Ų�����̸ʲô�����������أ���
����ôû���ʸ�ĸ����ɫ��Ȼ�ر��ˣ���С���㽲����ʲô������
���ҽ�����ʵ�ڻ���������Цһ����˵�������Ҹ�����û���ʸ����
��С������ĸ���ɻ�������ң������ڽ�ʲôѽ��үү��������д�������װף�������������ͷ�����Ǹ�����һ�����ݣ���ʮĶ����Ƕ��ø����ң������ص�ȥ�ʹ�����д��������ʦ�ģ���
�������������������������Щ�£�Ҳ����ע�⣬���������Ϣ�Ƕ�����Ҫ��������˵�������Ƿ��ҵ������Ҳ�Ѿ������游�����������ˣ�Ӧ����û������ġ�������ĸ��Ϊʲô��Ҫ������̸�����أ�
����Ȼ�����������ĸ��˵����Ҫ��Ȼ�����ܹ����������أ���
����������������û�й�ϵ���ҵ����еĺ�����תʢ�ˣ��������˼���Ϊ����û�м̳е��ʸ�ģ��Ͳ�����Ҳ�ò���ʲô�ġ���
���Ҳ������㽲Щʲô����ĸ��˵�������Ѿ������㽫���μ��ⳡ�ּҵľ��ף�Ҳ��ϣ����̳в�ҵ��ֻϣ������־����ѧ���ˡ�������һ�����˼���û���ʸ���һ�仰���Dz�ͬ��ģ���û���ʸ�˭���أ���Ҳ�Ƿ��ҵ������
���Ƿ��ҵ�����Ҳ�����Ц��һ����������Ƿ��ҵ���������ΪʲôҪ�����ضԴ����أ������˲Ʋ����ǵ�̬��Ϊʲô��Ȼ��ˣ�Ϊʲô�ҵĸ�����Ҳ��ˣ����ǣ�����˵��������ĸ�Ŀ������������Ƿ������ﵱȻ����ȷ�ġ����Dz������ɵġ�Ȼ��������ĸ��ΪʲôҪ���������������أ�����ԶҲ�벻ͨ��Щ���⣬Ҳû������ȥ�ҳ�����������������һ��Ĵ𰸡���֮���������Dz��Ƿ��ҵ�����Ҷ���Ը�������������干ͬ������ȥ�ˡ������Dz��Ƿ�����������������õ�ֻ��ʹ�ࡣ�Ҳ�����Ϊ��Ҫѧ�Ѷ�����ū���ϥ���Ҳ��ܽ�ĸ����ȥ���ֶ����þ̵ĺ���ͥ��λ������ұ����ߣ�����ѧУ����Ψһ��·����Ҫ�뿪��������Ѩ����Խ��Խ�ã�
��ʲô��������̸�ˣ����Ҷ�ĸ��˵�����Ҿ���Ҫ������ѧУ����һ��Ҫͬ����У���
���Ҿ��Բ���ͬ�⣡��ĸ��̬�ȱ��Ҹ���������Ҳ�ϣ���ҵĶ��ӽ��������Ǹ�ˮ�֣�ȥ������Ʈ��������������ѧ����ƺ����Ƶ����ӣ���Ҫ�������еģ���������й��Ĺ�����Ҫ���Ϊ��ѧ�ʵ��ˣ���
����Ҫ����ʲô�أ���
����ҽ������
���Ҳ���ϲ����ҽ������ֻϲ����������
����ҽ��Ҳ���Ժ���������������ϵ�ҽ������
������......��
�����ҵĻ�����ֻ����һ�����ӣ�һ�еĴ��㶼��Ϊ����á���ĸ���е�˵����С������Ҫȥ�Ϻ���ѧУ����ʹ��Ҫȥ��Ҳ�ȵ����б�ҵ��ȥ�����б�ҵȥ���������Ǹ���Ա��������ȥֻ�����¼���ˮ�֡������𣿡�
�����ǣ���Ҫ�������ס��ĩ����......��
��ʲô�������ˣ��ǻ��ں���̶̵ļ��깤���أ���ĸ��˵����С��������Ȼ���������࣬�������Ը��ˣ������㾿�������Ǹ�С���ӣ����ò��࣬Ӧ�����軰�������Ѹ��ж��꣬����ʱ������˳�����ˡ�������Ŀ����ֲ�ͬ�ˣ�����ѡ�����·����ҽ����������Ա����������ѧ�ң�һ�ж�����㡣������������ϣ������ҽ���ģ����ϴ�ѧ��ҽ�����������ģ���ϣ�����ܹ�������ҽ�����ң�Ϊ�˽�������㣬��Ӧ��ת�����ϸ���ȥ�����С���
�����ǣ����ܹ�������ѧ�𣿡��һ��ɵ�˵�������ǻ��Ǯ�𣿡�
�������Ѿ�̸���ˡ��������Dz�����ġ���
��ֻ��δ�ذɣ����������������������Ļ���
������Ķ���ɣ���ĸ��˵������Щ��ͥ���£��㲻Ҫȥ�����ˡ�һ�е����鶼�����أ����ǽ�������һ�費�ڣ�Ҳ������ʦ�أ�һ�ж�Ӛ������ʦ�ˣ���
������������˵�����Ļ��أ�����������仰�����ѹ��ˡ�
������һ��Ԥ�ȵĴ���ѽ������˵�����б������������ʲô�أ�ϣ������ʱ������ϸ��в����������Ͼͺ��ˡ���Ҳ�����ĵ�ҽԺȥ�ˡ���
�����Dz���Ҫ����������֪�����IJ�֢���أ�Ҫ������ȥ�Ǻܲ������£����ض�Ҫ���������ˡ���������һֱ������ĸ��������������⣬��������������װ����֪���ˡ�
����˭������ģ���ĸ���ɻ�����ҡ�
�����Լ�����ġ����������ػش���ʵ�ϣ����ǴӺܶ�������ġ���Ѿͷ�������Ķ��ҽ����������Ҳ����ԼԼ������й�ĸ����Ҫ�������¡��������Ĺ�������������ˡ�
����û�����������ء���ĸ��˵����˵�������ÿ�����ֻҪ���ض��ķ�����Ǣ�ƾͺ��ˡ��㰲�Ķ������ɣ�����������ò����㵣�ĵġ���
��������˵������֪���Dz��������ض����Ƶġ���ѧ��ʦ�������ض������Ľ�����ȫ����ֻ�м�����ʿ��������û�������豸�������⣬�����У�ĸ������Ǯ���������氺�������أ���֪������ڲƭ�ҵģ�������Ϊ����С�����ء����Ѿ��ǰ�������ˡ��˼�˵��ʮ���������Ѿ������ˡ������Ҳ��������Ѿ������ˡ���������װ���������Ҳ�Ը��ʹĸ��֪��������Ϊ�����ǡ�������˵������Ҫ�Ұ��Ŀ����ϣ��ҽ�ȥ�Ժ�����ȥ���ơ��ҹ�Ȼ���ǣ��������ҵĵ��ǵ���ʱ�ű�¶�ɡ�Ŀǰ��¶ͽȻֻ����ĸ�����Ƕ��ѡ�
���ò��ˡ��Ҿ���ĸ�Ļ��Dz��ò����ġ������Ҳ�δ��̫��Ĵ���ʱ������������ҽѧԺ���ҵ����е�Ը����Ȼ���������ҡ�������������һ���ɻ�����ʱ���Dz��ǻ�Ӱ�쵽�ҵĸ���ѧҵ�أ��ҿ�������ǰ;�ı仯�����ҵ����Ż�����ʱһ������ս����ʧѧ�����Ǵ�����ľ�������ı��ܿ־塣�Ҹ���ĸ�����ֿ־塣
ĸ��˵������һ���醈����͆�һ��ɣ��ȵ��Ǹ�ʲô�أ���
�ҿ��������ϸ�һ�������˺���ѧУ��
�ҹ��������ȶ����ҿ�ȡ���µķ�Ӧ�ܺã�����֪���Ҹı���ԣ��л����ֶ������ˡ���Щ���������ֻ����ʱ������ţ�������������˲������ѹ�����ʲ��취�أ�Ϊ�˲�Υ��ĸ����˼�����ֵö��ܼ�������ˡ�
��������Ϊĸ��Ҫ����Ժ���������ƺ��ѳɶ���֮�ʣ����ҵ���������Ȼ�Ǿ���������ʧ�ܵġ����������������ǵ���Ը�Ѿ���������ʵ�֣�����������ĸ�ӣ����������������������Ƿ���������ʵ�ʵ��ж�������ʲô�жԵı�ʾ�ˡ�������ĸ��һ�����治�Σ����Ǿͻ�������塻��Ȱ���ҵ����ʲô�ط�ȥ�ġ�
�����ڵȴ��ţ���Ҳ�ʱ��Ž�����һ�������Ĵ�������Ѿ����ں����˵�ǰ�̣��ҵ������еĹػ���������ĸ�����ϡ�ĸ��Ҫ�����ˣ�һ�ж��ӽ��˾����ԵĽΣ�ĸ��Ԥ������ҽԺ�Ƿ���ҽԺ�ǵ����ķ���ҽԺ����Ϊ����ֻ��Ը�ó�������ҩ����Ը�⸶�κο����ķ��á���ĸ���ڷ���ֻ����ĩ�������Ľ�ɫ��С���梵���Ȯ���˻�����ҽ���룬��ȥ��ҽ������ĸ��ȴֻ��Ŀ���뷨�ӽ�ƶ����ҽԺ�����Ƕ����˵�ʬ������ڴ��Ŷ����·�ߡ����������г�����ƶ�����������ɷ���ҽԺ���ݾ�����Ч����֪���ġ���֪���ú���������ǣ�����ʲô�취�أ�
��ʱ��ս���Ѿ��յ����������ؾ��Ѿ��˵��ֲ��ˡ����ٹ��˺;��̴���Ѿ������ǰ��ĩ���ؿ�ʼ�뿪�����ˡ���ŵ��ǻ�Ʊ�Ѿ�Ԥ����һ�����Ժ����۰ĵĴ�Ʊ�����۾ŵĻ�Ʊ������������������ɳ����⽻������˾�ر��æµ���ڸ���ʹ�o��ǰ�Ⱥ�ǩ�յ��������ų�����С����ʼ�������ָ�ʽ��ҥ�ԡ���ɳ��վ��ų�վ������ס��������ɳ�����ij������淢�ֶ�ʱը������ӰԺ��������Ƭ�ӡ��˵ô�ۡ��͡���Ѫ��Ѫ�������IJ�ϰ���Ѿ�½�����֡��ij������ֳ�Խ��Խ�࣬�ȱȽ��ǡ�ҹ���ݵĵƺ�ȴ���Ӳ��ûԻͣ�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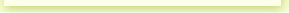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