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当有构思 切忌随意性 ——创作谈·四千五百八十六 在网上看了一位网友写的小说,其小说曰,上班途中,有辆墨绿色轿车超车;紧接着,一辆黑色轿车也超了过去……而后,看到血腥的一幕:墨绿色轿车被逼到桥外出口边,黑色轿车斜堵住他的车头,又从车上下来三个黑衣年轻人,各持一支铁器……那男的头上淌着血恐惧地大喊「救命」…… 我想,我是看进去了,我期待着故事的发展;然,这位网友又说了另一个故事:市府进行消防演习,另一个局的女科员担纲演出被施救者,套着消防索要从三楼垂降,才刚从窗口悬垂下来,她忽然失神了!本该抓住索套的双手却张了开来……不幸当场殒命……打电话来的美人二说:「……本来要派去演出的是我吔……」 我想,我又看进去了;可是,这篇小说没有了、结束了。 我想说,这位作者是有生活、有故事的,笔力也好,能够吸引读者。可是,不善构思。我说的是,不善于构思,而不是没有构思。小说的标题是〈黑色XXX〉。XXX不重要,重要的是「黑色」。该篇文字,纠结于「黑色」、黑上衣、黑衣裳等。 不知大家意识到没?纠结于「黑色」、黑上衣、黑衣裳,写以上两故事,是散文的构思法、不是小说的构思法。 如果是写小说,别车、有故事就继续写,没故事、就给出寓意,就成立了。而消防演习,本身已经构成了小说,如果顺顺好、还是篇很好的反转式小说。 我不认识这位网友,不知道他能否听得进意见,所以点到为止。我用汪曾祺的〈异秉〉继续话题。 就小说名〈异秉〉而言,写什么都可以。然,就汪曾祺的〈异秉〉开篇的、单行成段的「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而言,就只能写王二、写这个主人公的与众不同、与他人的「异禀」。 这不是我规定的,而是他的写法规定的。 然而,8081字的〈异禀〉,好好写了1756字后,写源昌烟店了。如果说王二要搬进烟店、非写烟店,那也没有必要、像写王二一样细致地写烟店;即使你认为细致写烟店、也有必要,至少后面没必要细致地写药店,是不是? 退一万步,就算写药店也能找出理由,那汪曾祺的〈异秉〉的最后的三个自然段,与王二无关。 〈异秉〉,汪曾祺写于「一九四八年」,重写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估计,一九四八年写失败了。然,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的重写,依旧很失败。 有的人,隔了几十年,把一切全都悟清了。而有的人,只怕一辈子也悟不清。像汪曾祺这样,偶然成了沈从文学生,又一辈子手中握有刊物、且被捧成名家的人,怕更容易成后者。 「名家」乱写小说,不止汪曾祺一个。而发现汪曾祺乱写小说的,也不止我一个——回答「欧亨利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影响呢」之话题的网友所提到的谢志强的〈小小说作家的才气〉,我找到了。 谢志强在〈小小说作家的才气〉中的「谁敢像汪曾祺那样写小说?他的〈异秉〉,万把字,结尾的千余字才进入正题——异秉,之前,全是散漫的铺陈,说王二所处的镇子的生活格局,而且,没有情节的进程,却是停滞,仿佛生活的历史在这儿打旋了……」等,未必就是好话;至少,可反过来听。 小说,有小说的写法;散文,有散文的写法。有时,一个起句,就规定了一篇小说的样式。无论是谁,也无论是不是名家、大家,都不可以过于随意。文无定法,是指在合理的范围内。超出了合理,就属随意。 顾晓军 2021-9-26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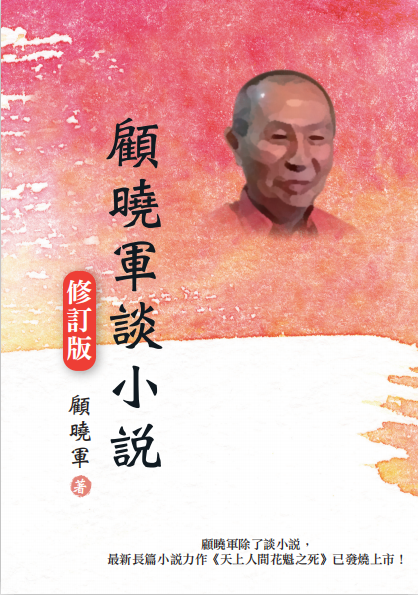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