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跳出党史话语体系来看“文革” |
| | 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无论党内的“好人”“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看来,都是中共怀相同政治理想、存相同政治动机、有相同政治目的的同志,都要承担执政党的政治责任
老高按:最近瞎忙,书看得少,网也看得少。今天才有工夫回到万维博客。探访左邻右舍,许多博友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朝鲜核试验上。想起两年多前我在这里开“老高的博客”,贴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前主任杨希雨的采访记《朝鲜这一箭,究竟射几雕?》,现在与那时相比,尽管时空有了若干转换,主角从金二换成了金三,但杨希雨所谈及的许多情况和思路,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此处不赘。
前几天转发了“文革”死刑犯徐正全文章,在按语中提到对“文革”有几种看法:“三年”(社会冲突论)、“十年”(权力争夺论)、“十一年”(路线斗争论),争辩的是“文革”的实质问题。今天读到董郁玉读哈佛教授麦克法夸尔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长文,主要谈的是“文革”的动因、起源。
麦克法夸尔这部巨著,我在出国前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读过中国大陆出的删节本。因为当时我对“文革”研究讨论相当隔膜,自己对“文革”的思考,更没有摆脱中共的话语系统,就像董郁玉所指出的:“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所以对老麦的这部著作,我竟不记得读后从中得到多少启发。
现在香港已经出齐这套书的全译本,今天再来读,想必就会有收获了!别的先不说,正如董郁玉此文中所讲述的: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虽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但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党史、或者说是在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把文革作为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构成文革起源历史中的具体是非而不可自拔。
特此向关心“文革”的朋友推荐董郁玉这篇文章,也希望各位能找读到麦克法夸尔的书!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看“文革”
——读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董郁玉,《炎黄春秋杂志》2013-02
谁的文革?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下文内简称《起源》)的中译本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齐。中国内地出版社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了经过删节的此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
这部专述文化大革命起源的通史,从文革前10年的1956年写起,到1966年文革爆发时止,分成《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年》、《大跃进 1958—1960年》和《浩劫的来临 1961—1966年》三卷,共计1430多页,实可谓皇皇大著。《起源》对来自官方与民间的海量历史资料条分缕析,多方考证,细致甄别,贯通因果,以至句句有根,事事有据,其旁征博引的史料之多,所述的历史事件之多,在中外文革研究领域中,尚不见出其右者。
对于中文读者来说,更重要的则在于,《起源》虽以文革起源为全书叙事的脉络,但其成书的逻辑却迥异于中共党史的逻辑,整部书都是在中共党史、或者说是在联共(布)党史的话语体系之外,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契入构成文革起源的国家政治运作,把文革作为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进行研究,从而使人们既能身临其境去体味文革的种种细枝末节,又能与文革拉开必要的观察距离,而不至深陷构成文革起源历史中的具体是非而不可自拔。
在传统的党史话语体系中,党即是国,国即是党;党史就是国史,国史就是党史。于是,各种官定的中国国家现代史乃至近代史,其叙事结构与内容,与中共党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结构及其内容毫无二致,雌雄不辨。这种国史党史同为一体的叙事结构,几无政治权力来源、国家权力合法性、政治责任和政治道德的位置,而尽是革命、路线、领袖和阶级的范式。
正是在这种范式的阐释中,在国史混同于党史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以中国的国家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被叙事,而是被当成了一个党在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挫折被叙事。并且,这个挫折被有选择、有限制地展开叙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这个党因为战胜了挫折、纠正了造成挫折的错误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当然,人们不能“对事实发火”。从《起源》一书中,读者可见,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治架构和社会结构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确实把中国国家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从某种角度上重叠在了一起。然而,即便如此,把这些同样的事实放置于不同的叙事结构当中,其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以国家历史为叙事框架,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政治组织为国家制定和输出的政策及其实施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正是中共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与分配以及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一定规则和程序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串联起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主干,却正是基于其政策实施结果的相应政治责任。一个执政党的政治责任,是其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之有无以及能否存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以中共党史为叙事框架,国家、社会、公民就很难在其中找到厕身之处,而中国共产党则在不同的执政阶段中,被分割成了代表不同“路线”的“左、中、右”派别;这些派别或又被划分成“好人”与“坏人”的不同群体。如是,在面对其对国家负有的政治责任方面,中国共产党就不再是因其掌握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而必须对国家负有全部政治责任的一个整体性的政治组织,而是由其中的“(四人)帮”、派(“改革派”或“保守派”)代表整个党,来为某个阶段的政治责任进行担当。这样,文化大革命也不再是这个政党的政策输出和权力运行的结果,而是“四人帮”、林彪等“坏人”当道、“好人”受难的结果,是“右派”不识时务、“左派”错整“右派”、“中间派”没有觉悟的一堆党内事务。
在国家政治中,一个政党作为整体的存在,是其对国家负起政治责任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共党内事务,实则掏空了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或者说把执政党对国家的政治责任,变成了厘清并公布谁是党内的“好人”、谁是党内的“坏人”,谁是党内的“七分好人、三分坏人”,谁是党内的不折不扣、彻彻底底的“坏人”,谁又是党内的胸怀“好心”却不得不办了错事、坏事的好人等党内是非。
如此一来,党内“好人”的受难,便可替换国家的政治灾难;党内“坏人”的罪错或某个派别对党负有的党内责任,亦可顶替整个党对国家负有的全部政治责任。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中,依党内是非而划定的“好人”与“坏人”,不是构成党的整体的不同部分,而是“好人”代表党,“坏人”——通过把他们开除出党——则似乎成了与党组织无关的一部分人,由此便可摆脱这些“坏人”施政而带来的整个政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也因此,党内的“坏人”不仅仅是党的敌人,也被用来充当国家的“公敌”。
从国家政治角度来观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政党,能否“摆平”其内部的“坏人”,以便生产出于国家而言的“好政策”,那是政党的内部事务。一个政党,其在政策制定与输出上,是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整体来看待的。这就是说,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好政策”,那么,从党外的角度看,这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好人”制定的政策;反之,如果执政党向国家政治系统输出了“坏政策”,那么,站在国家政治的角度,这同样也不会被认为是这个党内的“坏人”制定的政策。
因此,一个政党,不论依据什么样的党内标准划分出政党内部的“好人”与“坏人”,这些人都代表整个政党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因此,这个党也必须为这些政策的后果,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政治行为负起政治责任,而不论这些政策的“好”“坏”,以及这些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是“好人”还是“坏人”。
麦克法夸尔《起源》的最大叙事特点,就是没有在中共党内划分出“好人”与“坏人”,进而再以“好人”和“坏人”之分,来诠释他们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或者反之,依其所主张的政策的“好”“坏”,有倾向性地把一些人定位于“好人”,把另外一些人定性为“坏人”。没有“好人”“坏人”,当然也就没有国家政治责任的党内替罪者。在党史叙事中的中共党内的“好人”与“坏人”,在麦克法夸尔的《起源》中,都是中共党的一分子;就大的政治目标而言,他们都是为中共党的执政利益而怀相同的政治理想、存相同的政治动机、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的“同志”。这种不分“好”“坏”的客观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历史过程。
谁的政策?
国家政治,从某种角度简言之,就是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背景下,这些政策来自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政策的制定虽无政党之间竞争与博弈的过程,但是,政治权力所具有的天然竞争性,仍会在一个政党内部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体现出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政治的过程,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展开的。一项公共政策,其在实际中发生的效果,总是会强化或削弱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政治威信,从而强化或削弱他们的政治地位,进而强化或削弱他们在党内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动力所在,也是所有权力斗争发生的重要因由(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1—449页)。因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正是麦克法夸尔契入文革起源之处。
由此,《起源》把文革缘起的研究范围扩展至1956年,也正是因为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开始在实践中引发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并由于党内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限制而难以被纠正,以此为文革的爆发累积了政治能量。麦克法夸尔注意到,“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明显地,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5页)。
以战争的暴力方式取得政权,会难以避免地给政治权力的行使带来影响。这也是绝大多数“革命党”止步在“夺取权力”与“赢得权力”之间的鸿沟前,不能成功地过渡至“建设党”的基本原因。现在看来,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战争年代那种命令方式来操控权力,并且还能取得“成就”,这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政治权力的行使产生更大的误导。以暴力革命“夺取权力”,靠的是枪杆子;以和平建设“赢得权力”,靠的是公共政策。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的一个报告中,对那些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持谨慎态度的官员进行了嘲笑,说他们“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当然,可能连毛泽东自己都没有想到,压指标、下命令的军事指挥方式在和平时期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农业合作化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速度,让毛泽东自己规定的14个月的时间都相形显得过分保守了。几亿农民世代延续的生产方式,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正是这个“伟大的成就”,空前膨胀了毛泽东的意志。也正是在1956年底,他信心满满地宣布:“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很大的把握了。(本段引文均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21页)”
但是,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不似一项军事命令的执行那样可以迅速见分晓。农业合作化在4个月之内被迅速完成了。然而,这个政策的实施速度,加倍放大了其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不能像打扫战场那样,在短时间内被打扫干净。为此,政策实施者就必须采取其他相应的补救措施来为这个政策善后,并由此产生分歧。这种对政策及其实施的分歧,就是党内政治权力斗争的起源。
当然,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身处“一线”的政策实施者与置身“二线”的政策设计者毛泽东在政策上的分歧,只能以政策实施者向毛泽东低头检讨而消弭。然而,所有政策参与者都清楚,在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面前,失去更多政治威望的不是检讨者,而恰是毛泽东本人。由此造成的对失去政治权力的焦虑而堆积于胸的块垒,直至10年后的1966年,才被毛泽东一吐为快(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2—453页)。
《起源》以中共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为经,以中共党内政策参与者围绕政策制定和实施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为纬,为文革起源串通起了因果链条。并且,《起源》也常常以寥寥数笔来交代中共在其历史上党内权力斗争的脉络,以为读者建立起相关的阅读背景。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无疑就是要铲除“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除掉那个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上有自己的一套,并总是以检讨的姿态来蚕食自己政治地位的刘少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53页)。不过,正如《起源》所述,从中共党内权力派系的渊源上讲,刘少奇应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刘少奇堪称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如日中天地位的最力建造者。如果没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不遗余力的帮衬,没有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具有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主导思想,以及其他无数任劳任怨、鞍前马后的铺路和善后,毛泽东在党内说一不二的威望,就不会在曾经“山头”林立的中共党内如此快和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1—13页,第108—110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153—171页,第218页)。
经过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和大跃进,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威望和实际地位受到了削弱。以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性,他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毛泽东力推的许多政策,在实际中引发了大量问题,“甚至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实质性的不同意见,自那以后,这些不同意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日趋严重,也正是在这些不同意见中埋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种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5页)。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在党内独断暴行的揭露,以及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删节了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参见《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106页,《大跃进1958—1960年》第300页),都强化了毛泽东对失去党内政治权力的担忧。没过多久,提议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彭德怀就在次年的党内政策之争中被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力。而1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更证实了这个“君子之仇”有多深:早已经是“死老虎”的彭德怀又被揪了出来,就此事反复写出交代材料;而“同意”删去这两个部分的刘少奇和其他人,都在文革中为此付出了大小不等的代价(参见《人民内部矛盾 1956—1957年》第106—108页)。
苏共与中共的同构性,宿命般地决定了其最高领导人在党内取得、保有和捍卫权力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的形成,也绝非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人之功。即使从以党史话语体系精心构造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苏东等各个国家的所有共产党组织,虽经过频繁的党内权力斗争,但却都没有形成符合一般政治伦理的制度化的党内权力规则;党的领袖及其同志,都认可、服膺甚至舍身维护这种比宫廷政治还要晦暗和残酷的“山寨规则”。
问题在于,在没有掌握国家权力之时,围绕党的政治权力之争,不论多么残酷,多么背离常规的政治伦理,其影响所及,还基本限制在政党组织的范围内。而在这样的政党“夺取”了国家权力成为执政党,并且是在没有其他竞争执政的政党存在的情况下,其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及其后果,就会对整个国家产生深重的影响。这种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演绎到极致,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论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还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看,以动员全社会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党的内部权力斗争,且在以此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做出颠覆性改变的同时,还能保有整个党的执政权,这样党内权力斗争方式确是一个政治行动的创举。这也许就是麦克法夸尔所谓:“从来没有一个独裁者,发动社会力量反对他自己所创建的国家。这次确乎是所有群众运动之母。(《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445页)”
谁的责任?
实际上,毛泽东敢于如此所为的独特优势,就在于由刘少奇最先擎起的“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
上述共产党在进行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既定政治程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毫无遵循。从各国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的历史看,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者,无不是其意识形态的忠实体现者。
而正是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为那些按照一般政治伦理标准衡量过于残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方式,提供了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支持。权力斗争的胜者,一定要申明其拥护、遵循和代表那个支撑党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一定被冠以反对、违背和篡改了党的意识形态。
因此,党的意识形态,是党的政治权力正统性的根据所在。在苏共二十大上,“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出席会议的大会代表都得到了列宁在1922年12月写下的‘遗嘱’的文本,列宁在这个‘遗嘱’里对斯大林作了严厉的批评;还有一份写于1923年1月的提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附录”(《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第45—46页)。由此可见,在共产党内部,如果要剥夺一个人的政治权力,甚或要否定一个人的政治遗产和历史地位,那么,都必须将其与党的意识形态强行剥离。把列宁“遗嘱”下发至苏共二十大代表,就是想证明斯大林绝非列宁主义的合格信徒和忠实执行者。
被各国共产党公认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掌握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中的实体性政治权力。列宁的早逝,也让列宁主义附体于列宁之身的时间十分短暂。而实际上,真正规范了列宁主义范畴、对列宁主义做出最“权威”的解释,却正是由斯大林在列宁死后做出的。因此,列宁在党内所掌握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也没有与以其名字命名的“主义”过紧地粘连在一起。
至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以后,共产党内部的实体性政治权力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就具备了现实而坚实的基础。以掌握党的最高政治权力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党的正统意识形态,这就在赋予了这个人的言说以至高无上性的同时,又赋予了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价值的超越性。如此,把党的意识形态附体于个人,某种程度而言,就等于把这个人化身为了党的意识形态。正如上述,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参见《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314—322页,第448—449页)。
正是这样的“附体”,让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具有了“神性”。这个“神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的言说、政策设计、权力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上。而1945年之后中共所取得的一系列革命成就,不过都是这个“神性”的证明而已。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共产党的事业一帆风顺,那么,不会有人去怀疑这个神祗的灵性。但是,当党的最高领导人设计、制定的政策在实际中遭遇失败时,让其去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政治责任,这就不啻让那个在祈祷中丧失了保佑灵性的神祗去担当凡间的具体罪错。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反对毛泽东制定的政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指导思想,反对党的意识形态,反对党,反革命……就都成了一回事情。由此,在党内政治权力斗争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毛泽东奠定了不败的基础(参见《大跃进1958—1960年》第299—302页,《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第171—181页)。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党的意识形态化身地位的确立,为毛泽东的政策设计赋予了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和不可置疑性。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成了其所打造的这个政治神祗的最大祭品。这也正是麦克法夸尔的不解之处:“刘几乎肯定从未想到过任何政变,但他却未作任何抵抗,这确实是很奇特的。相反地,他1966年5月顺从地主持了打倒他的主要政治盟友的会议。(《浩劫的来临 1961—1966年》第451页)”
当然,在这样的政治架构中,对毛泽东那些在国家政治实践中已然遭遇到多重失败的种种政策感到无能为力的,还不止是刘少奇。在党的意识形态附于毛泽东之身时,那些曾亲眼见证过神祗灵性的同志们,看着“这位带领他们从漫长的革命征途走向胜利的人,现在又以某种捷径,带领他们向乌托邦发起了冲刺”的时候,“谁会去提醒作为神的毛说,大自然可以驯服,却不可被践踏;人们可以移山,却不能创造奇迹;政治革命可以在十年或者甚至一天里成功,但思想革命却需要几个世纪”(《大跃进 1958—1960年》第314页)?
正是这样的“人神”一体,使毛泽东具有了党内其他任何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本钱。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化身,“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党的指导思想,因此,毛泽东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化身。这个政治现实,正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几近彻底颠覆了党的组织结构,但却能给除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扣上“分裂党”的帽子,以一人之身凌驾全党之上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现实,也是中共在日后整理文革瓦砾之时,颇有投鼠忌器之感,难以将毛泽东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彻底剥离,并且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及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引文均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根源。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提出要“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为之确立了“实践检验”的标准;且用“发展”的限制性定语,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在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动留下了通路。
不过,总体来看,只要“毛泽东思想”存在,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就确实具有不可分性。在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以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并未要改变党的指导思想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现象。客观而言,党的意识形态、党的政治权力与党的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合体”,可以提高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增加党的领导人的正统性和高层政治权力的稳定性。这也是毛泽东之后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需要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观念及其理论,并将其纳入至党章的基本动机。
更重要的还在于,保证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是保证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性的需要。文革的灾难由“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造成,以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些举措,一方面使毛泽东脱身于国家政治责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中共在国家政治中的合法执政地位。
中共执政地位的确保,需要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的存续,又需要确保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过去的事情“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才有当下中国大陆文革历史研究的冷清局面……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环环相扣的制约和限制中,党对国家应负的政治责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灾难,都始终没有得到细致言说的机会。也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缘故,在今日中国,在相当多的人的想象中,文革竟然有了玫瑰色调的魔幻色彩,由此,也才会公然出现“重庆模式”下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仍旧站在中共历史的制高点上。这,也许正应了那句证明毛泽东身在神坛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而以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点的《起源》,也正是用“毛主席万岁”这句耐人寻味的“最高指示”,结束了这三部探讨文革发生起源的皇皇大著(《浩劫的来临 1961—1966年》第454页)。
相关文章: 三年文革·十年文革·十一年文革 文革死刑犯对文革到底留恋什么? “文革”,这一代人最重要的人生段落 一个文革死刑犯如何看待“文革”? 对造反派随意性记录,导致历史记忆混乱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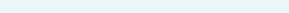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