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于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立刻引起了在近年的社会科学领域极为罕见的争论。 亨廷顿向世人推出了一种冷战后国际政治的新视角——“文明冲突论”。 该文特别强调儒教——伊斯兰教两种文明的联系将是未来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 亨廷顿为思索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又一全新的视角。 前不久,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发言称,美中对抗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这段话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也引发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美国文明”?它的特色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文明”又是怎么看的?会否带来灾难?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图片来自Worldwide Speakers Group) 今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新美国” 智库主办的“未来安全论坛”上定性中美关系。她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对抗。” 她并且说:这是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冷战时期跟苏联的对抗那只不过是一场西方内部的斗争。 斯金纳表态一天后,保守派的《华盛顿观察者》周刊发表《国务院准备与中国进行文明的冲突》一文,透露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被定性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
这种想法明显采用了已故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1992年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即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文化与宗教认同将是主要的冲突来源。今后的战争将不在国与国之间爆发,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爆发。
美国国务院今天这样的“战略思维” 显然是对当前国际情势的误判,所以立刻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抨击。不过,斯金纳并非新手上路,却居然把种族主义正常化,难道是另有“苦衷”?况且以黑人的身份而为白人种族主义背书,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不过,本文无意深究“文明冲突”这个伪命题,而是要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美国的“文明”?它的特色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文明”又是怎么看的?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文明"的看法是否会给美国带来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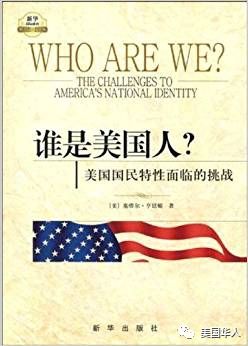
要了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必须先了解他心目中的美国的“文明”特征。换句话说,美国的国家认同是什么?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这本书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一般讨论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都会提到“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这是杰弗逊总统首先提出的有关美国身份定位的阐述,内容包括个人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和民粹。
在威尔逊总统任上,美国众议院于1918年4月3日通过一个《美国信条》的法案:
“我相信美利坚合众国是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其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它是共和的民主;由许多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主权国家;它是一个完美不可分割的联合;它建立在自由、平等、正义和人道的原则之上,为此,美国的建国者牺牲了生命和财富。因此我相信,我有责任爱国、支持宪法、遵守法律、尊重国旗,抵抗所有敌人。”
这个法案应当是第一次对美国国家身份的正式定位。它本身虽然是个“官样文章”,不过的确能代表美国“文明”的特色。
亨廷顿则将“美国信条”定义为体现“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的原则。”
但是,他接着说:“如果在17世纪和18世纪,殖民地不是由英国新教徒而是由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天主教徒来定居的,那么今天美国会成为美国吗?答案是不会。 它不会是美国,它将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
他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的成立靠的是从英国来的定居者(settlers,不是移民);第二,唯有美国是宗教改革的产物,是新教徒设立的。换句话说,美国的国家身份特征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徒”(WASP)。
简单说,这个身份认同一种由种族和宗教所界定的民族叙事。亨廷顿虽然在《文明的冲突》里面说,北美“盎格鲁新教徒”定居者所做的贡献并非源于种族性,而是源于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新教徒的职业道德,对洛克个人主义的信仰,对集权国家的不信任,等等。这点没错,问题在于他同时认为,这个文化(“文明”)与种族和宗教无法分割。这个关键点在《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里表达无疑。【1】
其实,“定居者”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白人中心的自我解嘲罢了。除了美洲原住民以外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外来者,都是移民。小罗斯福总统在二次大战前(1938)就曾说过:“记住,永远记住,我们所有人,特别是你和我,都是移民和革命者的后代。”
亨廷顿认为,美国的国家身份自从60年代开始变质,而这个变化与1964年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1965年通过的《选举法案》,以及1965年的《移民法案》都有深刻的关联性。这些保护少数民族的平权和投票权的法案,以及合法使用其它语言的措施(减少对英语的要求),损害了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
这岂不等于说,《吉米·克劳法案》反映了美国身份?马丁路德金牧师的民权运动伤害了美国身份?白人种族主义的思维跃然纸上!
令亨廷顿最感到不安的是墨西哥移民的问题。他认为,墨西哥移民与先前移民很不同,他们不容易融入美国社会。由于拉美移民快速增长,亨廷顿认为这使得美国西南部地区“西班牙化”,美国将会分裂为一个英语国家和一个西班牙国家。他把美国的种族多样化看成是“文明的冲突”,拉美裔如果要追求美国梦,唯一的方式就是用英语做梦。
亨廷顿认为美国充满了“达沃斯人”(世界主义的精英,与基层脱节),仅仅靠“美国信条”不足以维系美国的身份,美国必须回归到有强烈宗教性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文化,以及启蒙运动的理念。换言之,新移民不符合美国“文明”,很难被同化。
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负责书评的角谷美智子评论该书的写作风格,她说亨廷顿引用了很多前人的旧观点,有点像80年代与90年代对多元文化的辩论,缺乏新意。
角谷美智子认为,全书读起来就像是个400页的PowerPoint演讲稿,全书充满了“三点原则”、“四个挑战”、“四个阶段”等等概要式的表达,将极其复杂模糊的社会和历史现象简化为流程图的条目。亨廷顿提出的是一种新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为要保护和加强“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美国身份”。
内容方面,我认为,波士顿学院的政治和社会学教授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评论最为尖锐(2004-5-1)。
沃尔夫指出,北美殖民地在独立时期并非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徒。纽约和新泽西州主要由荷兰定居者居住;天主教徒在马里兰州势力很大;罗德岛是由浸信会所设立,其中不少人有德国血统;德国人和英国的贵格会在宾夕法尼亚州占主要地位。
沃尔夫认为,宣称“存在一个共同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说法忽略了一些重要事实,即新教的各个教派间彼此斗争,对“新教文化”究竟是什么充满歧见。宾州贵格会对文化的解读与麻州的公理会就截然不同,它甚至受到公理会的压制和迫害。
文化不是固定的,沃尔夫用天主教说明,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新移民在被同化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的文化。天主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教派,其独特的风格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庆祝复活节、上学、体育活动、外交政策等。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文化重要的一环,它早期来自犹太文化的敏锐性。
亨廷顿宣称,新移民同化的程度远比以前要差,沃尔夫则认为这个看法没有事实依据。以最大的移民群体墨西哥移民为例,亨廷顿认为墨西哥移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申请公民身份的很少,也没有与他族通婚。沃尔夫说,这都不符合事实。墨西哥移民学习英语的能力不低于先前的移民,他们改变信仰,成为新教福音派的比例,除了韩国移民以外无出其右。
自由与民主源于西方的经验,而且深深植根于欧洲的基督教历史,这点本来没错,只需要再加上希腊罗马。不过亨廷顿进一步认为,自由与民主背后并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现代化只能在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发生。关于这点,东亚民主国家的崛起已经驳斥了他的观点。
美国文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互为因果。纵使退一步看,不谈原住民,美国很多领土都是从西班牙和法国的天主教殖民地移转过来的。美国西南部很多领土(包括德克萨斯州)是从墨西哥掠夺来的。批评墨西哥移民分化美国身份,这并不符合历史,有煽动种族情绪的嫌疑。
其实从建国的历史来看,除了”盎格鲁“这层种族外衣有问题以外,”新教“这层宗教外衣也是有问题的。美国的建国者(国父们)有很多并不属于新教,虽然他们都受到新教的熏陶。他们也受到苏格兰启蒙深刻的影响。美国的建国理念(《独立宣言》、《宪法》)是新教与苏格兰启蒙完美的融合。这点,美国历史学家诺马可(Mark Noll)在他2002年的巨作《美国的上帝》里面分析得十分详细。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亨廷顿拒绝用意识形态(例如,独立宣言,美国信条)给美国定位。他支持实用主义,间接带来了白人中心论,难怪引起批评者的抗议,指责他冷酷地漠视道德与历史,与(保守)权力同谋。
亨廷顿自己的数据显示,爱国心并不因种族不同而有巨大的落差,非拉美裔的白人愿意为保卫国家上战场的有81%,新移民的数字是75%。其实,真正的差距在底层与精英之间,精英的全球意识比较浓厚(达沃斯人),民族主义的意识比较淡泊。有趣的是,他们很多都是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排斥移民并不能加强国家认同。亨廷顿所居住的波士顿尤其如此。
亨廷顿总结说:“白人本土主义运动是对失去国家身份的趋势的一种可能和合理的反应,在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困难的情况下会成为高度可能的走向。”
这样说等于是肯定了美国不需要高瞻远瞩的指导性信条,民粹是个无法避免的走向。这种思维用在美国就带来了“让美国再度伟大”,以及“美国优先”的反移民和国际孤立主义。亨廷顿竟然成了特朗普时代的先知和旗手!
虽然在私人层面,特朗普的言行与新教伦理背道而驰,不过在历任总统中,只有“关税人”特朗普最符合亨廷顿的期望。特朗普那种无法辨别公私的分际,只知道“你输我赢”,只用“你是否支持我”作为衡量一切是非准绳的作风,正好符合白人种族主义的部落思维和强盗逻辑。

Samuel Huntington, a prophet for the Trump era一文,2017-7-18。(图片来自《华盛顿邮报》)
特朗普总统2017年7月中访问波兰,在华沙发表谈话,敦促欧洲人和美国人捍卫西方文明,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分子和野蛮人群(非白人)。这种论调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亨廷顿。
当特朗普呼吁西方国家“鼓起勇气捍卫我们文明的意志”时,他坚持只接受那些“分享我们的价值观并爱我们的人民”的移民。当他敦促跨大西洋联盟“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谁”,并谨守“历史,文化和记忆的纽带”的时候,我估计,亨廷顿在坟墓里发出了微笑。
所谓文明的冲突,说白了就是由于白人感到自己的优势地位和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恐惧到饥不择食,甚至不惜被普京利用。不仅特朗普,欧洲所有高举本土国家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的主要民粹党派都跟普京有着暧昧的关系,包括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等。
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寻求国家认同的呼声就不断响起。20世纪初国会所通过的《美国信条》法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参照点。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法兰西斯·福山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反对身份政治》一文(2018-8-14),他认为民主国家应当促进“信念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国家认同不应当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历,历史关联或宗教信仰之上,这些东西带来的不过是部落式思维。
美国与欧洲的民族国家不同,国家认同应当建立在核心价值观和信念之上,以鼓励公民认同国家的基本理想,并使用公共政策来同化新来者。
福山呼吁:要把美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极端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中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被政治炒作的)宗教的国家身份治国,排斥多样性。左翼中的身份政治提倡者则过分高举多样性,通过专注受害者心态来摧毁国家叙事的合法性。【2】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文明冲突论"的发言不过是回到亨廷顿1992年的老调,并没有正视今天美国国家认同的危机,特别是左右族群间的撕裂和“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部落思维。在这个错误的假设上(美国优先的新孤立主义)订立外交策略,更是十分危险。
前面提到的圣母大学历史学教授诺马可2007年发表过一篇雄文:《美国的两次建基》,他详细解释,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政治上,美国立国的理念经过两个阶段的变化,大致以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宗教)和南北战争(政治)为分界点。这两个阶段的文化精神和原则有重大的调整,最终导致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3】
换句话说,美国的文化并不是固态的,它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改变。要把它固定在某一个时段,希望借此解释整个历史过程,那其实是个不尊重历史的冲动。你只需要放眼看去,美国文化上的创新精神,特别是高科技和理论科学,大多数是移民的功劳,包括从亚洲、中南美和非洲来的移民。
今天美国最需要的是一位真正高瞻远瞩的领袖,把握住“信念式国家认同”的精神,引导国家走出部落主义的地雷区。
注: 1. “福山说,亨廷顿似乎正在赢得胜利,但......”,微信《哲学园》公共号2019年5月15,该文翻译自:”Huntington’s Legacy,” by Francis Fukuyama, National Interest, 2018-8-27. 2. 福山的文章在维护弱势族群权益的人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认为他反对身份政治的言论否定了弱势族群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参照《外交事务》杂志2019年3/4月《来自多方,但仍然为一》,E Pluribus Unum,一文精彩的讨论)。不过,我感觉这两者不一定互相冲突。福山关心的是“信念式国家身份”的认同以同化新移民;争取弱势族群平权的人,大可以抛弃部落思维,利用这个共同性来争取权利。福山最后的辩解也指出四位作者们会错了意。 3. “America’s Two Foundings”,Mark Noll, First Things Magazine, December 1, 2007.
来源: 美华 美国华人 2019-06-2-02
撰文:临风
编辑:雯君,Jing
本文由作者授权原创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
《文明冲突论”所引起的大哉问:什么是美国的“文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