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中的鐵原阻擊戰(14,完) 薩蘇 
徐信 187師,是63軍的另一個主力師,不但換裝蘇式裝備最早,還有一位傳奇的師長,此人就是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信上將。
徐信,原名徐連晨,七七事變後,於1937年9月參加八路軍,是一名地道的燕趙子弟。或許天生帶着對戰爭的敏感,這位未來的將軍在抗戰期間很快就嶄露頭角。一打邱門,二打定縣,三戰馬莊,到抗戰時,從士兵開始軍旅生涯的徐信很快因為戰功升任冀中軍區6分區第32團團長,被稱為楊成武麾下的一員愛將。
事實證明,楊成武沒有看錯人。1945年,為了阻擊八路軍的攻擊,日軍在獻縣大修工事,號稱要“固若金湯”。結果碰上徐信,一個預先多次演習的連續爆破,就生生地將獻縣城拿了下來。1947年,傅作義手下的王牌軍35軍和晉察冀野戰軍第3縱隊在淶水遭遇,一仗之下,“虎頭師”32師師長李銘鼎被擊斃,而守淶水的主將,就是時任8旅23團團長的徐信。因為這個失利,抗戰之前就是老行伍的35軍軍長魯英麟自殺身亡,誰能想到一員老將竟然被這個小字輩活活逼死。
抗美援朝期間,徐曾擔任第63軍188師563團團長和187師副師長、代師長。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63軍187師代師長,師長。1953年回國,次年到蘇聯入伏羅希洛夫高等軍事學院學習。1957年回國,任高等軍事學院合同戰術教授會副主任,訓練部副部長。1962年起任66軍軍長,北京軍區參謀長。1980年11月任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助理。1982年12月至1992年10月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64年晉升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1987年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2年退役。2005年在北京因病逝世。
有將軍的老部下回憶他的作戰風格,說徐信打仗多刁啊,攻也行,守也行,“猛如虎,狡如狐”的綽號,給他才最合適。 徐信作戰機巧,靈活,愛動腦筋。在河北至今流傳着“徐團長倒着走走死鬼子騎兵”的傳說,說的是梯子溝戰鬥中徐信率部阻擊日軍掃蕩部隊,掩護楊成武司令員的總部突圍的傳奇。戰鬥中偷襲的日軍戰鬥動作十分迅捷,但遭到徐部頑強抵抗,偷襲一分區指揮機關未能成功。惱羞成怒的日軍出動騎兵部隊死死咬住了徐信率領的一個連掩護部隊,形勢十分兇險。 徐信卻十分冷靜,帶部隊用八路軍的老傳統“敵進我退”在山區大繞圈子,竟然連走了兩天兩夜,日軍騎兵不習山路,竟有被“走死”的,卻始終捕捉不到不斷變換位置的八路軍,只好收兵。事後老鄉傳說徐信所部行軍時一旦疲勞就會倒着走一段,這樣走了一陣又轉過身來繼續走,日軍始終在他身後撲空。 這當然不是氣功或者別的什麼神秘的東西,科學地說,只不過是倒着走與正着走使用的肌肉不同,這樣做可以讓肌肉群得到輪換休息而又不用停下來。所以徐信所部兩天兩夜都在不斷移動,使敵軍始終無法捕捉到他。 梯子溝一戰,有些部隊特別是後勤部門因為跑不動被日軍追及,傷亡甚大。若是都有這樣的機動能力,可能損失會小得多。 在五次戰役中,和志願軍其他前線部隊一樣,徐信的187師在突圍中打得十分艱苦。 應該說,第五次戰役的開局,187師打得十分出色。作為軍主力,該師在進攻臨津江,突破雪馬里的戰鬥中打得異常兇狠。面對“聯合國軍”重點設防的臨津江防線,徐信一改志願軍擅長夜戰的特點,制定了一個白晝渡江的作戰計劃,親率主力561團率先突擊敵軍防線。由於訓練十分嚴格,187師在敵前隱蔽極好,渡江動作極快,充分利用了敵軍措手不及的短暫時間,過河即全力向前穿插。儘管敵軍隨後用飛機迅速封鎖渡口,但已經過河的187師、189師等部隊全力前插,使敵方十幾公里的防線崩潰。這一戰,63軍重創英軍29旅,全殲格羅斯特營和一個炮兵隊、一個坦克連。在志願軍左中右三路進攻部隊中,左翼的63軍進展最為順利,19兵團通令嘉獎並授予187師“猛插分割”錦旗。彭德懷司令員通令表彰187師:“這種勇敢穿插分割的精神,值得各部學習,特予以通令表揚。” 但是,正因為突得靠前,撤退的時候187師比其他部隊也就更加艱苦。 5月21日,189師在洪川江斷後掩護全軍後撤。次日,和軍指一起行動的187師讓軍指先走,在洪川江與北漢江之間的金珠里與敵突前部隊交火,掩護疲憊的189師脫離戰線。此後,187師自己也開始向北漢江後撤,其間一度被進展飛速的美軍截斷在敵後。但是,有反掃蕩經驗的徐信果斷指揮部隊避實就虛,在敵人空隙中不斷鑽進,最終順利到達北漢江邊。 在到達北漢江的時候,187師的官兵驚訝地發現,儘管自己一刻不停地行軍,但美軍部隊竟然先一步已經到達了江邊,一個美軍軍官正在上游組織部隊徒涉渡江。美軍的偵察機,就在江面上盤旋。 雙方機動能力的差別暴露無遺。 接到偵察員報告的徐信顯然面臨着極嚴峻的考驗——如果等待黑夜的到來,部隊在江南很難不被敵軍發現,幾個小時就可能遭到合圍。如果消滅面前的美軍再渡江,敵軍數量不少,又有裝甲部隊伴隨,這將是一場極艱苦的硬仗,已經彈盡糧絕的部隊,恐怕很難完成任務。 在艱難中徐信做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部隊卸下偽裝,大搖大擺地渡江! 志願軍的軍事素質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整整一個師已經無糧無彈的部隊,鎮靜地排成整齊的隊伍,如同閱兵一樣在美軍的武器射程內開始了渡江! 美軍無動於衷——無論空中還是地面的美軍,都把187師當成了南朝鮮友軍。此時,美軍各部奉命以最快的速度追擊志願軍後衛部隊,誰也無暇和戰績不佳的南朝鮮人打招呼。187師的渡江,成功了。 如果說徐信只是靈機一動就騙過了美軍,那是對整個軍事科學的侮辱。戰爭不是賭博,187師渡江的時候,留在最後的,是炮兵。徐信將炮兵留在南岸,目的是一旦有變,就把殘留的炮彈全部傾瀉到上游渡江的美軍頭上,把整個戰場攪成一鍋粥,以炮兵全軍覆沒的代價掩護大部分步兵脫離戰場。 徐信自己也留在南岸,和炮兵在一起。 幸而,美軍對此毫無覺察,范佛利特做夢也沒想到志願軍會這樣“友好”地和美軍從一個地方渡江。 入夜,美軍不願這個時候在善於夜戰的志願軍面前行動,停了下來開始宿營。徐信乘機率領炮兵緩緩撤過北漢江。他發現,在對岸江邊的蘆葦叢中,軍長傅崇碧正焦急地等着他。 187師渡江的時候,傅崇碧始終在江對岸等待,直到看着徐信帶着炮兵撤下來,才長出了一口氣——187師是傅崇碧的王牌,眼看鐵原難免一場惡戰,要是這張王牌還沒打就丟在北漢江,那後邊的仗還怎麼打? 187師繼續後撤,途中接到情報,一路美軍以坦克搭乘步兵沿北漢江西北岸在向63軍的背後迂迴。但是,夜間不習慣行動的美軍已經失去了最好的攻擊時機。188師563團,徐信師長起家的老部隊,已經在臨津江青平里渡口背水為陣,等待着他們的是一場激烈的阻擊戰。 據說,紅軍強渡大渡河的時候,也有同樣的一幕——國共兩軍隔江打着火把相安無事地行軍趕往瀘定橋,甚至紅軍還會吹國軍的聯絡號問候對方。中間大雨突降,國軍留下宿營,對岸的“友軍”卻繼續前進,結果——第二天,瀘定橋落入紅軍手中,“第二個石達開”成了紙面文章。 有勇,有謀,有運氣,可就是這樣一名善戰又能戰的將軍,6月9日面對鐵原前線的重任,恐怕也不得不承認這副擔子沉得要命。 雖然此前鐵原戰鬥的主角是188師和189師,但187師其實一直在一線——按照傅崇碧的作戰指揮,187師始終擔任右翼防禦主力,承擔玉女峰以東,漣川至鐵原鐵路,公路(含)以西地域的防禦,以防敵方中央突破,幾乎和189師同時與美軍發生戰鬥。只是此後美軍選擇189師防禦正面進行突破,187師的陣地才略微平靜。但隨着前線的戰鬥越打越緊,187師的部隊不斷被抽出投入一線救火,不但傷亡很大,而且大多一上去就被黏在前線無法下來。到6月9日,徐信師長的手裡,實際能夠使用的兵力只有一個團。 但這還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無論蔡長元還是張英輝,都是沙場老將,他們在前面的防禦中,已經把阻擊戰的招數施展到了極限。蔡長元的機動防禦最大地削弱了美軍進攻的勢頭,張英輝的藏兵於九地之下讓美軍如同破褲子纏腿般步步難行。連李奇微也不得不在回憶錄中帶着醋意寫道:“敵人再次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並且在其大批部隊和補給完整無損的情況下得以安然逃脫。” 但是,以空間換時間的戰術,首先要有空間。打到這個時候,志願軍在鐵原前方的防禦空間已經基本被用光,整個陣地只剩了窄窄的一條。打阻擊經驗豐富的徐信就算手拿方天畫戟,讓他在屋子裡和人家肉搏又怎麼使得開? 而美軍經過十幾天的鏖戰,也逐漸掌握了志願軍的作戰規律,加之鐵原前方並非高山峻岭,而是丘陵地帶,這樣在敵方飽和的火力強壓下,187師不可能僅僅依靠意志就守住陣地。 一邊打一邊在琢磨,徐信師長平靜地拿出了自己的方案——守不住,就不守好了,只要不讓美國人進攻就可以完成志司的任務嘛。 不讓美國人進攻?怎麼可能?那除非李奇微是我們送去的無間道。 徐信就是有辦法,他的辦法是——反攻。 此時談反攻更令人驚訝,因為兵力、火力上我軍全無優勢。志願軍的反擊通常選擇夜間進行,特別是面對的美軍在五次戰役中已經打得“成了精”,對於志願軍的夜襲作戰準備十分充分。他們每到晚上,必要收縮陣地組織夜間防禦,在面對志願軍的一面,美軍則擺出了非常特別的一種防禦陣型。 這種防禦陣型,是用裝甲部隊的戰車圍成環形,外面放上蛇腹鐵絲網,將炮兵和探照燈部隊放在中間,形成一座鋼鐵的移動城堡。這種移動堡壘的位置,通常設在比較開闊的地勢上。夜間,美軍不斷釋放照明彈,照亮周圍,使志願軍夜襲的企圖面臨着極大困難。 在這樣的防禦工事面前,連靠近都困難,如何能進行攻擊呢?即便是五次戰役打響之時,志願軍要強攻如此大敵,也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何況,打到此時,63軍上下已經幾乎彈盡力竭,如何能攻得動呢? 大概也是看出志願軍對這種集群防禦沒有太好的辦法,依靠“鋼鐵城堡”的美軍十分猖狂,每到傍晚,美軍的炮兵就會對鐵原方向發動一次近乎瘋狂的炮擊。美軍的炮兵多自行火炮,非自行火炮則都有大馬力牽引車,打完,美軍把大炮拉回“鋼鐵城堡”裡面,從美國來的慰問團就在“鋼鐵城堡”的後面開始演出。 查證西方史料的時候,一個事實嚇了筆者一跳。直到6月9日,到鐵原前線慰問的,居然是美國鄉村音樂巨星Elton Britt,約德爾唱法的集大成者。他在當天演出完畢後前往橫城繼續慰問那裡的美軍官兵。如果這位巨星晚一天離開,只怕難免喪身戰場。志願軍官兵——當時對美國鄉村音樂可說一無所知——不會因為這位歌星在場就手下留情。 徐信師長的作戰計劃依然是進攻,但他把自己的步兵放在了二線,並不準備讓他們利用黑夜去靠近美軍陣地。他真正想用來反擊的主力,是63軍一直雪藏的炮兵。 說“雪藏”其實是不貼切的,因為63軍並沒有雪藏炮兵的意思。由於組織得當,63軍在後撤途中帶回了大部分重型火炮。該軍軍屬炮兵團轄3個炮營,1個火箭炮營,還有一個裝甲汽車隊。根據美國《時代》雜誌報道,當時在鐵原前線,志願軍使用了美制155毫米榴彈炮和蘇制150毫米榴彈炮。但是,志願軍的大口徑火炮陣地一貫是美軍空中攻擊的首要目標。而志願軍的火炮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畜力牽引,機械化程度較低,道路又大半在美軍封鎖之下,所以,大中口徑火炮機動性能較差。鐵原前線雙方炮兵實力相差太大,調上去的火炮經常在對射中輕易被炮術熟練的美軍摧毀,或者剛剛放列就遭到美軍飛機的空襲。所以,鐵原之戰的大部分時間,炮兵部隊一直沒有痛痛快快打過一仗,始終在和美軍捉迷藏,沒有找到能完全發揮自己作用的戰場。此時,志願軍的火炮陣地已沉寂多日,大部分重型火炮已經隨主力部隊後撤。只有大口徑迫擊炮還留在陣地上,火箭炮營還沒有撤走。 徐信的看法是,美軍的鋼鐵城堡固然堅固,但是如同曹操建了連環舟,固然安穩,但也把自己拴死在那裡了。槍是夠不着它,也打不動,可要是炮來打呢?那它周圍的開闊地就不夠寬闊了。我們打它,它要麼不跑,那我可以動,它不能動,那不就是挨打的靶子嘛?它要麼跑,周圍那麼密集的車輛人員,半夜裡還不知道要壓死多少自己人呢。既然如此,與其在陣地上等它來攻,不如我們先去給它來個火燒連營算了。我們的炮兵原來不好打它,是運動不上去,現在鐵原都打到了自家家門口,我們把前線的迫擊炮集中起來,加上軍部的火箭炮,拉上去就能進入射程,不設炮兵指揮所了,也不要瞄準了,那樣大的目標,打着什麼算什麼,給他來個一錘子買賣好不好?等把它打毛了打亂了,我的步兵上去再干它一傢伙,這麼大的動靜,不信美國人一兩天能緩過來。 對徐信這個建議,傅崇碧作何反應有完全不同的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仿佛一句話點醒夢中人,傅崇碧一拳砸在桌子上,187師反攻的方案就此制定。一種說法是傅崇碧苦笑一聲,沒多說話,只是把軍直屬的火箭炮營交給了徐信。這兩種說法哪個是真已經無從分辨,但傅崇碧對前線的認識應該和徐信沒有多少區別。在前面的阻擊戰中,打得緊時,傅崇碧把自己的警衛部隊、軍部的勤雜人員都組織起來,派上了前線。到63軍視察的楊得志看着空空如也的63軍軍部頭皮發麻,一咬牙把兵團司令部警衛營抽調出來“借”給63軍,沒兩天又被傅崇碧大部分送到了前沿陣地。 應該說這是被美軍逼出來的一招。事實上如果不準備在鐵原城裡打巷戰,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了。巷戰傅崇碧不是沒想過,但志司給63軍的命令是阻擊美軍於鐵原之外,而不是在鐵原和美軍據城而戰,那將使鐵原對志願軍的戰略轉移失去意義。而且,鐵原城已經是一片廢墟,美軍一旦進城,就可以用火力切斷志願軍後撤之路,真打起來無論阻擊成果如何,63軍肯定是不可能出來了。所以,這是下下的選擇。從5月29日打到6月9日,戰鬥已經進行了十二天,離志司要求的“十五天”阻擊期限還有三天。傅崇碧把還沒有撤離的軍屬炮兵全部配屬給徐信,能不能頂住完成任務,確實就看這一錘子買賣了。 徐信的反擊,在6月10日夜間打響,出擊的炮兵部隊一線配置迫擊炮,二線配備“卡秋莎”火箭炮,在步兵掩護下悄無聲息地進入美軍“鋼鐵城堡”對面的陣地,因為志願軍部隊已經幾天沒有成建制的炮火反擊了,美軍只對中國軍隊的步兵襲擊作了防範。凌晨2:00,由一門120毫米迫擊炮發射黃磷燃燒彈指向,63軍炮兵各自為戰,在最短時間內把炮彈打光。對面美軍上百輛坦克圍成的營地頓成一片火海。 混亂中美軍並非不想還擊,但僅僅打了幾炮就發現中國軍隊的炮兵陣地無從分辨,猝不及防中美軍準備第二天進攻的彈藥被志願軍發射的火箭彈點燃,劇烈的殉爆造成了比志願軍炮擊更壯觀的爆炸。 唐滿洋所在的566團,此時已經撤下來保護正面陣地側翼,同時充當軍隊的預備隊。10日深夜,他親眼目睹了這次令人難忘的炮擊。 “我們的炮不是在一個陣地上,從前線十幾個點一起朝美國人的頭上打,被美國人炮彈炸彈欺負狠了,陣地上都在喊‘炮兵,炮兵’。美國人陣地上,那不是一般的爆炸,是整個一片在燃燒,坦克啦,炮啦遠處也看不清楚,可那個火和平時不一樣,那是一種紅的、黃的、白的摻雜的火,是鐵在燒!” 63軍的炮兵把殘存炮彈全部打光,然後全部撤出戰鬥——這完全吻合徐信的戰鬥設想。這次突襲,就是“一錘子買賣”,炮彈全部打完,否則留下來也只能是累贅。 炮兵之後,187師的突擊隊乘着美軍混亂之際,對美軍營地發動突襲。這一次,美軍的炮火再無阻擊,突擊隊員直把手榴彈丟進殘存的美軍營帳之中。 對於這次中國軍隊的突然襲擊,或許是因為被視為恥辱,美軍記載很少。根據隻言片語的記錄,我們可以知道,遭到攻擊的美軍至少有第7步兵師和第17炮兵團的部隊(志願軍始終認為打的是美軍騎1師,但是,無法從美軍的資料中得到證實),大部分美軍在遭到襲擊的時刻感到十分突然,他們果斷地逃離了現場,任由志願軍對物資和車輛發泄炮火——對於美國來說,這些永遠不及士兵的生命更珍貴。因為一輛坦克只需要幾個小時就可以製造完成,而一個士兵,至少要十八年。這也和徐信將軍回憶炮擊後中國步兵衝進美軍營地投擲手榴彈如入無人之境頗為吻合。被襲擊後的第二天凌晨,大雨滂沱,但美軍步兵第7師的一部分士兵出於安全考慮沒有敢回到營地,他們在樹林中搶救傷員的時候拍攝了一張照片,讓人不由想起美國朝鮮戰爭紀念碑的造型——焦慮,疲憊,神色木然身披雨衣的步兵們,在朝鮮的荒野中艱難地執行任務。 另一條值得一提的記錄是當天和志願軍作戰的美國兵中,有一個負責操作探照燈的一等兵弗蘭西斯·華爾(Francis P。 Wall),戰後一直堅稱當時美軍遭到了不明飛行物UFO攻擊。他堅決地把自己的看法談給飛碟研究專家約翰·提摩曼(John Timmerman),而提摩曼則將其公開發表,曾經轟動一時。在這份報告中,華爾回憶了UFO帶着奇怪的嘯音對美軍陣地進行攻擊的過程,以及自己用M-1步槍擊中UFO,並遭到報復的過程。他的戰友也承認那一天之後華爾的體重從180磅直跌到138磅。這一事件在世界不明飛行物UFO研究會的目擊記錄中,被編作1076號。 不過,也有他的戰友悄悄地對記者說華爾可能是在戰爭中受的刺激太深,以至於失去了理智。 用中國話,所謂失去了理智,就是嚇昏了頭…… 這和徐信將軍指揮的這次“一錘子買賣”的炮擊有何關係,還不得而知。 遭到痛擊的美軍並沒有發動即時的反擊,而是退後一步,等待物資和裝備的補充。 一個未經證實的說法是撈了便宜的徐信打上了癮,非常希望11日晚上再來一次。去找傅崇碧要兵,說哪怕用俘虜來抵也成。 面對如此巨大的誘惑,傅崇碧只回答了一句話——“徐信,你看我跟你去怎麼樣?” 徐信無言以對,只好作罷。 傅崇碧也覺得很可惜,但是沒辦法。63軍是真的快打光了,13天鐵原大戰的慘烈超出很多軍事學家的想象。傅崇碧已經快連哨兵都沒有了,以至於打完鐵原,撤下來見到彭老總,傅崇碧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要兵”。彭德懷當時就拍了板——“我給你補兩萬”。 187師頂住了,傅崇碧終於可以微微地鬆一口氣了。 傅崇碧鬆了一口氣,李奇微嘆了一口氣。 6月11日,李奇微代表“聯合國軍”司令部,下達了暫停超越鐵原線發動攻擊,就地組織防禦的命令。 1951年6月18日,美國《時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名為《朝鮮戰場的第二個仁川?(BATTLE OF KOREA: Another Inchon?)》的文章,把李奇微在鐵原的突破與麥克阿瑟在仁川的登陸相提並論,大肆誇讚這位將軍的豐功偉績,認為這是對紅色中國軍隊實施全殲、徹底扭轉戰局的最好機會。 假如這篇文章出現在五月下旬,李奇微一定會大嘆深得我心——切斷鐵原,把志願軍的主力留在臨津江以南,正是他實現軍事生涯頂峰的最好時機。他也深信在自己處心積慮的設計中,彈盡糧絕的志願軍很難脫出自己的手心。然而,如今一切可能都不存在了。 他暫停攻擊是無奈的。63軍的阻擊擋住了他攻擊的箭頭,與此同時,20軍58師在史倉里華川,15軍在芝浦里,朝鮮人民軍第一、第三軍團在戰線兩翼的阻擊,也讓他無法過分深入。抬頭看去,志願軍利用鐵原阻擊爭得的時間,已經在鐵三角底部的伊川地區重建了穩固的防禦體系。而美軍的進攻此時已經打到了筋疲力盡,曾有多次遭到志願軍夜襲的時候,美軍連哨兵都在呼呼大睡。悍不畏死的中國軍人,刁鑽的戰術,崎嶇的道路,滂沱的大雨,美國兵從來沒有打過這樣艱苦的仗。美國的有識之士也開始認識到,徹底擊敗中國人民志願軍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以妥協方式結束戰爭方不失為最明智的選擇。 一個月之後,板門店談判正式開始。和平開始向朝鮮,這個滿目瘡痍的國度露出了曙光。 記者對戰爭的理解,與軍事家的差距是二十天。 哭笑不得的李奇微看着這條遲到的“新聞”,只能這樣感嘆了。 6月12日,志願軍的戰略轉移已經完畢,按照志司的命令,63軍撤離陣地,鐵原阻擊戰的大幕終於落下。 一場戰爭的落幕,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似乎是一個溫情的時刻,然而,對每一個戰場上的戰士來說,感受又絕不相同。 我問唐滿洋撤下來那天他什麼感受。 他半晌無言,緩緩走到窗戶前頭,看了老半天,忽然對我說:“蘇權銘那天帶着一個連來接我的陣地。我說,美國人的炮打得沒數,這一仗打下來可懸了,老蘇,你有啥話,跟我說說吧,我給你帶回去。蘇權銘說,你快下去吧,我沒事兒。 我再問他,他還是說,我沒啥好說的,這兒太危險,你快下去吧,我得布置防禦了。我就回頭往下走,剛走到山腳,突然炮就響了,集中打我們陣地。這一回炮打得特別凶,我越聽越不放心,炮聲一停,趕緊往陣地上跑。到陣地上一看,蘇權銘和他的指導員,都讓炮彈給炸死了……我就……我就……”天殺星唐滿洋吸了口氣,聲音帶了一點發顫,“我就拿了我那個大衣,給他蓋臉上了。” 他伸出手去,雙手對着空氣異常輕柔地做了個覆蓋的動作,仿佛那下面是什麼一碰就會破碎的東西。 “這個時候,撤退的命令就傳下來了。” 後來才知道,蘇權銘,是唐滿洋的老搭檔,特等功臣,打竇家山的時候,兩個人就分率敢死隊的兩個分隊。 沉默半晌,唐滿洋溫和地看向我,緩緩地但誠懇地說道:“打仗的事兒,就說到這兒吧,以後再不說了,好嗎?心裡太難受……” 楊恩起記得最清楚的,是撤退到伊川以後,國內送上來的火腿、肉罐頭吃都吃不完,也有蔬菜了,也有水果了,還有慰問演出,世界仿佛在一天之內從地獄轉到天堂。 只有一個瞬間灼烈得如同刺痛的傷口。 566團1連被評為大功連,但戰鬥打響前兩百多人的1連,只有楊恩起一個人能夠走上領獎台。他的戰友們,不是長眠在鐵原前線的山嶺里,就是在後方的醫院中。 雖然也帶着兩處傷,但楊恩起走上領獎台的時候十分鎮靜,因為他覺得自己,就是1連。全連的戰友,都在看着自己。只是當他把帶着繃帶的手舉上帽檐敬禮的時候,掌聲中全場的人都哭了。 他們在為那些不再能走上領獎台的戰友而流淚。 但他們其實更應該驕傲。長津湖冰雪中奮勇追擊的中國軍人讓世界知道,當戰爭走進中國人的軌道,我們不畏懼任何敵人。而鐵原燃燒的陣地同樣讓世界知道,即便一切占盡上風,與中國人的戰鬥依然要付出最沉重的代價。 這一切都宣示着一個即將雄踞東方的民族正在傲然直起自己的身軀。 從此,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輕鬆地議論對中國開戰這樣的話題,雖然在此前的一百年,這種話題都可以在咖啡桌上談定。因為那些在長津湖和鐵原長眠的中國軍人已經告訴了世界,無論占上風還是占下風,都不要輕易與這樣一個堅強的民族為敵。 直到今天,這條戒律,依然是世界大國們無法逾越的準則。 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元帥,面對從鐵原撤下來的63軍官兵,把下面的話語毫不吝嗇地加之於這些有名的和無名的中國軍人——“祖國和人民感謝你們!我彭德懷也感謝你們!” 在志願軍撤出鐵原的同一天,“聯合國軍”進入只剩殘垣斷壁的鐵原,然而,此時他們已經對這座城徹底倒了胃口。直到日曆翻到二十一世紀,仍然沒有人嘗試讓這座城市恢復生機。直到今天,這裡依然是一片被時間凝固的廢墟,如同化石,紀念着這次世界軍事史上無法磨滅的戰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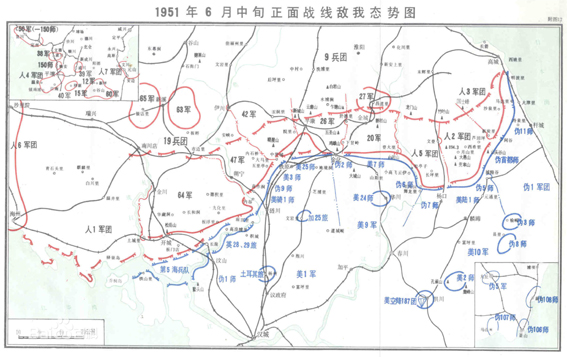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