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那些浅见之徒,永远生活在昨日,因而反对任何只为明日的觅路者而设的观念,他们对本书立刻发出呼喊,指为“悲观主义”。但是这些人只是以为探求行动的本源,即等于行动的本身,只是热衷于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我的书不是为这样的人写的。“ ——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
听听一百年前这位高人对民主本质和现状的惊世预言和分析:
”当时的人们,虽然权力在手,却仍为“普遍真理”争论良久, 议论未定,兵已过河, 以致实际的力量,得以乘隙而起,把一干梦想家们掷落在一旁。” “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没有金钱,宪法的权利根本一无所用,有了金钱,方能够妙用无穷,予取予求。”
民主的命运
作者:(德)斯宾格勒 / 翻译:陈晓林
选自 《西方的没落》第十九章
在刚开始的时候,民主只属于知识分子的领域。 西方早起民主政治史上,有名的几件大事:路1789年8月4日夜晚法国的“阶级大会",“网球场的誓约”, 以及1848年5月18日普鲁士的“法兰克福会议”, 可算是历史上无比高贵而纯洁的事件——当时的人们,虽然权力在手,却仍为“普遍真理”争论良久, 议论未定,兵已过河, 以致实际的力量,得以乘隙而起,把一干梦想家们掷落在一旁。但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的另一目的,却也并不落后,一径潜滋暗长,终致,人们开始了解到一项事实:只有拥有金钱的人,才能利用宪法的权利,民主的权利。事实上,选举权的功能,竟能够发挥到,接近理想主义者所以为的高度,则必然是因为:有组织的金钱势力,尚没有从中操纵竞选者的缘故。一旦这等势力出现于政治舞台,则选票也不过只是徒具形式的公众意见的记录纸而已,对于真正操纵政治的权力结构,已不复具有任何正面的影响。 表面上,西方的,议会式的民主政治,与埃及,中国,阿拉伯等文明中的”民主政治“,大相径庭,因为在那些文明之中,全民普遍的参政权,根本从未成立。但事实上,如我们这个时代,一般民众,也只是在”选举区“中,被集体操纵的一群,相对于政治的”主体“而言,也仍只是”客体“而已;这与巴格达人民对其教派统治,拜占庭人民对其僧侣阶层,以及任何其他地方,人民对其统治结构所表现的集体服从,根本绝无什么不同意义。自由,永远只是纯粹的负面现象。自由表现于对既存传统,王朝,教主的摒弃,但是事实上,实际的政治权力,依然存在,绝未削减,只是有这些体制,转入于新的力量中--如政党领袖,总统,先知等等名目而已。相对于这些新的政治中心,大众仍只是无条件地被动的客体。
古典人民的基本权力,曾伸展至拥有最高的国事与司法的职权。为了施行这些权力,人民乃集合于所谓的”公会所” (Forum) 中。 其实, 在“公会所”中,人民只是欧几里得式的“质点”,被具体地集拢起来,以充作古典风格的政治影响程序下的客体而已,政客们可以用具体切近,诉诸感觉的手段,左右这些人民-- 举例言之,这些手段包括:施于每一人眼前及耳边的雄辩之术;包括很多我们看来,简直厌烦不堪,难以忍受的方式,如呜咽不休,擂胸顿足;对听众作恬不知耻的谄媚,对敌手撒异想天开的谎言;冠冕堂皇的辞令,慷慨激昂的陈词;还有游戏与表演,威胁与攻击,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金钱。金钱之介入政治,早在西元前400年的雅典,便已现出端倪,到了凯撒与西塞罗时代的罗马,便是达到了骇人听闻的高潮。到处都是一样,选举的活动,从阶级代表的提名开始,即已成为各政党候选人的战场,同时也即是迎接金钱源源进入的所在。而从查马之战以后,金钱的数额越来越趋庞大,“个人手中能够集中的财富愈巨,则政治权力的争夺,发展为金钱问题的程度便也愈大”。 西塞罗这一段话已足以说明一切,无需更做赘述了。然而,从深一层的意义来看,若认为这是贿赂舞弊,仍是为中肯 qi之言。这不是什么多了行为,民主精神的本身,在达到其成熟状态时,便已注定了必然会采取这样的形式。西元前310年的克劳迪斯(Censor Appius Claudius), 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希腊精神的信徒,也是主张宪政的理想家,有如法国革命时代的罗兰夫人 (Madame Roland) 圈子中的人物一般,在他所从事的政治改革中,确实不会在公民参选权上玩弄狡狯,也绝不会采用更改选法,以图利己的政治“艺术”——但他所有的努力,只不过为这些“艺术”铺路“而已。并不是民主的体系有利于舞弊,而是从最初应用民主政治开始,种族的特性便已出现,金钱便已发挥作用,而且,非常迅速地,完全控制了局面。终极而言,在金钱独裁的时代里,将金钱的运用,描述为一种堕落的标记,是颇不公平的事。 罗马的公职,自从其产生的过程,需经由一系列的选举以来,由于所需资金甚巨,往往使每一个政治家,都不免向其周围的伙伴告贷。选举的资金,或用于邀请所有选民晚餐,或提供角斗表演的免费座位,甚或登门送上现款——诚如西塞罗所言:“传统道德,荡然无存。” 选举的资本,庞大惊人,有时达数亿银币之巨。以罗马一地所蓄积的款项之充沛,而西元前54年的选举,由于动用太多的款额,竟使当时的利率,一时从4%,剧升至8%。凯撒竞选“护民官”时,支付浩繁,以致克拉苏必须为他签约担保二千万银币,那些债主方肯让凯撒离去赴任。而在凯撒竞选“最高僧侣院”的职位时,由于信用过紧告贷无门,几乎毁于一旦,他的对手卡特拉斯 (Catlus), 竟能认真考虑向他提出贿赂,逼他撒手。但是,对高卢的征服与开发——这也是出于财政上的动机——终使凯撒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而凯撒之所以积聚巨款,就如今天南非的罗德兹一样,乃是为了权力,并不是如凡理士(Verres) 一样,或甚至克拉苏那般,只是由于喜爱财富而已。相形之下,克拉苏首先,但主要是一个财政家,其次才算是政治家。而凯撒掌握的, 则纯是事实: ——在民主政治的土地上,没有金钱,宪法的权利根本一无所用,有了金钱,方能够妙用无穷,予取予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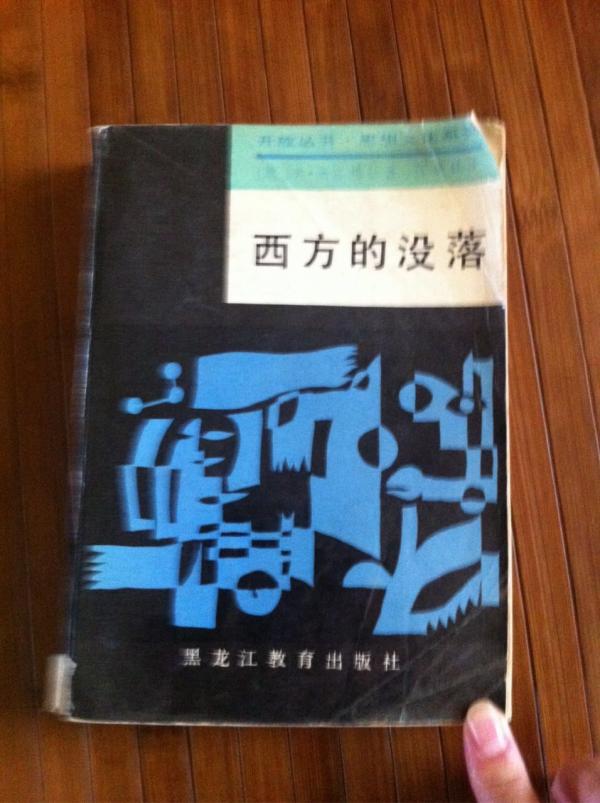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