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逸草:文中提到的受害者中,有我们父辈的朋友,也有好几位我好友父辈的亲友。
怀旧好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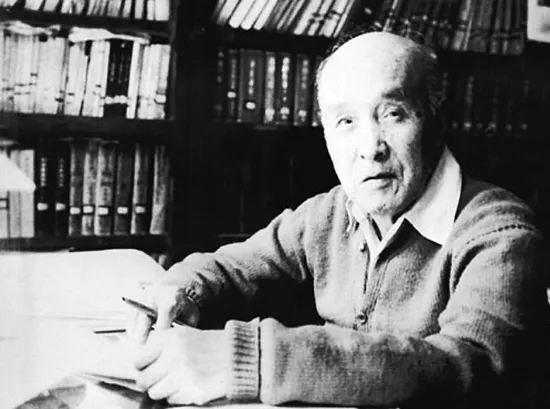
一、震惊海内外的文字狱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建国初期的一件大冤案,在当时具有铁案的性质,不容他人置疑。胡风是全国人大代表,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5年5月18日正式批准拘捕胡风的前两天(5月16日),胡风即已被捕。夫人梅志亦于次日早晨被捕。实际上从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的第一批材料之日起对“胡风分子”的秘密抓捕行动即已开始。据当年参与“胡风专案”审讯工作的王文正先生说:“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捕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在这些人员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在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在被逮捕关押的92人中,于1965、1966年先后被判刑的3人,他们是:胡风、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沈国凡采写、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第5页) 大搜捕从北京开始,各地紧跟,仅为时月余,所谓的“胡风分子”即被搜捕殆尽。如北京被捕的除胡风夫妇外,还有牛汉、谢韬、徐放、绿原(刘仁甫)、路翎(徐嗣兴)杜谷(刘令蒙)、阎望等,天津有阿垅(陈守梅)、鲁黎(许图地)、卢甸等,南京有化铁(刘德馨,在北京被捕)、欧阳庄等,湖北有曾卓、郑思、伍禾(伍德辉)等,湖南有彭燕郊等,浙江有冀汸(陈忠性)、方然(朱声)、孙钿(郁钟瑞)等。安徽有张禹等。 上海被认为是胡风的老巢,故是这一场冤案的重灾区。先后被捕的有贾植芳、贾夫人任敏、耿庸(郑炳中)、耿夫人王皓、彭柏山、刘雪苇(在北京被捕)、白丁(徐平羽)、王元化、梅林(张芝田)、何满子(孙承勋)、张中晓、罗洛(罗泽甫)、李正廉、罗飞(杭行)、满涛(张逸侯)、许思华、顾征南、尚丁、王戎、施昌东等20人。其中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占了7人,即社长刘雪苇、总编辑王元化、副总编辑梅林以及编辑人员耿庸、何满子,张中晓、罗洛。 受胡风一案牵连而受审查乃至隔离审查者也有不少,据我所知,仅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教授的被捕,就牵连了不少人。如费明君(文学翻译家,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陈秀珠与张德林(夫妻二人均复旦中文系53届毕业,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助教),王聿祥(复旦中文系53届毕业,时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章培恒(复旦中文系54年毕业,地下党员,留系任党支部书记),范伯群、曾华鹏、朱碧莲(三人均复旦中文系55年应届毕业的高材生),孫惠群(复旦新闻系55年应届毕业生)等。另外,我亦是受牵连而遭拘押审查者。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典型的现代文字狱,是仅仅依据胡风于1954年7月22日向中共中央呈交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以及《人民日报》公布的三批胡风与友人间的私人信件摘抄和编者按语来立案的。所谓的“摘抄”,实质上是断章取义、构陷于人;而其编者按语,则不乏罔顾事实、无中生有、穿凿附会、逞臆罗织之辞。而且立这么一个大案,竟然没有一份正式文件向办案人员申明政策,由此而造成更多株连的冤案。 二、风风雨雨二十载 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是上海最早被捕且拒不认罪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关押至1965年,被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2年。他一生坐牢四次,前三次坐的是国民党和日伪的牢,罪名都是共产党嫌疑;这最后一次时间最长,坐的却是共产党的牢,罪名竟是反革命,这是他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其实他一生追求民主进步,向往革命,不惜为此而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上海解放,他怀着迎接新中国的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应聘担任震旦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专职教授乃至中文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中文系并入复旦中文系,他亦随之任教于复旦中文系。 我与贾植芳先生相识于1953年。那时我在部队做文化教员,后调到文工团搞创作,因工作需要,部队推送我去复旦大学中文系进修。解放前,我上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1952年我到复旦大学进修时,读的是中文专业,后来我跟班听课的54届提前于53年毕业,系主任郭绍虞先生就安排我跟贾植芳教授学习。贾先生是一位非常热情健谈的人,我们讨论俄国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常常一谈就是半天,他还常留我在他家喝酒吃炸酱面。我也多次请他到我部队驻地叙谈,如1953年我的驻地在黄家花园(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的私邸,后改建为桂林公园),我就请他来参观过,他还带来刘大杰先生送我的译著《野性的呼唤》。1954年初我调到文工团搞创作,还请他来团里作过讲演。后来又请他观摩由冯允庄(即上海孤岛时期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苏青)编剧、尹桂芳主演的越剧《宝玉与黛玉》(不料这次观摩竟在“反胡风运动”中牵连了编剧苏青,留在下文再说)。所以我们的过从是比较密切的。 但是贾先生平日似乎很少谈及胡风的文艺理论以及胡风在文艺圈子里的恩恩冤冤,我对于这些更是漠不关心,直到胡风上《三十万言书》,才引起我的关注。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文章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严加驳斥。随即对胡风的批判运动逐渐展开。复旦中文系也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批判会”,方令孺教授在会上提议让贾植芳教授作“中心发言”。方令孺原是新月派诗人,解放后当选为上海市妇联副主任,在政治运动中一向表现积极(她在“反胡风运动”后入了党并于“反右”后调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但她在“文革”中亦难逃厄运)。贾先生知道其言外之意是要他作检查,一下子来火了,拍桌子说:“要干你自己干,我宁可辞职也不会做这事!”但他的冲动使他面对更大的压力。后来他在家人的劝导下不再硬顶,采用摘取报刊上批判文章中一些辞句凑成发言稿的办法来应付过关。但这违背了他固执的性格,所以内心深为苦闷。那天我去看他,见他闷闷不乐,便邀他外出散心。我们乘车到延安中路上的一家饭店叫了酒菜边吃边聊。他说他跟胡风虽然是生死之交,但对胡风的文艺理论了解得也不多,胡风在文艺圈子里的恩恩怨怨自己也不甚关心。现在硬要他作什么检查交待,这就只能作违心之论了,但这样做了还是过不了关。我当时也还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是说了一些宽慰他的话,如前几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等,批判时严厉,事后还不是一阵风过去就没事了,孙瑜还照样当导演拍戏,俞平伯还照样当教授教书。酒足饭饱之后,他的情绪似乎好多了,于是又去就近的戏院看了一场戏才分手。 接下来因部队整编,我将会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先参加集训,后来又去杭州办事,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与贾先生联系。直到1955年5月中旬我从杭州回沪,无意中看到《人民日报》发表舒芜揭发胡风的材料和按语,深为胡风不平,便去看望贾先生,沒想到这一回竟撞到了枪口上。原来贾先生已于5月15日被秘密逮捕,此时公安局的人还在贾家搜查。当时是贾家的小保姆来开的门,她一见我就神色紧张地说:“贾先生出去了。”我见她身后还影影绰绰地有两个人在注视我,便只得离开,转身去敲隔壁历史系胡厚宣教授的门。胡家小保姆一见是我,也连忙说:“胡先生不在。”她知道我是贾家的常客。我这才意识到贾先生可能出事了,只得怅然而归。 谁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部队政治部的一位科长找到我,要我带上所有的个人物品,跟他去一个地方学习,而且汽车就在外面等着。我知道这是要审查我了,就说:“我还有两箱书,是否可以一起带上?”他爽快地说:“都带上吧。”这一晚他将我送到一处临时拘押我的地方,让我独自住在一间屋子里,门口还站着一个背着步枪的哨兵。这一晚真是思绪万千,难以入眠。夜半起来解手,还得“报告”,由哨兵押到院子草丛边小便。此时哨兵的枪已是端在手上,怕我有什么不轨的举动。我苦笑着对他说:“你这样拿枪顶着我,我怎么尿得出来!”第二天那位科长又来了,要我把所携之物搬上吉普车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一次他把我带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的拘留所,将我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门外还站了一个哨兵。拘留所的干部要我交出随身的物件(如手表等钱物),还抽掉了我的裤带,大概是怕我自杀。我当时就向他抗议:“我不是犯人,为什么这样?"他说:“押进来的人都这样,这是规定!”我无奈地回到监房,凭着一股不谙世事的书生意气,竟写了一份抗议书交上去。强调自己是来谈问题的,不应该把我当犯人。第二天警备区政治部文化部来了一位干部,说话的态度比较温和,他说:“你的要求我们己经知道了。我们没有把你当犯人,怪我们没有交待清椘,误会了。从今天起,你在大院里可以自由活动,吃饭就跟着营部一起吃。我们的唯一要求是你必须交待清楚跟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也就舒坦多了。于是我一五一十地向他谈了我与贾植芳认识的过程,并申明,我与“胡风集团”中的其他人并不相识,更无交往。他要我作进一步交代,将想到的都写下来。以后他每隔两三天来一次,我将能够回忆起来的都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但我实在想不出贾植芳先生有什么反动言行。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充满激情拥抱新中国的进步文人,但这种正面印象在当时的语境中却不能表露。不过审查我的那位干部倒也不逼我捏造事实,也从不厉声厉色地说一些“要老实交代”之类的话。而且后来我带进来的香烟抽完了,口袋里的钱也用完了。他居然还借钱给我买烟。 我在拘留所里面的行动倒是挺自由的,可以在大院里散步、看书,并与营部领导一起用餐,这使我的心情略为舒坦了些。但是等待却是焦灼的,我渴盼早日回归社会。因为1956年部队搞正规化,加上我所在的文工团建制撤消,要裁简一批社会关系较为复杂的人,我有海外关系,自然就成了裁简的对象。我是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当口,被押来拘留所审查的。我担心这次拘押审查对我的工作分配会有影响。果不其然,就在审查我的期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曾有调我去工作的意向,后来一听我因胡风问题正在受审查,他们那里本来就是胡风案的重灾区,怎么还会再要一个与胡风案有牵连的人呢?我在焦灼不安中度过了两个月,警备区政治部终于结束了对我的审查,给我以“受胡风分子思想影响”的结论。后来我被分配到一所初级中学去当语文教师。一年后,我被评为区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调到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在这里我与复旦55届中文系毕业的朱碧莲相遇了。 朱碧莲的遭遇跟我相似,临毕业时遇上了胡风案。她平时学业优秀,在班上名列前茅,曾两次获得陈望道校长的嘉奖,教授们都很看重他。贾植芳先生在她的毕业论文上给了92.5分,而别人的最高分是92分。党组织因此而怀疑贾植芳为什么如此垂青于她,于是对她进行审查,将她与另一些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女同学集中在一座废弃的小草屋里交待问题。受胡风案牵连的和有所谓其它问题的男同学则集中在一座废弃的大草棚里受审查。朱碧莲本来会分配到研究单位去工作的,这一来自作罢论,最后给了“受胡风分子思想影响”的结论,并给予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分配到一所初级中学去当语文教师。幸而一年后她也被选拔上来了。 我与她是校友,志趣相投,又有着相同的遭际,很快就由友情发展为亲情,1957年春節后她成了我的妻子。可惜好景不长,在整风运动中我对“反胡风”时受审查的事提了意见,加上我在私人聚会上说过“胡风问题历史会作结论的”,后来被告了密,这就难逃厄运了。内子朱碧莲曾劝我说话要谨慎,我却书生气十足不放在心上,让她为我的直言无忌不时地担心。她虽也为自己在“反胡风”时被留团察看一年的事提了意见,但说话有分寸,不落把柄(后来复旦大学团委接受意见正式发文,撤消对她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为此支部书记还故意诱导,说她不如我敢于向党提意见。幸亏她没有“响应号召”,要不然我们夫妻二人同落陷阱,境况将会更其凄惨!我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家里的事全赖她一人操持。此时支部书记又告诫她要站稳立场,与我划请界线,还劝她同我离婚。其时内子已生下一女,便以此为推托,拖延未就。 从“反胡风”时受审查到“整风反右”再遭打击,这样的事例有不少。如安徽的张禹,曾在上海主持泥土社的编辑工作,经他之手出版了很多胡风及其友人的书稿。他于1954年调至安徽文联工作。在“反胡风”运动中,泥土社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出版基地,在上海的泥土社老板许史华已经被捕,他这个泥土社的合伙人自亦难以幸免。尔后他于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又如复旦大学的施昌东,在做学生时就在《文史哲》上发表《论“美是生活”》的论文,在美学上很有才气。还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初期在《文艺月报》上发表了批判文章,结果在“反胡风”时却被抓进监狱关了一年,后来实在审查不出问题来才释放,留在复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然而却没逃过1957年的“整风”阳谋。1958年又差一点被流放到青海去,还是系里说资料室缺人手,才将他留了下来。再如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王聿祥,在贾植芳教授被捕的第二天去贾家,正好撞在枪口上,也受到审查,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又再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德林在“反胡风”时受审查,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更被逐出华东师大十余年。浙江的孙钿更为不幸,反胡风时被关押了一年余,反右时又被划为“大右派”,发配至梅山盐场等地做苦工,后又被关押。武汉的伍禾原为湖北文联副主席,反胡风时被关押,58年又划为右派。更悲惨的是耿庸的夫人王皓,她在耿庸被捕后接着也被逮捕,关押审查了一年才被释放。她对此不满,1957年“整风”时提了点意见,单位要将她划为右派,她受不了一再的精神折磨,便跳黄埔江了却此生,冤案害得耿庸家破人亡! 我在农村劳动改造三年,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所在的农村地区却不见自然灾害的迹象,但农作物确实长不好,“一大二公”刮共产风,加上瞎指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是我们这些到农村来劳动改造入了“另册”的人却不敢消极怠工,我们这些书生经过长期的艰苦磨炼,竟也能挑上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走一长段田间小道。种田、养猪样样在行。1960年底我总算被摘掉沉重的“右派”帽子,于1961年暑期后调回学校。 从1961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五年中,我一边教学,一边写有关楚辞的论文,还写了两个剧本《武昌起义》和《屈原之死》,但是在当时的境况下这些东西都只能束之高阁,藏之石匮,不过我相信它们总有面世的一日。然而“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东西却使我陷入险境。一位曾关心过我的女干部向造反派透露,我写过一个《武昌起义》的剧本。于是造反派对我穷追猛打,说我写这个剧本是为国民党反动派招魂,妄想国民党反攻大陆云云。他们三天三夜轮番斗我,逼我交出剧本。我则一口咬定,我曾写过一个剧本的分幕提纲,后来力所不逮,便没写成,连提纲也没有保存下来。造反派从我那里逼不出什么东西来,便到我家去逼我妻朱碧莲,我妻刚生下第二个孩子,还躺在床上坐月子,见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来逼,吓得差点晕厥,造反派见势只得扫兴而归。我被暂时释放回家后,连夜找出秘藏的书稿,将其中的《武昌起义》和《屈原之死》两个剧本以及一部《新文学史讲义》用水泡烂撕碎,分批放进抽水马桶里冲入化粪池灭迹。我亲手毁掉融入自己多年心血写成的文稿,真是痛心之极,但为了避祸,我只能出此下策。当然我也保留了几篇有关楚辞的论文,交出去供他们批判。可笑的是,屈原口中的“群小”“党人”,一些中文系出身的造反派竟说我借此攻击群众是小人,攻击共产党人云云。之后我被关进了牛棚,成天除了交待便是劳动,浪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后来我总算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了,又被下放“五七干校”,专门从事船运黄砂、石子、砖头之类建筑材料,劳动强度很高。直到1972年我才得以进入“复课闹革命”的行列。由于我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前途很悲观,所以从此改行从事语言与逻辑的教学,并进而潜心于佛教逻辑的研究。 1976年我第二次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四人帮”倒台了。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当年杜甫听到安史之乱被平息时那种极度兴奋的心情我们也领略到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不断在“劳动改造”的“另类”人,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专业,发挥自己的专长了。 遗憾的是,那些在胡风冤案中的屈死者如阿垅、吕荧、张中晓、彭燕郊、彭柏山、郑思、伍禾、王皓、许世华、方然、费明君、满涛、苏青等人,却无缘于胡风冤案昭雪以后的大好时光了!其中吕荧是仗义执言的鲠直之士,他本不在胡风案的名单之中,但他竟在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在郭沫若作了《请依法处理胡风》的讲话之后,走上台公开为胡风辩护,结果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隔离审查了一年。十多年后,在“文革”中又被公安机关收容至北京清河农场强制劳动。1969年3月5日,呂荧在屈辱和冻饿中病逝,卒年54岁,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曾为之辩护的胡风冤案后来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杭州《浙江文艺》主编方然则是写文章为胡风辩护而被捕入狱的,关了10年,1965年获释后失去了工作,只能当一名月薪18元的小工维持生计。1966年“文革”一开始,又被无尽地批斗,他要求重回监狱而未果,于是投水自尽,年仅47岁。翻译家费明君被流放到青海后,过着非人的生活,最后竟饿死在青海,连尸骨也不知所踪。许世华是泥土社的老板,出版过不少进步书籍。胡风案中被捕后,坐了11年牢,1966年释放回家,却已是人去楼空,爱妻竟已归属他人!他在极度悲愤之下,以最慘烈的方式来抗争——上吊自尽了!另外,翻译家满涛虽于“文革”后的1978年辞世,但难于瞑目的是,他并未等到中央为胡风冤案平反。上海孤岛时期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苏青(当时与张爱玲齐名,二人是挚友)与胡风素昧平生,只因我请贾植芳先生去观摩由她编剧的越剧《宝玉与黛玉》(尹桂芳主演),事后她与贾有过一次通信,查抄贾家时此信被抄出,苏青为此而受牵连,蹲了一年半的牢,后被“宽大释放”,但未作结论,回到剧团看大门。“文革”中又被抄家批斗,并被黄浦区甬剧团开除,以至生活无着。后被黄浦区文化馆收留,1975年退休,退休工资仅43元(1954年她的工资是三百多元)。由于长期压抑、困顿,苏青己病入膏肓,于1982年年底大口吐着鲜血,含恨而亡,年仅68岁。直至1984年苏青逝世两年后,上海市公安局才为她作出迟到的平反结论。 三、历史终于给出了结论 我因说过“胡风问题历史会作结论的”而被划为“右派”。20多年以后,历史终于对“胡风问题”作出了结论。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发出七十六号文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作了平反。中央文件指出:“造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件错案的责任在中央。”并决定:“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这个中央文件出来以后虽然使胡风案得到了平反,但仍留有尾巴,不够彻底。为此,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予以补正。补正主要有三条:一、原文件仍按旧说将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所说的五个方面指责为“五把刀子”。新文件对此作了纠正。二、原文件对胡风的“宗派活动”仍有严厉的指责,新文件撤消了这种指责。三、原文件指出胡风的一些文艺思想存在着错误,新文件对此亦予以纠正。至此,胡风一案历时33年终于获得了彻底平反,有了一个公正的历史结论。当然,这一公正结论的出台,也是经过了多年的争取才获得的。如胡风于1979年获释,1980年3月从成都返回北京,1980年9月22日周扬去看望胡风,带去中央为他平反的文件,但文件中仍保留了部分旧结论,胡风未在平反结论上签字。尽管如此,胡风在获得初步平反后曾出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等职。并于1983年迁入木樨地供高知和副部级干部住的新建大楼。其夫人梅志亦于1980年7月由中国作协安排为驻会作家。胡风仍在梅志的照料和帮助下不断地申诉,但申诉并不顺利,由此而抑郁得了癌症。1985年6月,胡风病逝于北京。胡风身后,在其夫人梅志的积极争取下,又获得了中央对胡风的第二次平反(文化部长朱穆之在胡风追悼会上的悼词,但仍不彻底)和第三次平反(1988年6月18日中央《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终于使胡风案有了一个真正公正的结论。梅志在本樨地新居度过了她最后22年的安定生活,撰写了《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和《胡风传》,以及许多感人的散文。1992年起,她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1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作协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2004年梅志去世,享年90岁。 胡风一案中的难友们在1979~1981年间均已先后平反复职。如北京的牛汉,平反后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2013年卒于肺心病,享年90岁。谢韬,平反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2010年去世,享年88岁。徐放,平反后任《人民日报》社群众工作部副主任、高级记者。绿原,平反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编审。他在诗歌创作上,1998年获马其顿第37届国际诗歌节金杯奖。同年,他所译的歌德名著《浮士德》获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他的儿子、女儿因家学渊源,亦都成了翻译家。绿原于2009年逝世,享年87岁。路翎,平反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戏剧出版社编辑,因脑溢血于1994年去世,终年71岁。杜谷,平反后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1年当选为中国作协四川分会常务理事,1982年参加中国作协。天津的鲁黎,平反后复任中国作协天津市分会的领导职务,于1999年去世,享年85岁。浙江的冀汸,平反后任中国作协浙江省分会副主席。浙江宁波的孙钿,平反时已64岁,推选为宁波市八届人大常委、九届政协常委,于2011年辞世,享年94岁。武汉的曾卓,平反后重返武汉文联工作,后当选为中国作协武汉市分会副主席、名誉主席,2002年辞世,享年80岁。湖南的彭燕郊,平反后任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年去世,享年88岁。南京的化铁,平反后再度从事诗歌创作,但他的境遇不佳。大概当年他是南京空军部队的气象参谋,胡风案中被开除军籍后,失去了工作单位,只能靠打零工为生。平反后只拿到很低的退休工资。而妻子和女儿长期患类风湿关节炎,不能工作,儿子又失业在家,因此生活结据,有时鬻字为粮,聊补家用。他于2013年去世,享年88岁。安徽的张禹,曾在上海主持泥土社的编辑工作。平反后,任安徽省文联主办的《清明》杂志编审,并历任安徽省第四、五、六届政协委员。于2011年辞世,享年89岁。 上海的胡风案难友较多,最令人注目者,当首推王元化。王元化是一位学术标杆式的学者,他的三次思想反思充分显示了思想家的气质。胡风案平反后他先后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主管上海分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组长,市人大常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等。他出版的著作甚多,蒙他惠赠予我的就有十数种之多,其中《思辨录》是其思想反思的代表作。他于2008年辞世,享年88岁。 另一位是贾植芳,1980年中央为胡风案第一次平反时,仍给贾留了一个“汉奸”的罪名。我先得知此事,即转告于他。为此他于10月28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要求彻底澄清,恢复名誉。同年年底,上海市中级法院宣布贾植芳无罪,撤消1966年3月的刑事判决书。1981年初,复旦大学宣布,恢复贾植芳的教授职务。1983年,又任命他为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贾在恢复教职后,招收国内第一批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后又获准招收博士生,到80岁才停招。学校还为贾调整了住房,其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美满,还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提名奖。他于2008年去世,享年92岁。贾夫人任敏平反后结束了长达23年的分离之苦,从山西农村返回上海团聚,后因患脑溢血,于2002年离世,享年84岁。 再一位是耿庸,平反后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上海科技大学人文学系兼职教授,于1981年和1983年两度荣膺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社会公职。耿庸的原配夫人王皓在“反胡风”和“反右”的双重打击下自尽身亡。耿庸在平反后喜获年轻女编辑路莘的爱慕而重组了家庭,又分得了一套新居。我与内子朱碧莲承邀去他们的新居造访过,见他们老夫少妻相敬相爱、生活美满,殊觉欣慰。 梅林,1955年在胡风案中被捕受审查一年,释放以后调至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任编辑、副总编。1980年胡风案平反时,他已退休。1986年去世,享年78岁。 刘雪苇,平反后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1998年在北京辞世,享年86岁。 白丁(徐平羽)在胡风冤案中受审查十个月,但获释后即恢复领导职务,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化局长、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等,口碑很好。但“文革”中受江青迫害,入狱七载,以致瘫痪。1986年辞世,享年77岁。 何满子,平反后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2009年辞世,享年90岁。 罗飞,1955年胡风案中受审查后发配到宁夏,在农村中小学教外语。平反后调宁夏人民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女作家》季刊主编、编审。 尚丁,“文革”后任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新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等。2009年辞世,享年88岁。 罗洛,胡风案受审后发配青海,平反后历任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兰州图书馆馆长等。1984年调回上海,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上海分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上海市九届人大代表等。我与罗洛同为上海市九届人大代表,罗洛接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工作之后,重印了《中国学术丛书》,拙著《因明学研究》忝列其中,印数达一万冊之多,为此我与罗洛略有交往,他给我印象是沉稳而博识。他虽然在胡风冤案的难友中是年龄偏轻的一位,却离世嫌早,只享年71岁! 施昌东,平反后恢复了教职,评聘为副教授。他发表了不少美学论文,并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1979)、《美的探索》(1980年)、《汉代美学思想述评》(1981)、《一个探索美学的人》(60万言的自传体小说,1985),他还与同窗挚友潘富恩合作,写了《先秦诸子哲学思想》(1984),《中国哲学论稿》(1985)和《中国古代认识论史略》(1985)。由于过度的消耗精力和体力,1983年终因胃癌复发英年早逝,年仅51岁。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和与潘富恩合著的三部哲学著作都是在他身后出版的。临终前他入了党,《解放日报》作了美学家施昌东入党的专题报导。 在上面提到的受“胡风问题”牵连而在学校里受审查的一些人中,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均甚卓著,故于198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并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等职务。著有《洪昇年谱》《献疑集》《不京不海集》等,主编(与骆玉明共同主编)《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杰出贡献奖。由于长期超负荷劳动,终于积劳成疾,享年77岁而卒。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张德林在“反右”后被清洗出师大14年,于1978年落实政策后才返校任教。时代的紧迫感和个人的落伍感促使他夙兴夜寐地苦读苦思苦写。经过十多年拼搏,他出版了《小说艺术谈》(1986)、《现代小说美学》(1987)、《审美判断与艺术假定性》(1993)、《现代小说的多元建构》(1998),《时代见证》(2010)、并主编了《京剧艺术教程》(2000)一书。从而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并担任博士生导师。他还兼任《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的执行副主编、民盟华东师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朱碧莲,在改革开放形势的鼓舞下积极进取,也获得了不俗的成就,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先后出版了《楚辞讲读》(1986)、《宋玉辞赋译解》(1987)、《楚辞论稿》(1993)、《中国辞赋史话》(1997),《还芝斋读楚辞》(2008年,这是以上四种楚辞研究著作的修订汇编本)、《中国古代文学事典》(主编,1992)、《留青日札》(点校,1992)、《杜牧选集》(1995)、《秦汉文学史五十论》(2009,与儿子沈海波合著)、《世说新语详解》(2013)等十余种著作。其中80万言的《世说新语详解》是其晚年的瘁心之作。2013年9月14日清晨,朱碧莲教授病逝,享年82岁。膝下的一双儿女,虽生非其时(女儿生于1957年“反右”伊始,儿子生于1966年“文革”开始),随同父母经历屈辱不安的生活,然成长期遇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女儿得以留学歐美,学成归国効力,儿子在国内上大学、得深造,现在姐弟二人都成了大学教授。 当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审查后被分到外省市去工作的范伯群、曾华鹏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范伯群被分到江苏南通中学任教,曾华鹏被分配去扬州财校教语文。但他们不甘落魄,坚持业余研究。“文革”结束后,二人均进入高校。范伯群在苏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华鹏在扬州大学中文系任教,而且后来二人都担任了中文系主任,并评聘为教授、博导。1980年,二人同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还先后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他们二人虽身处两地,但长期搞合作研究,先后有五种合著出版:《王鲁彦论》(1981)、《现代四作家论》(1981)、《冰心评传》(1983)、《郁达夫评传》(1983)、《鲁迅小说新论》(1986)。二人还与贾植芳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下(1989)。此外,范伯群还著有《礼拜六的蝴蝶梦》(1989),并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2000)、《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l2冊(1994)等。曾华鹏还撰有《现代作家作品论集》等著作。曾华鵬于2013年病逝,享年81岁。 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走过的道路颇为坎坷;幸亏中年以后遇上拔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年代,犹可奋发作为一番。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亦可谓无所抱憾了。 来源:《粤海风》2016年06期,作者沈剑英(华东师范大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