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502)—共产党不会再有罗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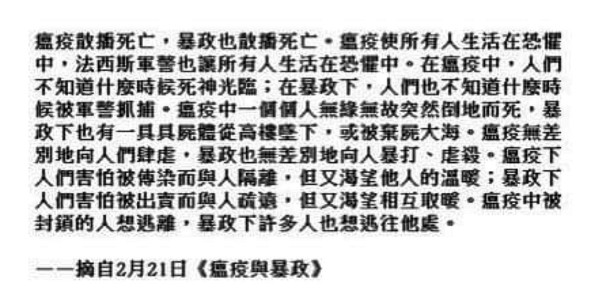

前文说「香港不会再有张敏仪」,网页有留言要我继续写「不会再有」的人物和事物。我想那是写不完的。 不过,我还是要再写一个「不会再有」的人,就是我称之为「左派文坛一代宗师」的罗孚先生。他是我晋身左派文坛的带路人,是我的恩师,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在网上搜寻「罗孚」,关于他的生平叙说,主要讲他是资深报人,原《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著名的散文作家,特别提到他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者,发掘出金庸和梁羽生这两大武侠小说名家。 罗孚自己说:「哪有这回事!……我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 一个编辑人约稿也不简单!罗孚在四十年代末随《大公报》移居香港,于1950年10月创办《新晚报》。 《新晚报》面世,即以与众不同的风格、新颖的专栏、引人入胜的文采而吸引无数读者,在数十份报纸中脱颖而出,销量直压畅销多时的《星岛晚报》。副刊中许多专栏,都是我少年时追读的文章,从中吸取不少写作养份。 1954年,香港最热门的新闻是白鹤拳陈克夫与太极拳吴公仪 在澳门的擂台比武。罗孚抓住这时机,邀约报馆中的写手陈文统(梁羽生)写连载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继而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上场。均大受读者欢迎。所谓「适逢其会」就是社会热门新闻的吴陈比武,不过罗孚能够敏感掌握时机。 罗孚来港后,就被中共吸收为党员,等于是党营后《大公报》的党委书记。他负有统战香港文化人的任务。联络著名老作家包天笑、叶灵凤、曹聚仁等。 《文汇报》当时设「文艺周刊」,借调罗孚做主编,刊登著名作家的新作,也接受来稿。 我20岁时,不知天高地厚,向这个高水准的「文艺周刊」投稿,居然屡投屡被接纳刊登。那时候,每逢周六,就急急打开《文汇报》,看自己的投稿有没有刊出。而每获刊登则不知心中有多高兴!其后获罗孚约见,又邀我参加一些文艺界聚会,我由此成为左翼文坛年轻的一员。 初识罗孚,只觉得他温文尔雅,气度非凡,又平易谦和。 「文艺周刊」虽以刊登名家作品为主,但他以文章质素而不是以作家名气取用稿件,则是我终生从事编辑工作的准则。这准则,使我其后放弃左派以「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编辑原则的政治取向。 其后我办《七十年代》,向罗先生邀稿,他也应承并写了相当长时间。在他联系右派或中间派文化人的过程中,我也有过小角色。我们一起与胡菊人、戴天、亦舒、舒巷城等结识和交往。后来他与徐复观先生往来密切,徐先生晚年文章中常提到的L先生就是罗孚。徐先生生前曾对我表示,他非常欣赏罗孚的人品、学问、文章,并说如果共产党人都像罗孚那样,中国就有救了。 但就在徐复观先生去世后一个月的1982年5月1日,罗孚这个共产党人,却突然在北京被栽上「美国间谍」的罪名,判徒刑十年。若徐先生还活着,他会觉得中国还有救吗? 关于罗孚被判间谍罪这件事,他在法庭上「供认不讳」,但既无事实陈述,而中国法庭的「供认」也绝难相信,于是外界对此始终觉得是一个谜。他儿子罗海雷在《我的父亲罗孚》一书中,说对父亲反覆追问,他也只是说:一,「他没有拿过美国人的钱」;二,在向美国人做统战工作时,对当时一些国际大事的做法和看法作了一点表达和透露,但实际上这些观点都不是什么机密。 我对这件事却不感到离奇,因为1970年妻子被隔离审查时,也曾指我是英国间谍。中共不同部门在香港有不同的「线」——公安的、军队总参的、调查部的、港澳办的,不同的线会向上级提供不同的小报告,一旦某高层误判,任何在香港帮中共做事的人,都有可能像遇到车祸那样被波及。而且一旦被捕,其他高层还欲救无从。据书法家黄苗子说,他曾经当面问过主管港澳事务的廖承志,廖说「可能是误会,现正在设法中」。而所谓设法,就是让罗孚虽背负间谍污名,却一天监牢都没有坐过,不过还是要留在北京,不能够公开活动,等同软禁。 留在北京的十一年,罗孚广交文化界朋友,也写了一些书介绍香港。其中一本叫《南斗文星高》,介绍香港一些写作界的奇人,实际上是告诉大陆人,只有在香港这样自由的地方,才会涌现出这些难以想像的写作奇才。 罗孚在北京度过1989年六四,但他在那里反而得不到资讯。 1993年他获释回到香港,他问我要了些六四时期的新闻录影带去看。他也替《九十年代》写稿。 《九十》休刊后,我主编《苹果日报》论坛版时,他也有来稿。他那时应该不是党员了。他对在北京获罪事一概不提,但对自己过去宣传革命、鼓动六七暴动却作自我批判,也参与过六四烛光晚会。他撰文说:「我所做的一些脱离实际的极左宣传,总是多少起了蛊惑人心的欺骗作用的……,牺牲了的和还健在的朋友们,当年受过损失和不便的人们,我向你们致歉!我不要求原谅,因为我自己并不原谅自己!」 2014年5月,罗孚与世长辞,终年93岁。 24日在他的追思会上,我应邀上台讲话。我引用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话说:一个人是他一生行为的总和:他所做的,和他能做的。 我认为以罗先生的才华和热诚,一生中有许多事是想做,但是不能做的。不是能力所限,而是受客观形势所限。但作为一位左派文化界的一代宗师,他一生所做的已经够多,而且在共产党及香港左派圈子中,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真诚的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