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飞机上,经历了欧洲黑暗的长冬,现在看见阳光,感觉心里都在疗伤啊! 
今天坐的是挪威航空公司,红鼻头飞机,哈哈。 现在就来聊聊北欧的SAS航空公司与挪威航空公司的故事。 以前我居住的地方很有一些瑞典SAS航空公司的人员,比如邻居老布就是,他两个儿子都是那里工作,长子混成了高管,前几年裁员,小弟问哥哥情况,哥有职业操守不肯说,最后公司以员工多加班,而不加工资来解决,尽量少裁点,因此,老布的小儿子没有下岗失业。 话说SAS公司在困难当头的时候,又出了一个挪威航空公司,挪威这些年发现了石油,不差钱啊,而且用自己家的油,嘿嘿,无法竞争[偷笑]。 那个时候,红鼻头飞机天天在我们屋顶上飞来飞去,平日不在乎,周五就有点冒火,“还让不让过日子了?” 后来瑞典空管局就给大家安装了一层玻璃门窗,瑞典的窗户个大,还是耗银子不少[偷笑],安装以后, 的确噪音减少,窗户共三层玻璃了,够重的。 挪威航空虽说无竞争,可飞行员集体罢工要求涨工资,停了二周,损失巨大,关键客户散走就麻烦大了,Ok , 涨[强]。 挪威航空开办伊始就聪明,买统一型号的飞机,这样修起来方便,瑞典SAS因为公司老,各种型号的飞机都有,修起来麻烦,光是配件,技术就拖得公司够呛。 这些都是老布邻居的心得。 这次飞行,天空湛蓝,白云非常有层次,有张力,心情愉快了很多,冬季真令人郁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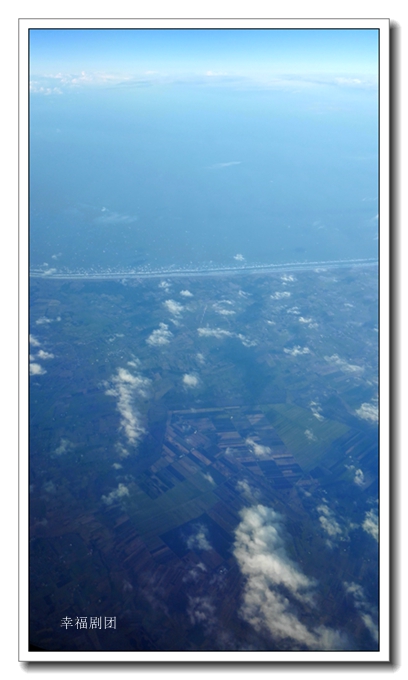




飞机转弯时所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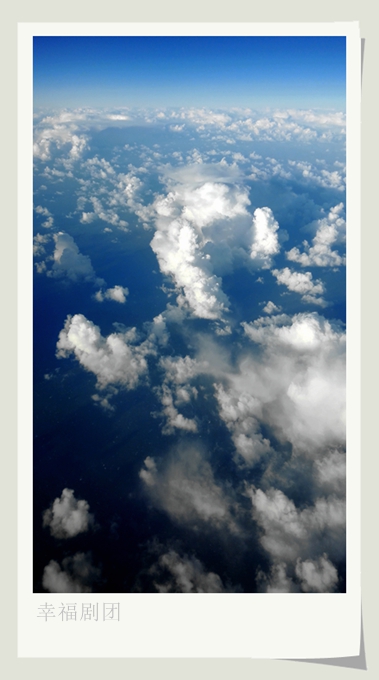

云层在阳光下,海水起倒影。 
已经接近目的地了,机场跑道可见。今天刚巧看到万维新闻讲让飞行员看到都害怕的跑道,跟这个一比,言过其实啊,哈哈哈。 
那么剧团会到哪里度假呢?

剧团要去的地方就是葡萄牙古国的离岛 ,马德拉Madeira, “马德拉就是马德拉,那份薄薄凉凉的空气,就是葡萄牙式的诗”,三毛的一句话已经把这个位于非洲西北海岸的马德拉群岛概括得极其精准。如果你对这里尚有些陌生,那么C罗的名字你一定了解,这位葡萄牙的天才球员就诞生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岛上。” 这个岛独特之处还有热带植物和热带水果的浓郁风情和滋味。 
最后附上台湾作家三毛所写的游记: 马德拉 玛黛拉游记 | 作者: 三毛 |
| 其实“玛黛拉”并不是我向往的地方,我计划去的是葡萄牙本土,只是买不到船票,车子运不过海,就被搁了下来。
第二天在报上看见旅行社刊的广告:“玛黛拉”七日游,来回机票、旅馆均可代办。我们一时兴起,马上进城缴费,心理上完全没有准备,匆匆忙忙出门,报名后的当天清晨,葡萄牙航空公司已经把我们降落在那个小海岛的机场上了。
“玛黛拉”是葡萄牙在大西洋里的一个海外行省,距本土七百多公里远,面积七百多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二十万人;在欧洲,它是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名气不比迦纳利群岛小,而事实上,认识它的人却不能算很多。
我们是由大迦纳利岛飞过来的。据说,“玛黛拉”的机场,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难降落的机场之一。对一个没有飞行常识的我来说,难易都是一样的;只觉得由空中看下去,这海岛绿得像在春天。以往入境任何国家,都有罪犯受审之感,这次初入葡萄牙的领土,破例不审人,反倒令人有些轻松得不太放心。
不要签证,没有填入境表格,海关不查行季,不问话,机场看不到几个穿制服的人,气氛安详之外透着些适意的冷清,偶尔看见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是和和气气,笑容满面的,一个国家的民族性,初抵它的土地就可以马上区别出来的。机场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它骗不了人,罗马就是罗马,巴黎就是巴黎,柏林也不会让人错认是维也纳,而“玛黛拉”就是玛黛拉,那份薄薄凉凉的空气,就是葡萄牙式的诗。
本以为“玛黛位”的首都“丰夏”是个类似任何一个拉丁民族的破旧港。——依着波光粼粼的大海,停泊着五颜六色的渔船,节节的石阶通向飘着歌曲的酒吧……
等到载着我们的游览车在“丰夏”的市区内,不断的穿过林荫大道、深宅巨厦和小湖石桥时,方才意外的发现,幻象中的事情和实际上的一切会相去那么遥远,我的想像力也未免太过分了些,“丰夏”完全不是我给它事先打好的样子。
我们的旅馆是一长条豪华的水泥大厦,据说有七百五十个房间,是“丰夏”最新的建筑之一,附近还有许许多多古色古香老式的旅馆,新新旧旧的依山而建,大部分隐在浓浓的绿荫里,配合着四周的景色,看上去真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只有我们这一幢叫做“派克赌场大放馆”的怪兽,完全破坏了风景,像一个暴发户似的跻身在书香人家洋洋自得,遗憾的是我们居然被分在它这一边。
旅馆大得有若一座迷城,豪华的东西,在感觉上总是冷淡的,矜持的,不易亲近,跟现代的文明人一个样子。
安置好房间,换上干净的衣服,荷西跟我在旅馆内按着地图各处参观了一圈,就毫不留恋的往“丰夏”城内走去。
旅馆站门的人好意的要给我们叫车,我婉拒了他,情愿踏着青石板路进城去,人行道老得发绿,一步一苔,路旁的大梧桐竟在落叶呢。与其说“丰夏”是个大都市,不如说它是个小城市镇,大半是两三层楼欧洲风味的建筑,店面接着店面,骑楼一座座是半圆形的拱门,挂着一盏盏玻璃罩的煤气灯,木质方格子的老式橱窗,配着一座座厚重殷实刻花的木门,挂着深黄色的铜门环,古意盎然,幽暗的大吊灯,白天也亮,照着深深神秘的大厅堂,古旧的气味,弥漫在街头巷尾,城内也没有柏油路,只是石板路上没有生青苔而已。
一共不过是十几条弯弯曲曲上坡又下坡的街道,一座大教堂,三五个广场,沿海一条长堤,就是“丰夏”市中心的所有了。住在“玛黛拉”那几日,几乎每天都要去“丰夏”,奇怪的是,这个可爱的城镇越认识它,越觉得它亲切、温馨,变化多端。只四万人口的小城一样有它的繁华,斜街上放满了鲜花水果,栉比的小店千奇百怪,有卖木桶的,有卖瓦片的,有鞋匠,有书报摊,有糕饼铺,有五金行,还有卖衬裙、花边、新娘礼服的,也有做马鞍,制风灯的,当然还夹着一家家服装店,只是,挂着的衣服,在式样上看去就是一件件给人穿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给人流行用的。
这儿没有百货公司,没有电影院,没有大幅的广告,没有电动玩具,没有喧哗的唱片行,它甚至没有几座红绿灯。
这真是十七世纪的市井画,菜场就在城内广场上,卖货的,用大篮子装,买货的,也提着一只只朴素的杨枝编的小篮子,里面红的蕃茄,淡绿的葡萄,黄的柠檬满得要溢了出来,尼龙的口袋在这儿不见踪迹,它是一派自然风味,活泼的人间景气在这儿发挥到了极致,而它的本身就是人世安然稳当的美,这种美,在二十世纪已经丧失得快看不见了。
这样的小城,不可能有面目可憎的人,看来看去,表情都是悦目,令人觉得宾至如归,漂泊大城的压迫感在这里是再也不可能感到的。在“丰夏”市内,碰见了几次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一连几次通过一个小得几乎看不见店面的老铺,里面乱七八糟的放着一堆堆红泥巴做出来的雕塑,形状只有两三种,鸽子、天使和一个个微笑的小童,进店去摸了半天,也没人出来招呼,跑到隔壁店铺去问,说是店主人在另一条街下棋,等了很久很久,才回来了一个好老好老的白发瘦老头。
当时我已经选好了一个标价三百葡币的天使像抱在怀里,老人看见了,点点头,又去拿了三个同样的天使,一共是四个,要装在一个破纸盒里给我们。
“只要一个,”我讲西班牙文,怕他不懂,又打着手势。
“不,四个一起。”他用葡萄牙文回答,自说自话的继续装。“一——个——,老公公。”我拍拍他的肩,伸手把天使往盒子外搬,他固执的用手按住盒子。
“一个就好了。”荷西恐他听不见,对着他耳朵吼。
“不要叫,我又不老,听得见啦!”他哇哇的抗议起来。
“啊,听得见,一——个,只要一个。”我又说。
老公公看着我开始摇头,唉——的一声大叹了口气,拉了我的手臂就往店后面走,窄小的木楼梯吱吱叫着,老人就在我后面推,不得不上去。
“喂,喂,到哪里去啊?”
老人也不回答,一推把我推上满布鲜花的二楼天台。
“看!”他轻轻的说,一手抖抖的指着城外一幢幢白墙红瓦的民房。“什么啊?”“看啊!”“啊?”我明白了。原来这种泥塑的东西,是用来装饰屋顶用的,家家户户,将屋子的四个角上,都糊上了四个同样的像,或是天使,或是鸽子,也有微笑小童的,非常美丽,只是除了美化屋顶之外不知是否还有宗教上的原因。
“是啦!懂啦!可是我还是只要一个。”我无可无不可的望着老人。这一下老人生气了,觉得我们不听话。
“这不合传统,从来没有单个卖的事。”
“可是,我买回去是放在书架上的啊!”我也失了耐性,这人这么那么说不通。“不行,这种东西只给放在屋顶上,你怎么乱来!”
“好吧,屋顶就屋顶吧——一个。”我再说。
“不买全套,免谈!”他用力一摇头,把盒子往地上一放,居然把我们丢在店里,自己慢慢走下街去了,神情这么的固执,又这么的理所当然,弄得我们没有办法偷买他的天使,废然而去。这样可爱的店老板也真没见过,他不要钱,他要传统。另一次是走渴了,看见远远街角拱门下开着一家小酒店,露天座位的桌子居然是一个个的大酒桶,那副架势,马上使我联想到海盗啦、金银岛啦等等神秘浪漫的老故事,这一欢喜,耳边仿佛就听见水手们在酒吧里呵呵的唱起“甜酒之歌”来了。很快的跑上去占了一只大酒桶,向伸头出来的秃头老板喊着:“两杯黑麦酒。”无意间一抬头,发觉这家酒店真是不同凡响,它取了个太有趣的店名,令人一见钟情。
当老板托着盘子走上来时,我将照相机往荷西一推,向老板屈膝一点脚,笑嘻嘻的对他说:“老板,合拍一张照片如何?拜托!”这个和气的胖子很欢喜,理理小胡子,把左腿斜斜一勾,下巴仰得高高的,呼吸都停住了,等着荷西按快门。
我呢,抬起头来,把个大招牌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一八三二年设立——殡仪馆——酒——吧——。”
老板一听我念,小小吃了一惊,也不敢动,等荷西拍好了,这才也飞快的抬头看了一下他自己的牌子。
“不,不,太太,楼上殡仪馆,楼下酒店,你怎么把两块牌子连起来念,天啊,我?殡仪馆?”
他把白色抹布往肩上一抛,哇哇大叫。
不叫也罢了,这一叫,街角擦鞋的,店内吧台上喝酒的,路上走过的,全都停下来了,大家指着他笑,擦鞋的几乎唱了起来。“殡仪馆酒吧!殡仪馆酒吧!”
这老实人招架不住了,双手乱划,急得脸上五颜六色,煞是好看。“你又不叫某某酒店,只写‘酒店’,聪明人多想一步,当然会弄错嘛!”我仰靠在椅子上不好意思的踢着酒桶。
“嗳噫!嗳噫!”他又举手,又顿足,又叹气,忙得了不得。“这样特别,天下再也没有另外一家‘残仪馆酒店’,还不好吗?”我又说了一句。
他一听,抱头叫了起来,“还讲,还讲,天啊!”
全街的人都在笑,我们丢下钱一溜烟跑掉了。
这叫——“酒家误作殡仪馆——不醉也无归。”
人在度假的时候,东奔西走,心情就比平日好,也特别想吃东西,我个人尤其有这种毛病,无论什么菜,只要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全都变成山珍海味。
“丰夏”卖的是葡萄牙菜,非常可口,我一家一家小饭店去试,一次吃一样,绝对不肯重复。
有一天,在快近效外的极富本地人色彩的小饭店里看见菜单上有烤肉串,就想吃了。
“要五串烤肉。”我说。
茶房动也不动。“请问我的话您懂吗?”轻轻的问他,他马上点点头。
“一串。”他说。“五串,五——”我在空中写了个五字。“先生一起吃,五串?”他不知为什么有点吃惊。
“不,我吃鱼,她一个人吃。”荷西马上说。
“一串?”他又说。“五串,五串。”我大声了些,也好奇怪的看着他,这人怎么搞的?茶房一面住厨房走一面回头看,好似我吓了他一样。
饭店陆续又来了好多本地人,热闹起来。
荷西的鱼上桌了,迟来的人也开始吃了,只有我的菜不来。我一下伸头往厨房看,一下又伸头看,再伸头去看,发觉厨子也鬼鬼祟祟的伸头在看我。
弹着手指,前后慢慢摇着老木椅子等啊等啊,这才看见茶房双手高举,好似投降一样的从厨房走出来了。
他的手里,他的头上,那个吱吱冒烟的,那条褐色的大扫把,居然是一条如——假——包——换——的——松——
枝——烤——肉——。我跟荷西几乎同时跳了起来,我双手紧张的撑住椅子,眼睛看成斗鸡眼了。茶房戏剧性的把大扫把在空中一挥,轻轻越过我面前,慢慢横在我的盘内,那条“东西”,两边长出桌子一大截。
全饭店的人,突然寂静无声,我,成了碧姬芭杜,大家快把我看得透明了。“这个——”我咽了一下口水,擦着手,不知如何才好。
“玛黛拉乡村肉串。”茶房一板一眼的说。
“另外四串要退,这不行,要撑死人的。”
不好意思看茶房,对着荷西大叫起来。
大家都不响,盯住我,我悄悄伸出双臂来量了一量,一百二十公分。我的身高是一百六十三,有希望——一串。
那天如何走出饭店的,还记得很清楚,没有什么不舒服,眼睛没有挡住,就是那个步子,结结实实的,好似大象经过阅兵台一样有板有眼的沉重。
松枝烤肉,味道真不错,好清香的。
人家没有收另外四串的钱,不附上了一杯温柠檬水给消化,他们也怕出人命。有一年跟随父亲母亲去梨山旅行,去了回来,父亲夸我。说:“想不到跟妹妹旅行那么有趣。”
“沿途说个不停,你们就欢喜了啦!”我很得意的说。
父亲听了我的话笑了起来,又说:“你有‘眼睛’,再平凡的风景,在你心里一看,全都活了起来,不是说话的缘故。”
后来,我才发觉,许多人旅行,是真不带心灵的眼睛的,话却说得比我更多。在“玛黛拉”的旅客大巴士里,全体同去的人都在车内唱歌,讲笑话,只有我,拿了条大毯子把自己缩在车厢最后一个玻璃窗旁边,静静的欣赏一掠即过的美景。
我们上山的路是政府开筑出大松林来新建的,成“之”字形缓缓盘上去,路仍是很狭,车子交错时两车里的游客都尖声大叫,骇得很夸张。导游先生是一位极有风度,满头银发的中年葡萄牙人,说着流利的西班牙文,全车的乘客,数他长得最出众,当他在车内拿着麦克风娓娓道来时,却没有几个人真在听他的,车厢内大半是女人,吵得一塌糊涂。
“玛黛拉是公元十五世纪时由葡萄牙航海家在大西洋里发现的海岛,因为见到满山遍野的大松林,就将它命名为‘玛黛拉’,也就是‘木材’的意思,当时在这个荒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凶猛的野兽,葡萄牙人陆续移民来这儿开垦,也有当时的贵族们,来‘丰夏’建筑了他们的夏都……”
导游无可奈何的停下来不说了,不受注意的窘迫,只有我一个人看在眼里,他说的都是很好听的事,为什么别人不肯注意他呢。旅行团在每个山头停了几分钟,游客不看风景,开始拚命拍照。最后,我们参观了一个山顶的大教堂,步行了两三分钟,就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滑车车站。
“滑车”事实上是一个杨枝编的大椅子,可以坐下三个人,车子下面,有两条木条,没有轮子,整个的车,极似爱斯基摩人在冰地上使用的雪橇,不同的是,“玛黛拉”这种滑车,是过去的居民下山用的交通工具,山顶大约海拔二千五百多公尺高,一条倾斜度极高的石板路,像小河似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弯弯曲曲的奔流着,四周密密的小户人家,沿着石道,洋洋洒洒的一路排下去,路旁繁花似锦,景色亲切悦目,并不是悬崖荒路似的令人害怕。
我们每人缴了大约合一百元新台币的葡币从旅馆出发,主要的也是来尝尝古人下山的工具是怎么一种风味。
在滑车前面,必然的犹豫、争执,从那些太太群里冒出来了,时间被耽搁了,导游耐性的在劝说着。
荷西和我上了第二辆车,因为是三个人坐一排的,我们又拉了一个西班牙女孩子来同坐,她跟另外三个朋友一起来,正好分给我们。坐定了,荷西在中间,我们两边两个女人,夹住他。
“好!”回过头去向用麻绳拉着滑车的两个葡萄牙人一喊,请他们放手,我们要下去了。
他们一听,松了绑在车两旁的绳子,跳在我们身后,车子开始慢慢的向下坡滑去。
起初滑车缓慢的动着,四周景色还看得清清楚楚,后来风声来了,视线模糊了,一片片影子在身旁掠过,速度越来越快,车子动荡得很厉害,好似要散开来似的。
我坐在车内,突然觉得它正像一场人生,时光飞逝,再也不能回返,风把头发吹得长长的平飞在身后,眼前什么都捉不住,它正在下去啊,下去啊。
突然,同车的女孩尖叫了起来,叫声高昂而持续不断,把我从冥想里叫醒过来。“抓住荷西,抓住荷西!”我弯下身向她喊。
她的尖指甲早已陷在荷西的大腿上,好似还不够劲,想穿过荷西的牛仔裤,把他钉在椅子上一样,一面还是叫个不停。荷西痛不可当,又不好扳开她,只有闭着眼睛,做无声的呐喊,两个人的表情搭配得当,精采万分。
站在椅背后的人看到这种情形,跳了下来,手中的麻绳一放,一左一右,开始在我们身后拉,速度马上慢了下来。
回头去看拉车的人,身体尽量向后倾,脚跟用力抵着地,双手紧紧拉住绳子,人都快倒到地上去了,这样的情形,还跟着车在小跑,不过几分钟吧,汗从他们戴的草帽里雨似的流下来。“上车,踩上来,我们不怕了。”我大声叫他们,那个女孩子一听,又开始狂叫。“上来!”我再回身去叫,拖车的人摇摇头,不肯,还是半仰着跟着小跑。这时,沿途的小孩,开始把野花纷纷向我们车内撒来,伸手去捉,抓到好几朵大的绣球花。
好似滑了一辈子,古道才到尽头,下了车,回身去望山顶的教堂,居然是一个小黑点。山路从下往上望,又成了一条瀑布似的悬挂着,我们是怎么下来的,真是天知道。
拉车的两个人,水里捞出来的似的湿透了,脱下了帽子,好老实的,背着我们,默默的在一角擦脸汗,那份木讷,那份羞涩,不必任何一句语言,都显出了他们说不出的本分和善良,我呆望着他们,不知怎么的感动得很厉害,眼睛一眨一眨的盯住他们不放。荷西在这些地方是很合我心意的,他看也不看我,上去塞了各人一张票子,我连忙跟上去,真诚的说:“太辛苦你们了,谢谢,太对不起了!”
给小账当然是不值得鼓励,可是我们才缴不过合一百块台币,旅行社要分,大巴士要分,导游再要分,真正轮到这些拉车的人赚的,可能不会占二十分之一,而他们,用这种方式赚钱,也要养活一大家人的啊!
我们抵达了好一会儿之后,才有一辆又一辆的滑车跟了下来,那些拉胖太太们的车夫真是运气不好,不累死才怪。
我注意看下车的游客,每一个大呼小叫的跨出车来,拍胸狂笑,大呼过瘾,我一直等着,希望这一排十几辆车,其中会有一个乘客,回身去谢一句拉车的人,不奢望给小费,只求他们谢一声,说一句好话,也是应该的礼貌,可是,没有一个人记得刚刚拉住他们生命的手,拉车的一群,默默的被遗忘了。这种观光游戏,是把自己一时感官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劳力辛苦上,在我,事后又有点后悔,可是不给他们拉,不是连糊口的钱都没有了吗?
当时我倒是想到一个减少拉夫辛劳的好方法——这种滑车其实并不是一定要全程都拉住车子不放的,车速虽快,可是只要每几十公尺有人用力拉一把,缓和冲力,它就会慢下来。其实,只要在滑车的背后装两枝如手杖一样钩的树枝,拉夫们每两个一组沿着窄窄的斜道分别站下去,像接力赛似的,每一辆滑车间隔一分钟滑下来,他们只要在车子经过自己那一段时,跳上去,抓住钩子,把车速一带,慢下来,再放下去,乘客刚刚尖叫,又有下一段的拉夫跳上来拉住,这样可以省掉许许多多气力,坐的人如我,也不会不忍心,再说,它是雪撬似的,没有轮子,路面是石板,两旁没有悬崖,实在不必费力一路跑着卖老命。
我将这个建议讲给导游听,他只是笑,不当真,不知我是诚心诚意的。
细细分析起来,“玛黛拉”事实上并不具备太优良的观光条件。它没有沙滩,只有礁岩,没有优良的大港口,没有现代化的城市,也谈不上什么文化古迹,离欧洲大陆远,航线不能直达……可是游客还是一日多似一日的涌来“玛黛拉”。
当地政府,很明白这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小岛,要吸引游客总得创出一样特色来才行,于是,他们选了鲜花来装饰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比花朵更能美化环境的了。
“丰夏”的市中心不种花,可是它卖花,将一个城,点缀得五颜色六色,“玛黛拉”的郊外,放眼看去,除了山林之外,更是一片花海。我们去的时候是秋天,可是车开了三百多公里的路,沿途的花没有断过,原先以为大半是野生的,因为它们没有修剪的匠气,茂茂盛盛的挤了个满山满谷,后来跟导游先生谈起来,才发觉这些绣球花、燕子花、菊花、中国海棠、玫瑰,全是居民配合政府美化计划一棵一棵在荒野里种出来的,不过十年的时间吧,他们造出了一个奇迹,今日的玛黛拉,只要去过的人,第一句话总不例外的脱口而出:“那些花,不得了!”三百多公里的道路,在我眼前飘过的花朵不下有亿万朵吧,这样的美,真怀疑自己是否在人间。
同游览车内的两个中年太太,大概实在忍不住花朵的引诱,伸手在窗外采了两朵白色的玫瑰,导游一转身看见了,只见一向和蔼有礼的他,脸色突然胀红了,狮子似的大吼一声,往这两个太太走过去,他拿起麦克风来开始在全车的人面前羞辱她们,大家都吓坏了,这个导游痛责破坏他乡土风景的游客,保护花朵有若保护他的生命一样认真,几亿朵花,她们不过采了两朵,却被“修理”得如此之惨,这是好的,以后全车的人,连树叶都再也不敢碰一碰了。
怎么怪导游不生气,花朵是玛黛拉的命脉之一啊。
“玛黛拉”的松树长在高山上,杨树生在小溪旁,这儿的特产之一就是细直杨枝编出来的大小篮子和家具,非常的雅致朴实,柳树看得多了,改看杨枝,觉得它们亦是风韵十足,奇怪的是,每看杨树,就自然的联想到《水浒传》,李逵江边讨鱼,引得浪里白条张顺出场的那一章里,就提到过杨树。
岛上的居民几乎全住的是白墙红瓦的现代农舍,四周种着葡萄和鲜花,一丝也看不出贫穷的迹象来。
在岛的深山里,一个叫做“散塔那”的小村落,却依然保持了祖先移民房舍的式样。
茅草盖着斜斜的屋顶,一直斜到地上,墙是木头做的,开了窗,也有烟囱,小小的窄门,胖子是进不去的,这种房子,初看以为不过是给游客参观的,后来发觉整个山谷里都散着同式样的房子,有些保持得很好,漆得鲜明透亮,远看好似童话故事中的蛋糕房子一般。
“散塔那”坐落在大森林边,居民种着一畦畦的蔬菜,养着牛羊,游客一车车的去看他们的房舍,他们也不很在意,甚而有些漠然,如果换了我,看见那么多游客来参观,说不定会摆个小摊子卖红豆汤,不然,钉些一色一样的小茅屋当纪念品卖给他们,再不,拉些村民编个舞唱个狩猎歌,也可以赚点钱。可贵的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在这个山谷里,没有如我一般的俗人,游客没有污染他们,在这儿,天长日久,茅草屋顶上都开出小花来,迎风招展,悠然自得,如果那田畦里摘豆的小姑娘,头上也开出青菜来,我都不会认为奇怪,这个地方,天人早已不分,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了。
回归田园的渴望和乡愁,在看见“散塔那”时痛痛的割着我的心,他们可以在这天上人间住一生一世,而我,只能停留在这儿几十分钟,为什么他们这么安然的住在我的梦乡里,而我,偏偏要被赶出去?
现实和理想总没有完全吻合的一天,我的理想并不是富贵浮云,我只求一间农舍,几畦菜园,这么平淡的梦,为什么一样的辛苦难求呢?旅行什么都好,只是感动人的事物太多,感触也因此加深,从山林里回到旅馆,竟失眠到天亮。
离开“玛黛拉岛”的前一天,我们在旅馆休息,很欢喜享受一下它的设备,可惜的是,它有的东西,都不合我的性情。夜总会、赌场、美容院、三温暖、屋顶天体浴、大菜间、小型高尔夫球,都不是我爱去的地方,只有它的温泉游泳池,在高高的棕榈树下,看上去还很愉快,黄昏时,池里空无一人,去水里躺了个痛快,躺到天空出星星了才回房。
七日很快的过去,要回去了,发现那双希腊式的凉鞋从中间断开了,这双鞋,跟着我走过欧洲,走过亚洲,走过非洲,而今,我将它留下来,留在旅馆的字纸篓里,这就是这双鞋的故事和命运,我和它都没料到会结束在玛黛拉。
行李里多了一只粗陶彩绘的葡萄牙公鸡,手里添了一个杨枝菜篮,这是我给自己选的纪念品。
回到大迦纳利岛家里,邻居来问旅行的经过,谈了一会,又问:“下次去哪里啊?”“不知道啊!”漫然的回应着。
人间到处有青山,何必刻意去计划将来的旅程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