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担心的是禁书,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读书;在奥威尔笔下,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赫胥黎笔下,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高伐林
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长篇小说《1984》,肯定不会觉得陌生。这本书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与苏联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被合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书中描绘了极权国家“大洋国”的可怕景象:自由遭剥夺,思想受钳制,生活被压缩,尤其是人性被逼迫到不分是非善恶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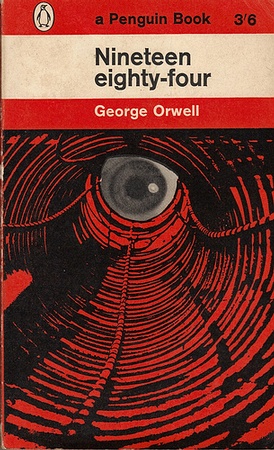
1961年企鹅版《1984》,是1961-1972年间企鹅的美术总监Germano Facetti设计的。
《1984》出版后48年在中国才开禁
《1984》是奥威尔辞世前最后一部著作,小说中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衍生出“奥威尔式”(Orwellian)、“奥威尔主义”(Orwellism)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作家和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乔治·奥威尔1903年生于印度,他的父亲在当地殖民地政府供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或没有钱财的中产家庭”。一岁时,母亲带他先回到英国。他自幼天资聪颖,11岁时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诗作《醒来吧,英格兰的小伙子们》。14岁又考入著名的伊顿公学,还获得了奖学金。但早在小学时期,他已经对不平等有了初步的体验。
1921年,奥威尔从伊顿毕业后考取了公职,到缅甸当了一名帝国警察,在那里,殖民地民众的悲惨生活无时不在刺激他的良知。他深深感到“帝国主义是一种暴虐”,遂于1927年辞了职,写下多部作品描写这段生活。
1928年1月回国,25岁的奥威尔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四处漂泊流落。尽管他自幼就体弱多病,但在巴黎、伦敦两地,他当过洗盘子的杂工,住过贫民窟,并常常混迹在流浪汉和乞丐之中。次年,写下了关于这段经历的纪实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
奥威尔思想上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36年,有出版商聘请一位属于“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见证人”的作家,去北部工业区实地调查工人的穷困状况。奥威尔欣然应聘,历时数月,通过自己亲眼所见,记述了大量事实,谴责资本主义工业化对人性的摧残,还主张用社会主义来拯治社会的弊端。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威尔与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于保卫共和政府的战斗。他在前线担任少尉,喉部曾受重伤,为记述西班牙内战而写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书,后来成为关于这场内战的权威性文献。
但是,没死于法西斯枪弹下的奥威尔,差一点丧身在共和政府内部党派之争的倾轧中。这个惨痛的经验对奥威尔影响巨大。他曾说自己“从1930年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而这时候,他又开始考虑“捍卫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了。这个思想,影响到他后期的两部名作,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动物庄园》和《1984》的创作——仅以这两部作品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
作者是1948年写完《1984》,1949年出版,此后全球不知出版了多少种版本,总计销量超过5000万册(2003年统计)。但是1949年恰逢中共建政,这本书当然被视作“洪水猛兽”,在很长时间内列于“禁书”名单。即使到开始解冻、改革开放之后,也很长时间被限制发行。我在中国时到处打听这本书的中译本均不可得,是到美国来后才得知,这本书的中译本1985年在大陆“内部”出版过,1997年公开出版,但购买者必须买一整套丛书,不拆开卖。难怪发行量少了。不过,现在在中国大陆,《1984》已经有了张晓辉译本、孙仲旭译本、董乐山译本……还出版了台湾刘绍铭译本,据有人统计,中文简体字版已经出版了不少于八个译本。可见,思想的传播,终究还是阻挡不住的。
中国读者并不太看重《1984》
不难想见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比起男女主人公的悲欢故事,更让我震惊不已的是政权专管内部清洗的“友爱部”、专管思想控制的“真理部”这些名称、无所不在的“电幕”、标语“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还有真理部大厦的墙壁上铭刻的三句宣言:“War is Peace;Freedom is Slavery;Ignorance is Strength。”(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与中国大陆现实的高重合度。以致于不由得发出“作者写的不就是中国,就是今天么”的惊叹。感受最深的,当然就是小说中的“老大哥”,无止无休地按照最新的政治需要修改历史,销毁一切不符合最新口径的历史档案、书籍——主人公的工作就是干这个:奉命从过去的报纸、杂志、书籍,各种影像中删除某个人,就好像他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
不过,一个不无奇怪的现象是:中国人似乎并不太把《1984》当回事。这本书影响全世界,但在中国,尽管已经有了多种版本,可以自由选购,但是市场反应却平平。
两位读书人刘苏里和止庵在《1984》英文版出版60周年时,做了一次对谈。止庵说:“我看过两部根据《1984》改编的电影,都不大成功。我从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把书中的事情具体化的时候,就显得很简单,也很单薄,甚至不真实了。奥威尔这本书我第一次看是1985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其间看过不止一遍。我只要有机会就推荐这本书,这你也知道。有人问起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我想了半天还是举出这本。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在中国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它理应受到这种重视。”
止庵还说:波兰的米沃什曾对《1984》由一个英国人写出感到遗憾。这句被一个苏联人转述过。“我读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感觉。《1984》在欧美都是课外必读书,它的销量特别大,就是因为上中学就要看这本书。回到中国,我这么强调《1984》,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在中国实际上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除了在知识界个别有点反应之外。”
《往事并不如烟》写了百分之一
《1984》已写到百分之百
止庵曾回忆:“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参加朋友聚会,有位老先生非常兴奋地谈论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我当时说,在您感兴趣的那个方向上,走到头是百分之百,《往事并不如烟》大概才写了百分之一,我们由此可以想到百分之五,这样您就非常激动了。但是我告诉你有一本书,早已写到百分之百了,就是奥威尔的《1984》。您一辈子都想不透的东西,他已经早替您解决了。” 止庵这句话深获我心。我确实觉得,《1984》已经把道理讲的再透不过了。
止庵甚至说:“有关这个问题,你真是不能再说什么《1984》没有揭示过的了。”“不要只看具体写到什么,它从本质上揭示了一切。”
“苏联后来的解体当然并不是因为有了《1984》,但是《1984》至少使得铁幕以外的人不再相信苏联代表着人类的方向了。”刘苏里同意止庵的这个看法,并补充说:“起码苏联体制在欧洲蔓延的可能性,很大程度被这本书遏制了。”
《美丽新世界》:另一种预警
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中的另一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名“勇敢面对新世界”,为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于1931年创作、1932年发表的反乌托邦作品。书名得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米兰达的对白:“人类有多么美!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头!(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
这个书名,其实是在讽刺:新世界虽然“看上去很美”,其实科技并没有推动社会精神进步,相反,人类已经人性泯灭,成为在严密科学控制下,一群被注定身分和命运的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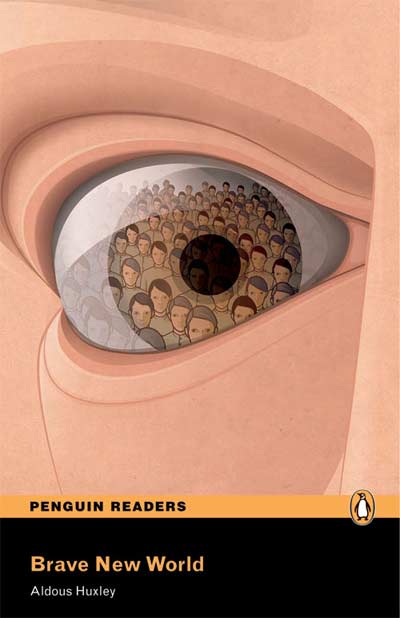
《美丽新世界》
37岁的赫胥黎从飞速发展的汽车工业身上,预感到未来的国家机器将不再用警察和军队来维持统治,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高科技手段。统治的目标将是经济繁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类也将被改造。于是写了这本薄薄的十多万字预言小说,不胫而走。 小说中的“美丽新世界”有高度的物质文明,所有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人们不愁吃穿,享受着最舒适的生活,每天下班以后,可以乘坐私人的超音速飞机,去世界各地度假旅行。经济繁荣和享受生活成为整个社会唯一的哲学理念、唯一的宗教。第一个采用流水线生产的亨利·福特被视为新的上帝,他生产出第一辆“福特”T型车的1908年被作为新的纪元元年(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福特632年,也就是公元2540年)。
赫胥黎叙述:人类认识到了科学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享受了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丰富的物质产品,也同时发现了这种生活模式的脆弱性。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不稳定因素——大到战争动乱,小到失恋生病——都会影响到物质生产,进而在不同程度上使人类社会发生混乱和倒退。于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保证各种物质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实现人类的幸福,就有必要消灭这些不稳定因素。“美丽新世界”的设计者认识到,改造社会的基础在于改造人。以前诸次社会革命,之所以成果不大,就在于它们对人的改造还不彻底。“美丽新世界”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四个方面彻底改造人。
1,杜绝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建立万无一失的优生体系。人类的出生地不再是医院产房,而是类似高级养殖场的“人类孵化中心”。为了防止父母的不良基因遗传给新生儿,胎生被取消,人是直接在孵化车间里被创造的,身上只含有优良的基因,所有对社会稳定繁荣不利的基因都将被去除。
2,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高质量的人来完成的。让有才干的人去干低级工作,他势必会感到非常痛苦,这就为社会不安定埋下了隐患。低等人的活只能让低等人去干,因为他们不会觉得是牺牲。所以对人从胚胎时期进行识别和分类,不同等级的胚胎将接受不同的培养,并且用各种手段强化胚胎之间的差别,以便适应将来不同岗位的需要。
3,还必须让每个人安心接受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等级,忠于自己的等级,这样才能避免等级之间的冲突。这必须靠宣传和教育来实现。一旦人在思想上接受了社会现实,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就不会有自觉的动力去改进社会,那么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就消除了一大半。
4,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产生很多烦恼和痛苦,必须找到办法来消除它们。最常见的烦恼有两种,性压抑和衰老。为了使每个人性欲都能得到充分的满足释放,“美丽新世界”提倡性的泛交,男女之间不再有夫妻关系,而只有性交关系。至于征服衰老,必须“给他们保健,不让他们生病,人工维持他们的内分泌,像年轻人一样,给他们输入年轻人的血液,保证他们的新陈代谢永远活跃。”
小说开始时,近乎全部人都住在城市。他们在出生之前,就已被划分为“阿尔法(α)”、“贝塔(β)”、“伽玛(γ)”、“德尔塔(δ)”、“爱普西隆(ε)”五种“种姓”。阿尔法和贝塔最高级,在“繁育中心”孵化成熟为胚胎之前就被妥善保管,以便将来培养成为领导和控制各个阶层的大人物;伽马是普通阶层,相当于平民;德尔塔和爱普西隆最低贱,只能做普通的体力劳动,而且智力低下,尤其是许多爱普西隆只能说单音节词汇。有情绪问题,就用一种叫作“索麻”(Soma)的无副作用致幻剂麻痹。“家庭”“爱情”“宗教”统统成为历史名词,社会的箴言是“共有、统一、安定”。
“美丽新世界”的设计者明白,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控制人的思想,他们也不允许思想自由,但採取的办法,迥异于《1984》国家用快乐和消遣作为思想的替代品,思想的空白被各种各样的娱乐和感官上的刺激所填补。人们也不再信仰上帝,而转而信仰亨利·福特。幸福不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之一,而反过来成为人的枷锁。
小说中设置的环境如上,具体情节是:一个“野蛮人”约翰和母亲,由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野蛮人保留区”进入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最大政权“世界国”的重要城市伦敦。“野蛮人”约翰有太多使当地人不解的地方,而他对伦敦也有太多不解,为了人生的自由、为了解放城市人而努力,却受尽城市人的白眼、取笑,陷入绝望,直至最后自杀而死。
“野蛮人”约翰说: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我现在就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当他被告知说,他的要求,实际上就等于“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害怕明天会发生的事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
在一阵良久的沉默之后,约翰终于开口:“这一切我都要求。”
奥威尔的预警赠给中国
赫胥黎的预警奉送美国和世界
跟《美丽新世界》比起來,当然《1984》名气和影响要大得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23年至今最好的百部英文小说之一,1984年还被改编成电影上映。1984年苹果公司为推出自己的新产品——苹果电脑,请来大导演雷德利·斯科特为其拍摄广告,灵感正是来自奥威尔的《1984》:不到1分钟的广告上,只见苹果电脑推出,让人民终于逃脱思想的奴役,将“老大哥”讲话的“电幕”砸得粉碎。《1984》的故事深入人心,以致著名作家村上春树都要从这个书名演化出自己新著的书名——“1Q84”,煌煌上中下三大册小说写得很精彩,让我读得欲罢不能。 但是我最近读的一本书《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尼尔·波兹曼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开宗明义却断定:
——“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尼尔·波兹曼(1931~2003。作者名为Neil Postman,在我看来,译为“波兹曼”并不准确,但既然已经传开,就姑且从众吧)是一位有世界名声的媒体文化学者、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创办了媒体生态学专业,并长期担任文化传播系主任。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就直截了当地写道: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来比较这两个可怕预言的不同: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
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在《1984》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
波兹曼的结论是:“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号!波兹曼更担心的、认为更可能成为现实的,并非奥威尔的预言,而是赫胥黎的预言。
当读完全书,我深切地感到,他说得极有道理。但是,要加个限制词,他发出警号所针对的对象,并不是中国等极权、威权体制的国家,而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他的上述警告,应该改作:“可能成为西方的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而对眼下的中国而言,还是奥威尔的预言更像达摩克里斯的悬剑——不过,当然,赫胥黎预言的情况也已经出现,危险性在逐步上升。
而对于美国来说,正处在赫胥黎预言的笼罩中。
换句话说:奥威尔的预言,是中国今天要面对的问题;而赫胥黎的预言,还不是中国的今天,而是明天的问题;但已经是美国、西方今天面对的问题。
波兹曼为什么会如此断言?他是怎么论述的?
当我写到这里,有别的事务岔了进来,暂时搁笔,明天接着聊。
相关文章: 中国有识之士也更警惕“赫胥黎预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