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直言本朝高祖皇帝早年是个无赖,“今上”汉武帝也有各种失德;他不以成败论英雄,把汉朝之敌项羽写成烈士列入“本纪”;陈涉在他眼里也非“反贼”,而是英雄。我们今天应该接续太史公“绝唱”
老高按:龙尾巴最后一甩即将转身离去,蛇信子已经触手可及——每次龙蛇之交,我一想象,感觉都不是太好;想到毛泽东、习近平,这两位年龄整整相差六十年的大人物,竟然都是属蛇(记得有一篇文章,忘了作者是谁,形容习是“酱缸里的蛇”),难道是偶然的?这个念头让我感觉更糟;再想想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蛇年——1917年,1929年,1953年,1965年,1989年,2013年……对于中国人而言,似乎不是爆发大灾难,就是在孕育大灾难!
蛇年除夕前我这些胡思乱想,肯定不符合逻辑,就算向喷我的朋友递上几把刀子,当作新年贺礼吧。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都感到社会进程、历史演化都猛然加速,像我这样进入人生暮年的衰翁,更是感到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就是一天、一月、一年。许多事好像发生没多久,细算起来却是三年五年乃至十年八年之前了!
不由得感到时光不停不歇地、铮铮有声地从身边飞速流逝:当下的这一分钟、一秒钟,转瞬就成了过去,进入历史。正巧读到秦晖教授一篇文章说:“此刻之前的事,对此刻而言已是历史,而此刻的事,对此刻之后而言也是历史。”——深获我心!
秦晖教授这篇强调“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的文章,其实并非新作,但最近被一些自媒体和播主翻出来,我感到并未过时,便去找了找,转载于下。我发现不少转载者竟然都或多或少有删改,不知原因为何,似乎是对敏感词有所避讳?我转载的这个是相对最完整的,但是否就是原文全文,我也并无把握。
史学要与权势保持距离,而非与现实保持距离
秦晖,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4期
昨天人们面对的现实,就是今人所谓之历史;而今天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明天所谓的历史。而且这个昨天、明天当然可以是比喻——意指可能很遥远的过去与未来,但也可以指24小时之前,甚至此刻之前的事,对此刻而言已是历史,而此刻的事,对此刻之后而言也是历史。当然实际的历史学著述几乎没有写到“此刻以前”的,但这只是技术上来不及写,或者说事情还没完也没法写。史学著述没写也不能说就不是历史,正如古代很多事史书上没写,但它们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一样。
所以,历史与现实并没有隔着一堵墙。现在有些人说:历史学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这话要看怎么说。如果说对身在其中的事容易产生情感或价值观上的偏见,而学术研究应该尽量避免偏见的影响,对身在其中的事“让后人来评说”,那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事实记录而言身在其中却有后人不及的优势,很多事如果今人不留下记忆,后人就没法评说。而且偏见这东西,严肃的史学家主观上当然要尽量避免,尤其不能像有些“后现代”学者那样根本否认史实的客观性,而把史实仅仅当做一种“叙事”,从而为胡编乱造的“影射史学”开方便之门。但是主观上尽量避免,客观上其实也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即便对于古代史,研究者也很难真正保持“价值中立”。所以对于史学的客观性一方面当然要求史学家秉笔直书讲究“史德”,另一方面更有赖于学术自由。人们很难完全避免偏见,但社会应该做到不能只有单方面的偏见,更不能用学术之外的权力去制造“一面倒的偏见”来单方面遮蔽事实。古人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今人所谓多元化“片面的深刻性”,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可以互相纠错而达至对客观性的“无限逼近”,都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史学与现实保持距离的意思是回避“风险”,那就更值得商榷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史学要与权势保持距离,而非与现实保持距离,不是为免招怨于权势而回避现实,更不能为讨好权势而捏造“现实”。我国古人就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榜样,而今日世界上,“现当代史”的发达与否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史学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都知道,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未必意味着历史学受到重视;而史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也未必意味着它的学术水平一定就高。我们中华文明历史当然很悠久,但平心而论,应该承认它并非最悠久的。尽管今天人们在运用各种考古手段把已知的文明史往前延,但不要说更远,就与较近的古印度河流域文明相比,据说是我们夏朝都城的河南二里头遗址不但比印度河畔的摩亨佐·达罗等古城要晚不少年,而且二里头那些土墙草顶的“宫殿”怎么说也没法与烧砖砌就、上有重楼、下有全城规划的下水道系统的古印度河流域建筑相比,据说是汉字雏形的二里头刻画符号,也没有摩亨佐·达罗象形文字那么丰富成形。
但是古印度文明虽然历史悠久,它却是个“没有历史的文明”,灭亡了的古印度河城邦且不论,就是后起的雅利安人印度文明虽然宗教文化高度灿烂,引得很多中国高僧都要去取经,却仍然没有什么连续可考的历史纪年可言,以至于如今国际印度学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靠法显、玄奘等中国取经者的汉文记载,去大致还原那时的印度史。比起印度文明来,我们自古以来史学就是显学,古代知识体系中历史学享有很高地位,历代史籍的积累号称“浩如烟海”,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遗产。
但是史学在我国文化传统中地位虽“显”,却一直有厚古薄今的特点。而且不仅是价值意义上的“厚古”——以“复古”的名义推动历史,典型的如西方当年的“文艺复兴”,无可非议——更是利害意义上的“避今”,这就是个问题了。
大家知道中国言论禁忌比较多,普遍认为当代人写的当代史是不可信的。一般来讲,能传世的历史学名著都是写前代的历史。尤其是正史,除了司马迁。所以我们说司马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说是“史家之绝唱”)。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司马迁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当然他也写了汉代以前的,但是至少《史记》里相当一部分写的就是汉代的事。而且他直言本朝的高祖皇帝早年是个无赖,“今上”汉武帝也有各种失德之处,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把汉朝的敌人项羽写成烈士,列入“本纪”;出身贫困而率先反抗“暴秦”却失败身亡的陈涉,在他眼里也不是“反贼”,而是英雄,列入“世家”。写本朝历史能够像他这样直言的,除司马迁再无二人。当然司马迁以后不是说没有当代人写当代史,但是除了良莠不齐的民间“野史”外,官方组织修的当代史除了有的被后人当做资料来参考外,作为成书很少能传之后世,因为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拍马屁著作,朝代一换,就被人扔进垃圾堆里。
于是我们看到的二十四史,《史记》以下的各史都是后代人写前代史的。以至于到了1980年代改革初兴时,大陆有人提出要修民国史。消息传到台湾后曾经引起讨论。那时台湾还没有开放党禁,国民党有意识形态控制,两岸有很多相似之处。大陆搞民国史,台湾就着急了,他们要不要搞呢?当时有些人说如果我们不搞,那就只有“□□”搞,我们就没有话语权了,这不行。可是另一些人说,如果我们也搞民国史,那岂不就意味着民国已经完了?因为按司马迁以后的传统,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本朝亡了以后下一朝代的人写的。大陆认为民国已亡,当然就可以搞民国史,但台湾一直宣称延续中华民国,他们怎么可以搞“本朝”史呢?于是就搞得他们左右为难。当然现在已经没这问题了,现在一方面那里已经实行言论自由,可以直言无忌地搞民国史了。另一方面台湾“绿营”不认同民国的大有人在,他们当然更无忌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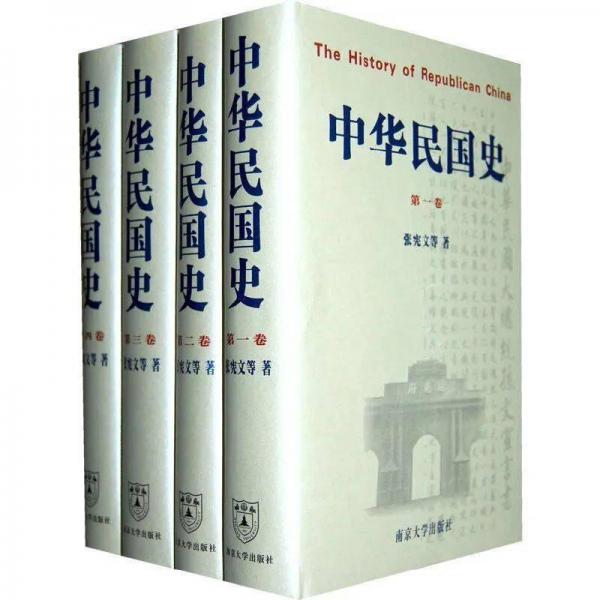
我们这边也有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已故的高华教授原来是搞党史的,而党史按照我国官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就不是历史。“党史”是“二级学科”,它所属的一级学科并不是“历史学”,是什么?原来,党史是属于“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这个学科,不算历史学的。也就是说,党史在中国被当作一门意识形态。例如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原来设有党史系,但它属于原来意识形态那一片,不属于史学片。人大有历史系,清史所,那是属于史学的,但党史系就不属于,他们培养的博士也不是史学的博士,而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科出来的博士。
我国的史学有这样的划分,可是其他国家的史学不是这样,比如过去苏联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也许因为苏联的历史不太悠久,不管怎么说,剧变以前的苏联史学界搞现代史的已经是主流,有人统计当时苏联史学界的文章,外国史除外,俄苏本国史的文章大概80%是1917年以后的苏联当代史研究和1861年以后历史的研究。而1861年以前的俄国史,在苏联整个史学体系中占的比重其实不大。
美国当然更是这样,固然在新大陆如果说古代史,那只有印第安部落。因此研究美国史几乎就是近现代史。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美国没有研究禁忌,所以当代美国史研究就很兴盛,例如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是美国当代史一大热点,越战1975年结束,到1980年代美国史学界就已经出现了一批越战史专家,出版了好几种多卷本著作,如威廉·C·吉本斯的4卷本《美国政府和越南战争》等,这在我们司马迁以后的传统中是不可能的。
司马迁以后搞历史好像就是要搞前代的,以避开禁忌,要是搞得近一点,好像就不是历史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我们今天应该接续太史公的“绝唱”,同时也是跟上时代的潮流。历史并不遥远,我们都生活在历史中。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很多理解有助于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很多理解,也有利于加深了解我们的现在。高华先生的可贵,就在于他把党史当作历史,而不是当作意识形态来搞,在直言“本朝”史方面敢为天下先,这是了不起的。
近期文章:
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人生没意义了
许多挚友被或左或右极端潮流裹挟而去,剩下我形影相吊
对“白左”的非正式研究:标签的后面是什么?后果是什么?
过去的这一年,难忘那些逝去的人
美国与俄罗斯两位重量级政治思想家对话全文
川普再次进白宫,与八年前首次进白宫面对的中国大不一样
下一代人若想有出息,就别听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没想到这部俄罗斯小说竟成为习近平的精神指南
美国的名校为什么左翼思潮占绝对上风
川普看到了美国真的病状,但他是否能开出对的药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