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读者赞赏许倬云的宏阔通透,部分专业学者却质疑其“考据密度”不足,甚至嘲讽他“宏大叙事的段子手”。批评却未能撼动他的读者缘,不少曾狂热追捧民族主义叙事的青年,在阅读许倬云的文本后,转而开始讨论“天下主义”“多元文明对话”
老高按:今天早上一睁眼就惊悉一个噩耗: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今晨去世,享年95岁。
震惊之下,立即写了一条X(即推特),说:“许倬云先生患有先天肌肉萎缩,有人预言活不过15岁。但他用近一个世纪岁月告诉世人:输在起跑线,也能成为人生赢家。……”
虽然我早就知道许倬云先生,读过他一些著作,但并不很喜欢,关注课题和语言风格我都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有些观点我也不以为然。但我的一位大学同窗,读博士成为许先生的关门弟子;另一位好友多年前就深得许先生的青睐,许先生看好其潜质,抱有厚望。他们讲述过许先生的一些轶事,例如说起许先生与金庸的交往,金庸在其《明报》连载武侠小说,许倬云竟然是天天追读《明报》豆腐块的粉丝,催促每天多登一点,甚至忍不住要求作者透底:某个人物后来到底如何了?让我这个“金庸迷”大感亲切。
上个星期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抓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好像文人写手早就盘马弯弓、枕戈待旦地等着了,消息一出来,当天就呼啦啦喷涌出来那么多精彩文字和视频?今天我也同样感到惊诧:许倬云先生今晨去世到下午三点的此刻,不过十来个小时吧?网上竟然就出现了数百篇悼念、缅怀、甚至全面评价许倬云的文章,其中固然有感事应景的急就章,却也不乏旁征博引、掰开揉碎的剖析文章。这里我转发两篇短文。
第一篇是加拿大的好友谢宝瑜发来的,他十九年前创作了一部反映毛泽东时代中农民和地主悲惨命运的长篇小说《玫瑰坝》,是这一代大陆背景的作者写出的第一部尖锐揭露中共土改残酷罪行的作品,谢宝瑜自己成立了一个绿野出版社,出版这部60多万字的作品,受到广泛重视,我在我的博客上也曾经做过介绍。今天读谢宝瑜这篇文章才知道,原来许倬云先生主动要求为这部小说再版电子版写序,还对作者坦承:读到小说女主人公之死时,流下了热泪。
另一篇,是我上午11点半在电子邮箱中收到的马四维文章《在时间切面上取火——许倬云生平、史观与民族文化观评述》,快不快?
许先生的成就、得失如何,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但许先生的两个警句,铭刻在我的心底:
你把自己圈得越小,敌人就越多。
历史学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权威的完满,而在于后浪一次次的改写与追问。

悼念许倬云先生
谢宝瑜
打开电脑,就见到许倬云先生于今天凌晨去世的消息,深感突然和悲痛。
许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史学界是咤叱风云的人物。我不是学历史的,本来无缘与许先生有什么交集。然而,2012年,我的好友臧小林告诉我,许先生读了我的小说《玫瑰坝》,很喜欢,愿意为拙作的第二版(电子版)作序。许先生是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愿意为拙作作序,我自然非常感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当然非常欢迎。不过,我当时也很好奇。历史与文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作为历史学家,许先生会为这本小说写些什么呢?
很快,我收到了许先生为拙作《玫瑰坝》而写的〈前言〉。许先生〈前言〉中说:“《玫瑰坝》这本书不是小说,在我看来,它是真实的、为了隐去而给主角们用了假名的实录。”
显然,许先生在读拙作的时候,不仅是在读小说,也是在读历史。把小说当成历史来读的人很多。据说某革命家就把小说《红楼梦》当成历史来读,甚至还从《红楼梦》中读到了阶级斗争。因此,我并不感到奇怪。从〈前言〉中可以看出,许先生不仅把拙作当成中国的历史来读,甚至还当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来读。他比较了英国清教徒革命与中国的革命,认为两者之间有共同之处。英国清教徒们曾经努力革除天主教的主教和神父们的败德和对一般平民的迫害,结果却造成了一个全无生机的社会,也是上面压迫下面的社会。中国也是这样。许先生说:“《玫瑰坝》中的人物抱着一番理想,进入这个山村,想要改变一切。由于他们自信站在‘理’的一边,扛着这个‘理’的组织就拥有绝对的权力。”许先生认为,英国的清教徒和中国的革命者都想建立一个伊甸园,一个人间的乐园,结果却都失去了这个乐园。“这是近代中国人切身经历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悲剧。”
显然,历史学家的眼光与普通的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有所不同。许先生总结出来的很多东西,我在写《玫瑰坝》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写的。然而,读了许先生写的〈前言〉后,我觉得他说的话极有道理。
2018年11月,我受到美国查塔姆大学(Chatham University)的Karen Kingsbury教授、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钱坤教授和张海惠馆长的邀请,去查塔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与两所大学的一些学生和我的一些读者见面,给他们作讲座,和他们一起讨论我在创作《玫瑰坝》过程中所用的素材、写作时的灵感、以及其它有关的问题。利用这个机会,我在11月16日去许倬云先生的府上拜访了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许先生,也是唯一的一次与他见面。
许先生和许师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相谈甚欢。我们谈话的题目非常廣泛,涉及到了许先生的身体,他的求学,他的学术活动,美国的政治,台湾的政治,等等。
在谈话中,许先生问我:“你在小说的最后写到陈素芬死去的时候流泪了吗?”我说,“我没有流泪,但是写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许先生说,“读到她死去的那一段时,我流泪了。”
我听到许先生这句话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我一向觉得,许先生是历史学家,见惯了历史上数不清的苦难和死亡,况且他当时已经八十八岁了,感情应该不再冲动,似乎不应该为一本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之死而流泪。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许许先生说的不是流泪,应该是别的什么。
与许先生和许师母道别,出了门,走了几步后,我问陪同我前去拜访许先生的臧小林好友:“许先生刚才说,读到小说中陈素芬死去的那一段时他流泪了。他说过这句话吗?”臧小林证实说许先生的确是说过这句话。
这件事让我对许先生更加尊敬了。可见,尽管许先生长年与冷冰冰的历史资料和数据打交道,却没有形成我的想象中的历史学家应该有的冷冰冰的铁石之心。他在八十八岁的高龄,仍然保持了丰富的感情,充满了人文关怀,悲天悯人,关心人间的疾苦,希望“……我们知道如何审查乐园的美好承诺,不再轻易上当”。
今天,许倬云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本来还希望找机会再次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很多与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关的问题。然而,这一切现在已经不可能了。许先生在史学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也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以及对这位大师的永久怀念。
许倬云先生千古
谢宝瑜
2025年8月4日,多伦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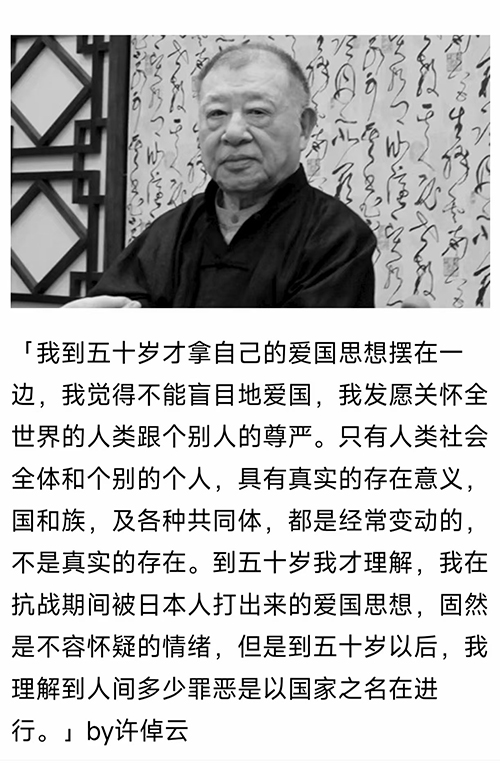
许倬云:《玫瑰坝》(电子版)前言
2012.9.14.
请见:
https://www.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65&extra=page%3D3
在时间切面上取火
——许倬云生平、史观与民族文化观评述
马四维,《中华艺术评论》2025年8月4日
二零二五年八月四日清晨,位于匹兹堡郊外的那幢灰砖小屋刚刚透出清新的晨光,许倬云在安静中合上了最后一本书——据照料他的学生回忆,那本书是他年轻时带去美国的《史记》,扉页仍夹着父亲当年为他写下的诗句。那一刻离他九十五岁生日仅余月余;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朋友圈与学术微信群瞬间刷屏,“大河入海”“替老百姓写史的人走了”成为当日最醒目的悼词。人们忽然意识到,这位终身以轮椅为舟、以书页为桨的史家,就这样从历史的前台悄然隐没,而他留下的,是横跨上古考古、宏观社会史与大众文化论述的浩瀚书海。倘若说中国二十世纪史学自梁启超以来如一条分流众多的江河,那么许倬云无疑是那道不急不缓、却格外坚韧的支流:他既在专业学术的深壑里纵横,也在大众阅读的浅滩上浸润民心,用他惯说的“做时间线上的切面”方法,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理解自身文化基因的立体透视图。
许倬云一九三零年生于厦门鼓浪屿,籍贯则在江南水韵丰沛的无锡。许家自乾嘉以来便是士大夫门第,家学渊源之深,使得他自小浸润在汉宋之学与近代西学并置的书房气息中。父亲许凤藻毕业于曾国藩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先是海军炮艇副长,后转文职,精通英语与古文。抗战爆发后,全家辗转川渝,父亲在防空洞外的油灯下朗诵《泷冈阡表》,对“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句句顿首,让尚不到十岁的倬云意识到“写史不仅是书斋功课,更关乎庶民安危”。那一幕——电线杆上挂着半具尸体、树干下散落一条血迹斑驳的大腿、无头女尸胸前婴儿仍在吮乳——成为他此后一生疏离“英雄史观”的心理原点,他后来在口述回忆录中坦言:“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小民添了痛苦,我对伟大人物已无敬意和幻想。”
战后回到无锡,他因天生足疾未曾走过正规义务教育,直接插班读高中。那份“错位”使他对制式教育保持距离,却也让他从父亲书房里习得古文、英文与史学的混合养分。一九四九年全家赴台,他本报考台湾大学外文系,但入学作文、国史试卷被批卷教师呈给时任校长傅斯年。傅氏的判语是“此子当为史料之眼”,随即力邀转系。今天看来,这个转折决定了华语世界未来半个世纪的一道独特史学光谱:倘若无此调剂,许氏或许只是一位文笔隽永的翻译家,而非后来那位在上古铜器铭文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搭桥的通才。
一九五七年,胡适四度致信募款,终为足疾未愈的许倬云争取到纽约侨领徐铭信捐出的一千五百美元奖学金,使他抵达芝加哥大学。芝大当时正是社会学“宏观取向”的策源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分析、韦伯的比较文明论与汤恩比的“挑战—回应”范式在此激烈碰撞。许在顾立雅门下主攻《春秋时代的社会变动》,却一头扎进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的课堂。他常说自己学习像“打卤面”:考古、甲骨、社会学与经济学扔进同一锅,以文化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四小系统”连成动态结构。正是这种“卤面式”的杂糅,让他的博士论文超出传统“礼制沿革”范畴,而朝向阶层流动、战争频率与区域贸易网络的多维分析。也因此,当他一九七零年移居匹兹堡大学、融入美国大学城特有的跨学科空气时,几乎没有“身份差”的痛苦——在钢城的河谷里,他照样能同时与考古学家讨论碳十四测年,同社会学家探讨宗教韧性,又与计算机系实验室借用运算资源测算古代人口估算模型。
真正奠定他专业史家地位的,是连贯出版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三部英文巨著:《Chinese History: New Perspectives》(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in Han China》(《汉代农业》)与《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A History of Western Zhou》(《西周史》)。若将中国文明比作一具活体,这三部书分别剖析其社会肌理、经济血流与政治骨架;许氏以“做时间线切面”的方式,将商周之际贵族—平民流动的“换血”、秦汉统一后市场取向农业的“脉动”、以及宗周—成周迁都所象征的“天下”观念成形,分别定格为三个“动态图层”。李济之先生曾赞叹,这种“系统—断面”双矩阵不仅突破了单线王朝史,也纠正了静态结构功能学派“动因缺失”的通病。今日年轻学者在写上古史时,不提“许氏模型”几乎无法开展田野与文本比对——哪怕是持反对意见,也得在他划定的坐标系里辩驳。
然而对普通读者来说,使许倬云真正“火出圈”的是九十年代末退休后的通俗写作。许自嘲:“专业论文是同行看的,我却更想对街坊叔伯有所交代。”《万古江河》正是在这种心态下问世:他不再以朝代为叙事单位,而是以青铜器带动的权力整合、水利网络塑造的农业区间、佛教与伊斯兰输入后形成的多层文化拼图等“巨系统”来叙述“中国”这条大河的发源与汇流。继而《说中国》追问:是什么力量让这条河里的百姓认同自己属于同一文化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更由内在价值观层面——礼乐之教的和谐理想、天下观的开放胸襟、士绅自治的责任伦理——解析何以“华夏”能屡遭破碎却再次凝聚。三书接连入选各类畅销榜,在自媒体时代被大量年轻读者引用为“摆脱碎片史观”的入门钥匙,也被部分批评者指为“文化本质主义的新名片”。许在公开演讲里回应:“我反文化优越论,但我也反文化虚无。”他认为,无论基督教共同体还是伊斯兰共同体,皆有其宗教排他性,而华夏传统历经多神信仰与实践主义冲刷,因而具备“海纳百川而不溶于自大”的潜能。正因如此,他对当下官方与民间急速升温的民族主义持警惕态度——“你把自己圈得越小,敌人就越多”,一句话在微博被转发数万次。
许倬云与胡适、黄仁宇的比较,经常成为史学讲座里的经典议题。胡适秉承清代小学传统,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重在微观考据;黄仁宇则受汤恩比“文明互释”影响,以《万历十五年》为标本,提出“大历史观”。许倬云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一次访谈中打了个比方:“胡适是微距镜头,对一枚甲骨文拍特写;黄仁宇是广角镜头,站在延禧宫屋顶俯瞰紫禁城;我想尝试移轴镜头,既保持边缘清晰,也让焦距平面倾斜,看看局部如何嵌进整体。”这种移轴手段在他后期写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可以在同一段文字里提及周公制礼作乐与今日欧盟共同体治理框架,以系统论把两者连接,并以平民生活的“日常成本”衡量历史转型的成败。
许氏一生最大争议也由此而生:大众读者赞赏他的宏阔通透,部分专业学者却质疑其“考据密度”不足,甚至嘲讽他“宏大叙事的段子手”。在他与李敖的笔战中,李敖讥其“拿学术大帽子吓唬人”,许淡淡回“我写史只是给百姓一个参照系,若有人非要把帽子当兵器,那便随他去吧”。批评未能撼动读者缘,一位高校教师统计,二〇一五至二〇二五的十年间,大陆高校本科“通识类史学阅读清单”中,《万古江河》的出镜率仅次于钱穆《国史大纲》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更有意思的是,不少曾狂热追捧民族主义叙事的青年,在阅读许的文本后转而开始讨论“天下主义”“多元文明对话”。
如果要概括许倬云的核心学术理念,或可归纳为四点:其一,历史是一系列动态系统的交互,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其二,小民的生计与情感是衡量制度优劣的底线尺度;其三,跨学科对话不是添味佐料,而是重塑问题本身;其四,文化认同应以开放与自我反省为双轮,既拒绝虚无,也抗拒优越论。这四点贯穿他上古史专著与当代评论之间,看似跨度甚大,实则同源于“做时间切面”与“替老百姓写史”的双重自觉。
回溯许倬云的人生轨迹,很难忽视几个时刻的历史暗合:他在抗战流离中悟得“平民视角”;在冷战高峰时移居美国,却用中文向世界阐释中国文化;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他提醒国人“天下主义”的初衷。有人说他像摆渡者,用通俗文字把传统史识渡到数字时代的青年心里;也有人说他自己便是一滴浪花,始终向前,不肯沉静。二〇二五年送别仪式上,他生前学生为他朗读了自选墓志铭:“江河入海,寸心不泯。”这句话源自《礼记·中庸》,却更像他对后学的叮咛:去河床挖掘变化的纹理,也别忘了河水最终奔向众流汇聚之处。
如今,他的讲义、书信、手稿正在台北与匹兹堡两地数字化,年轻的数字人文团队尝试用网络分析工具重建《汉代农业》里的农耕—手工业—交通路线交互模型;考古专业的学生则在《西周史》注疏中标注最新田野发现,试图检验他关于“姬姜婚姻网络”理论的预测误差。当新的切片被切下,或许旧有断面会显露瑕疵,但那恰恰是许倬云愿意看到的:他始终相信,历史学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权威的完满,而在于后浪一次次的改写与追问。而对所有仍在书桌前奋笔的读者来说,许倬云留下的,也许不仅是一套解释中国的宏大框架,更是一种不疾不徐却永远在路上的精神姿态——正如他年轻时书房窗前挂着的自题联:“以工作雕塑自己,以历史安顿众生。”
近期文章:
《1984》又被禁了!这次是在美国
释永信寓言:天下武术皆出少林,少林荣辱皆出朝廷
互联网悖论:“时时刻刻都可参与”“时时刻刻被拒绝参与”
爱泼斯坦档案会让川普陷入最大的信任危机吗?
偏执狂人士受双重折磨:受现实世界折磨,还受自己幻想折磨
自由、责任与幻想:索维尔看马斯克“美国党”的命运
这还是美国?这就是美国——这不是美国!
法案确实够大,是“大而美”,还是“大而丑”?
妖魔化中国公民形同自我蒙蔽,只会伤害美国自身
川普不能容忍监督白宫的“第四权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