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算法”,从根本上重塑了言论自由的本质:不一定是通过限制可以说什么,而是通过决定谁可以看到什么。算法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不是让思想自由竞争,而是干扰了思想的自由交流,放大或者抑制了信息的传播范围
老高按:作为多年媒体人,又正逢媒体形式多次巨变的历史阶段,自然一直非常关注、长期思考媒体遇到的新课题、新挑战——这也就是言论自由遇到的新课题、新挑战。在美国大选期间,媒体的作用格外重要,受到的抨击也格外激烈,甚至,我听到的消息说,长期不受媒体待见的川普,正在调兵布阵,将在跨进白宫之后,铁腕重拳整治媒体,已经弄得一些媒体神经紧张,惴惴不安。
据我掌握的不完整资料,仅在今年竞选期间,川普多次在演讲中威胁要吊销CBS、NBC、ABC和Fox等新闻频道的广播执照。据行业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一项分析统计,特朗普在9月1日至10月24日期间至少108次在演讲中口头“攻击或威胁媒体”,这还不包括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动作。
我列出了几十条与媒体有关的课题,正在逐一学习、调研,以求弄个明白。诸如: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异同——二者如何找到自己生存的合适空间;
新兴媒体的优势和缺陷,如何看待和化解新兴媒体在信息市场上的极大副作用;
媒体不仅要处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现在又加上了如何处理与有极大影响力、甚至在信息市场上可达垄断程度的个人企业和资本的关系;
媒体“理中客”的真谛及受到的冲击;
媒体市场形成和发育的过程及其规律;
等等。
许多内容,美国立法制宪先贤不可能预见到,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体会、总结和规范。昨天我读到一篇BBC一个月前发表的深度报道《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很有收获。其中有两个观点让我脑洞大开——
一个是:人们期望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平等地听到,但数年来的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做到。我本以为这可以改进、改善,但不少学者指出:“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从一开始就不允许思想自由和公平地竞争。”
另一个是:“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说话的权利,还是也指被倾听的权利?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阿尔温德·纳拉亚南所说:“当我们在网上说话时……谁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法。”
看来,高科技对言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复杂,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转载BBC这篇报道,与大家分享。
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我们交流的方式?
尼古拉斯·巴拉特(Nicholas Barrett),BBC,2024年10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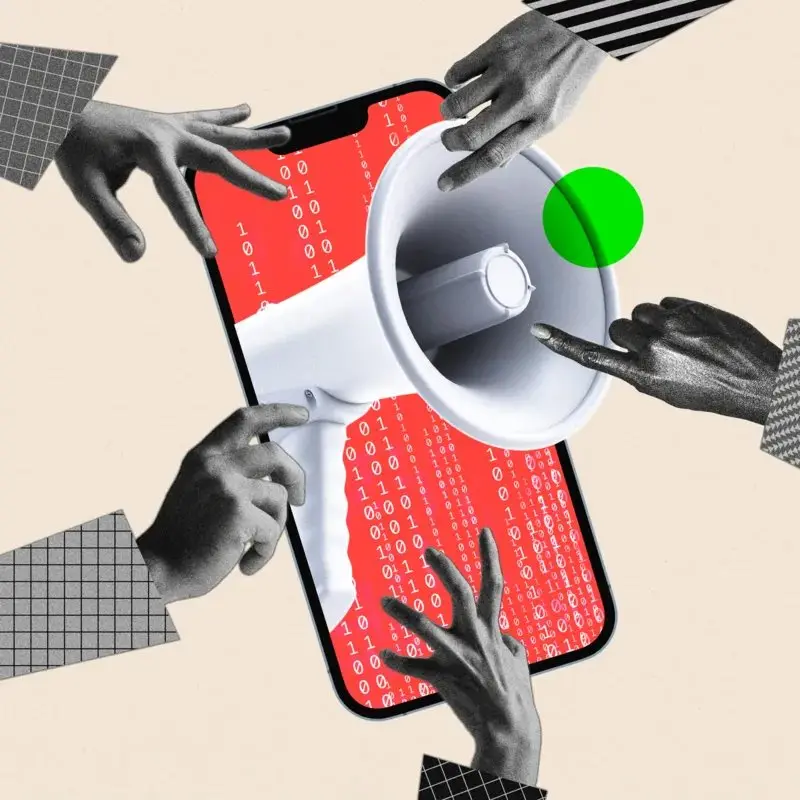
算法如何影响和塑造我们的言论?
人们所熟知的社交媒体算法已经存在15年了。
2009年,随着脸书(Facebook)推出排名式个性化新闻推送,算法应运而生,并改变了我们在线互动的方式。
和许多青少年一样,算法对希望控制他们过度行为的成年人也构成了挑战。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此无所事事。仅今年一年,世界各国政府就试图限制有害内容和虚假信息对社交媒体的影响,而这些内容的影响都被算法放大了。
在巴西,当局近期曾短暂禁用原名Twitter的X,直到该网站同意在该国任命一名法定代表人并屏蔽一份黑名单上的账户,当局指控这些账户质疑该国上次选举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欧盟出台了新规则,威胁称,如果科技公司不能防止平台干预选举,就要对它们处以营业额6%的罚款,并暂停其服务。
在英国,一项新的网络安全法案旨在迫使社交媒体网站加强内容审核。
在美国,一项拟议的法律正要出炉,该国表示,如果中国母公司不抛售TikTok,美国用户将失去这个软件。
各国政府面临限制言论自由和干涉互联网早期制定的原则的批评。
美国诗人兼牧场主约翰·佩里·巴洛 (John Perry Barlow) 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辩称:“工业世界的政府,你们是令人厌倦的血肉和钢铁巨人,我来自网络空间,这是思想的新家园。代表未来,我请求你们这些过去的人们不要打扰我们。你们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亚当·坎德布 (Adam Candeub) 是一名法学教授,曾担任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他自称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
他告诉BBC,社交媒体“两极分化、争执不休、粗鲁无礼、毫无升华,由此,我认为这是进行公共讨论的糟糕方式。但同时,起码在我看来,很多政府都在推动将其作为社会和政治控制的工具,这更糟。”
坎德布教授认为,除非内容“当下存在明显的危险”,否则“最好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思想集市,对不同观点持开放态度。”
数字城镇广场的局限性
“思想集市”这一理念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人的声音都能被平等地听到。2022 年,埃隆·马斯克接管X时表示,他将该平台视为一个“数字城镇广场”。

马斯克接手X时认为这个平台是一个数字城镇市场。
但这是否没有考虑到算法的作用?
美国律师兼耶鲁大学全球事务讲师阿莎·兰加帕 (Asha Rangappa) 表示,马斯克“忽略了传统城镇广场和在线城镇广场之间的一些重要区别:在不考虑这些差异的情况下取消所有内容限制将损害民主辩论,而不是帮助它。”
兰加帕认为:“思想集市”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初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件中提出的,“其前提是思想应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相互竞争”。她还补充说明“问题在于,像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与真正的公共广场完全不同。”
她认为,“社交媒体平台的功能从一开始就不允许思想自由和公平地竞争……社交媒体上思想的‘价值’并不反映它有多好,而是平台算法的产物。”
算法的演变
算法可以观察我们的行为,并决定数百万人登录时看到的内容——对于某些人来说,正是算法破坏了互联网最初创建时可能存在的思想自由交流。
“在早期,社交媒体确实发挥着一种数字公共领域的作用,言论自由流动,”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凯·里默(Kai Riemer)和桑德拉·彼得(Sandra Peter)告诉 BBC。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算法从根本上重塑了言论自由的本质,不一定是通过限制可以说的内容,而是通过决定谁可以看到什么内容”,里默和彼得教授这样认为。他们的研究探讨了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社交媒体上的言论自由。
“算法不是让思想自由竞争,而是放大或抑制信息的传播范围……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干扰了思想的自由交流,而这种形式往往被忽视。”
脸书是社交媒体推荐算法的先驱之一。作为一个坐拥30亿用户的巨大平台,它的首页推荐功能可以说是代表作之一。
15年前,当该平台推出基于用户数据的排名算法时,人们看到的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帖子,而是脸书希望他们看到的内容。
脸书平台还根据每条内容的讨论情况、优先显示有争议的话题的帖子,因为这些帖子获得了最多的参与度。

社交媒体奖励更有争议性的言论。图像来源,Oscar Wong
塑造我们的言论
由于有争议的帖子更有可能得到算法的奖励,因此出位的政治观点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被过度放大。批评者认为,社交媒体不是自由开放的公共论坛,而是提供一面扭曲和耸人听闻的公众情绪镜像,夸大了分歧,压制了大多数人的观点。
因此,虽然社交媒体平台指责政府威胁言论自由,但他们自己的算法是否也可能无意中构成同样威胁?
“推荐引擎不会屏蔽内容——相反,社区准则会根据平台的偏好限制言论自由,”TikTok前公共政策副总裁西奥·伯特伦(Theo Bertram)告诉BBC。
“推荐引擎对我们看到的内容有很大影响吗? 绝对是的。但你在注意力经济中成功还是失败,与你是否拥有言论自由是两回事。”
然而,“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说话的权利,还是也指被倾听的权利?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阿尔温德·纳拉亚南(Arvind Narayanan)所说:“当我们在网上说话时——当我们分享想法、写文章、发布照片或视频时——谁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算法。”
通过确定每篇发布内容的受众,平台“切断了演讲者和受众之间的直接关系”,里默和彼得教授认为,“言论不再取决于演讲者和受众组织,而是由算法决定。”
他们声称,这一点并未被纳入当前关于言论自由的辩论中,因为目前辩论的焦点是“发声的一方”。他们认为,算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扰了言论自由”。
算法社会
我们的时代被称为“算法社会”。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中,社交媒体平台和搜索引擎与国家管理言论的方式相同。
这意味着,根据耶鲁大学的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的说法,美国宪法中对言论自由的直接保障仅限如此:“通常理解的第一修正案不足以保护的言论实践”。
里默和彼得教授同意法律需要迎头赶上。 “平台在塑造言论方面发挥的作用比法律目前承认的要积极得多。”
他们声称,监控有害帖子的方式也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扩展对言论自由监管的看法。当前围绕内容审核的辩论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平台的商业模式如何激励它们通过算法塑造言论。”
虽然坎德布教授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但他也对平台集权持谨慎态度,这些权力可以通过计算机代码成为言论的守门人。“我认为我们最好将这些算法公开,否则我们就只是被操纵了。”
然而,算法不会消失。正如伯特伦所说,“城镇广场和社交媒体的区别在于,社交媒体上有几十亿人。人们有权在网上享有言论自由,但每个人却没有权利平等地被倾听:我们不可能看每一个TikTok视频或阅读每一条推文。”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对算法进行适度调整能否培养出更具包容性的对话,更接近我们面对面的对话?
像蓝天(Bluesky)这样的新微博平台正试图让用户控制显示内容的算法,并恢复旧有的时间顺序显示逻辑,它们相信这种时间顺序可以提供更少中介的体验。
脸书的吹哨人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在2021年向参议院作证时说:“我强烈支持按时间顺序排序……因为我们不希望计算机决定我们关注什么,我们应该拥有人性化的软件,或者人类一起对话,而不是计算机来决定我们听到谁的声音。”
然而,正如纳拉亚南教授指出的那样,“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信息并不中立:它们还受到富人越来越富效应、人口偏见和病毒式传播不可预测性的影响。不幸的是,没有中立的方式来设计社交媒体。”
平台确实提供了一些算法的替代方案,X上的用户只能从他们关注的人中选择提要。通过过滤大量内容,“推荐引擎提供了比仅仅关注我们已经认识的人更大的多样性和发现”,伯特伦认为。“这感觉就像是言论自由限制的反面——它是一种发现机制。”
第三种方式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说法,“无论是平台自我监管,还是未来的国家监管形式”都无法解决“网络言论自由问题”。相反,他提出了第三种方式。
“中间件”可以让社交媒体用户更好地控制他们看到的内容,独立服务商提供一种与平台内置内容不同的内容展示形式。福山写道,“一个由中间件提供商组成的竞争生态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个人偏好过滤平台内容,而不是根据平台的内部算法提供内容。”
“中间件将把选择自由交回到个人用户手中,他们的代理权将使互联网恢复到1990年代所渴望的那种多元化、多平台系统。”
在没有中间件的情况下,我们目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提高与算法交互时的代理意识。“普通TikTok用户通常对算法非常在意——在发现新事物的过程中向算法发出鼓励或阻止推荐引擎的信号,”伯特伦说。
“他们认为自己是算法的主人。我认为这是以这种方式思考挑战是有益方的——不是我们是否需要关闭算法,而是我们如何确保用户拥有被代理权、控制权和选择权,以便算法为他们服务。”
当然,即使我们自己制定算法,也存在着危险,我们仍然可能落入社交媒体的回音室。算法可能不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BBC的一项调查发现,当一名年轻男子试图使用Instagram和TikTok上的工具说他对暴力或厌恶女性的内容不感兴趣时,他的首页推荐流里依然会出现相关内容。
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随着社交媒体算法走向成熟,它们的未来可能不掌握在大型科技公司或政客手中,而是掌握在人民手中。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最近的一项调查,只有2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喜欢在网上公开记录自己的生活,低于2020年的40%。人们反而更喜欢与值得信赖的朋友和亲戚进行封闭的群聊。这种空间更强调对言论负责,对耸人听闻和挑衅的奖励更少。
Meta公司表示,现在直接消息中发送的照片数量超过了分享给所有人看的照片数量。
正如巴洛在1996年的文章中告诉政府“网络空间不欢迎他们”一样,一些网络用户可能也对社交媒体算法抱有类似的期望。目前,对于如何应对互联网上任性青少年,仍然存在着极有争议的讨论。
近期文章:
俄乌那片地方确实麻烦,川普是不是一把能斩乱麻的快刀?
多数美国人愿意再给川普一次机会,“是在拿未来赌博”
投票截止日:说一说与大选看似无关、其实有关的历史数据
大选倒计时最后一天:假信息意在引发美国公众的信任危机
大选倒计时第二天:美国梦还是美国噩梦的抉择前夕
大选倒计时第三天:美国近一半选民眼中的二号公敌
大选倒计时第四天:有点同情特朗普的“跟班”万斯
大选倒计时第五天:一位华人计票员苦思如何对选票动手脚
大选倒计时第六天:谁当选总统能拯救美国的保守主义
大选倒计时第七天:全球第三波威权化回潮中的美国大选
大选倒计时第八天:川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
大选倒计时第九天:“零元购”事件的来龙去脉
大选倒计时第十天:转载一位老作家的投票实录和感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