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這部回憶錄教會我們如何在不同時間節點上做出與學術相容、與人格相符的選擇,在面對政治巨浪時,把“判斷”與“研究”擺在各自位置,把“尊嚴”從抽象詞彙變成日常功課。一位政治歷史學者的價值,在於他用一生把一套可操作的秩序留在了我們手中
在大時代的列車與岔道上——評《余英時回憶錄》
馬四維,中華書法評論,2025年10月5日
讀《余英時回憶錄》會強烈感到這不是一本單純的憶舊之書,而是一部“以記憶復位學術”的時代見證。書中自述與旁證交錯,既有作者口述的親歷,也有編輯者廖志峰在《開往普林斯頓的慢車》中記錄的沿途細節:2018年在普林斯頓的長談、書房的留影、扉頁上的“河西走廊口占”、以及多次“正在尋找老照片”的電話迴響。這些碎片把一個“知識人”(余英時自稱常用的詞)最在意的事——學術與人格——安放在三段關鍵的時間坐標上:1949前後、1969前後、1989前後。若不在這三處節點上把敘述擰緊,我們就讀不懂這本回憶錄的歷史密度,也讀不懂余英時作為一位“政治歷史學者”的獨特形態:他既在政治的暴風圈外保存了學術自由的火種,又在歷史的長期線上檢驗政治抉擇的後果。
《回憶錄》裡最令人難忘的篇章之一,是他從內地輾轉至香港,在新亞書院遇到錢穆、唐君毅諸師的那一段。對一個年僅十幾歲的青年而言,這既是“離散”的起點,也是“入學”的起點;離散讓他與故土的制度現實拉開距離,入學讓他在傳統學術的“近身教養”里紮根。錢穆教他的,並非單一道統,而是一整套“為學即為人”的實踐品格:治學要有根柢,做人要有定力,立場可以鮮明,情緒必須節制。余英時後來屢屢回憶,這一段“在風雨之夜仍有燈可依”的生活經驗,使他相信中國學術的現代繼承並不靠口號,而靠具體的制度與人格:一間書院、一位老師、一張書桌、一套讀書方法。這些在1949年的去留之間被重建起來的“最小單元”,在余英時此後的學術與公共發言中反覆顯影。

也正是在這條去路上,許多人提出一個尖銳的反問:倘若沒有1949的出走,余英時會不會像陳寅恪那樣“倒在1969”?這不是一句修辭,而是一個必須嚴肅對待的歷史設問。《回憶錄》雖然不做“平行世界”的推演,但材料提供了判斷的底板。1960年代末的中國,知識界處境之艱,史不必再贅;陳寅恪以近乎全盲之軀完成《柳如是別傳》,1969年病逝廣州,成為那個時代知識人精神史的一個終點。若余英時留在大陸,他是否也會在高壓體制中失聲、受挫、甚至中斷學術?從他在書中處處強調的“學術即人格”的立場看,他決不會以口號換平安、以沉默換通行;這恰恰意味着,他很可能付出與陳寅恪相當、甚至更為慘烈的代價。換言之,1949的出走,既是歷史給他的現實安排,也是他主動的價值選擇:把自己安放在一個能繼續“學術生活”的制度空間中。只有在那樣的空間裡,才有可能醞釀他後來整個學術體系的生成——從晚明思想史到現代新儒家,從“士與中國文化”到“歷史與思想”,從經世之學到心性之學的再對話。
時間跳到1969前後,《回憶錄》在寫到赴美求學、在哈佛受教及早年的任教經歷時,語氣並不喧譁,卻處處可見一條內在的弦:學術的進路不是“題目疊加”,而是“問題深化”。他受教於楊聯陞等師,留意的並非某一派的“正統”,而是史料的縝密與問題的歷史生成。他反覆提出“由思想入史、由制度觀人”的互證方法,將思想史從“抽象觀念史”拉回到“士人群體的社會史”。也正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逐步把近代中國知識與政治的“糾纏敘事”建立為一個可研究的對象:晚明黨社運動如何重塑士大夫的公共倫理,清季新政如何催生現代學術共同體,五四以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三角張力如何塑造20世紀的知識人自我。站在1969年,美國也在巨變:冷戰、越戰、校園運動與新左派席捲學界。余英時並未被“風潮”吸走;《回憶錄》中可見他清楚地劃定邊界:政治可以構成研究對象、可以構成道德判斷的場域,但不可以吞併學術本身。正因如此,他在美國學界建立的是一種“兼容而不混淆”的範式——既能用現代學術的工具進入中國史的深處,又不把現代理論當作唯一的裁判官;既能與英語世界對話,又不在中國史實與漢語文本面前丟失細節。這種範式在1969年前後定型,它不是“避世”,而是為學術爭取到“在政治之外說真話”的工作間。
把時間推至1989前後,這一段在《回憶錄》與後來諸多談話錄、演講集中都有清楚記述。1989年的政治巨震,讓“知識人”與“公民”的角色驟然重疊,也讓“學術共同體”的倫理經受拷問。余英時沒有迴避,他明確站在“人的尊嚴—學術的自由—政治權力的邊界”這一條線上發表判斷:國家可以談秩序,但不能以暴力摧毀言說;大學可以談中立,但不能以沉默耗盡良知;歷史學家可以談複雜,但在生命面前必須先做出基本的是非判斷。若把這與他1949年的去留、1969年對學術邊界的維護接連起來看,1989年不是“臨時表態”,而是他長期學術—人格坐標的自然延伸。也因此,《回憶錄》並未將1989年收束為“個人情感史”的一章,而是當作“知識人共同記憶”的節點來處理:那一年以後,他關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自由主義價值、公共倫理與大學制度的思考全面展開;這不是“轉向”,而是“顯形”。
這三處節點共同構成了一條清晰的時間鏈:1949年,選擇可言說的制度空間;1969年,建設學術與政治的防火牆;1989年,在大的是非面前確認知識人的公共角色。沿着這條鏈去讀《回憶錄》,我們也可以回答前述的假設題:若沒有1949的離開,他會不會“倒在1969”?答案或許並非“必然”,卻非常“可能”。從他人格的硬度、學術的自持與在關鍵時刻的表態來看,他不可能在一個系統性壓抑學術與言說的環境中“安靜地偉大”;他會抗拒,會發聲,會承受代價。陳寅恪以“忍而不隱”的方式挺過了他的最後十年,終以“文史合一”的巨構完成自我;余英時則藉助地緣與制度的選擇,完成了另一種“忍而不隱”——以持續四十年的學術生產、以跨語言的大學講席、以“知識人”的公共寫作,累積成一種更廣闊的影響。兩條路徑殊途同歸,都是在“不得不忍”的時代裡為學術保存了尊嚴,只是代價不同、形式不同、影響範圍也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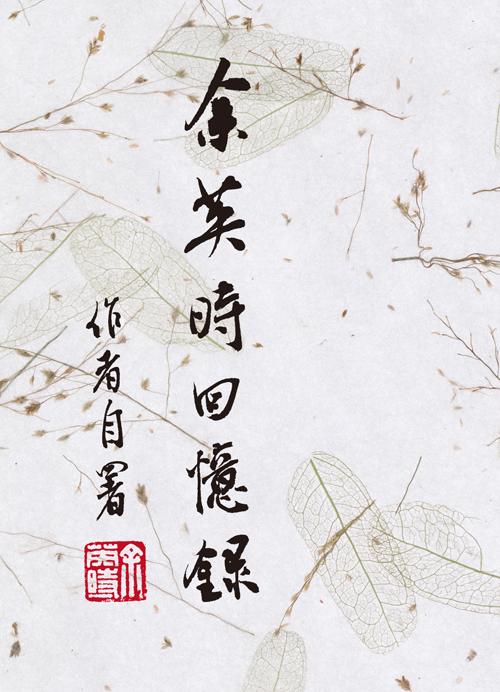
《回憶錄》的可貴,還在於它並不把自己寫成“命運劇”,而是細緻地展示生活如何與學術互相嵌扣。書中多次提及錢穆,提及新亞書院,提及書院之學與現代大學之間的張力與互補。讀這些段落,很容易看出他與老師在政治大是大非面前“立場鮮明、選擇正確”的一脈相承:錢穆以建制中的“獨立空間”抵禦意識形態化的大學,余英時以美式大學的制度彈性守住學術的底線;兩代人都不把“傳統”當作口號,而把它當作一種“可傳遞的生活方式”:以學術為職業、以道德為邊界、以公共言說為擔當。余英時曾自稱“尊嚴的知識人”,這不是榮耀的勛銜,而是一份自我約束:不把學術降格為政治修辭,也不把政治抬舉為學術真理;在必要時為基本價值發聲,在平常處回到文獻、回到課堂、回到史學的基本功。
從文本形式看,《回憶錄》與廖志峰的編輯手記互為補章。後者的“慢車”敘述,給讀者提供了進入作者私人生活的路徑:書房的門“極少讓人進入”、扉頁那首1978年深秋的《河西走廊口占》、在普林斯頓後院成林的竹子、一次次“怕你找不到我”的電話;這些細節都不是獵奇,而是在提醒讀者:一個學者的歷史感不是抽象出來的,它在他的生活習慣、時間管理、語言風格中長期淬鍊。《回憶錄》因此具備兩層時間:敘述的時間與編輯的時間。前者是作者從記憶取材的線性流動,後者是編輯在現實中奔走、在“馬拉松”的耐心裡把散落的碎片縫合起來的過程。二者交疊,使這本書不止是“我的一生”,更像是一種“如何將一生化為學術”的實踐記錄。
評一本回憶錄,不能只談“其人其事”,還要問它為我們的理解增加了什麼。對現代中國思想史而言,《回憶錄》至少提供了三條有用的線索。第一條,是“士與制度”的雙向觀察。余英時在書中反覆談到“士”的精神傳統,但他從不神化“士”;他強調,士人倫理之所以能在帝制時代維持張力,是因為有一定的社會與制度空間(科舉—書院—文會—家族)作為支撐;當這些支撐被破壞,士的倫理也會變形。這套思路在他對近現代知識分子的考察中延伸為“大學—出版—媒體—公共輿論”的現代支撐網絡。《回憶錄》讓我們看到,作者不是在“學術外”才想到這些,而是在自己的生活史中實踐出來:他之所以能持續寫作、能在1989年後發聲,恰恰因為他擁有一套可運轉的制度支持系統。第二條,是“史與心”的互證方法。余英時強調“思想史必須落在史料學上”,但他也從未放棄對“心性—價值”的追問;《回憶錄》中的自我追述並不迴避立場,反而在立場之內不斷用史料作校準,這種寫法本身就是思想史寫作的範式示範。第三條,是“知識人與公眾”的邊界重劃。書裡對1989年的處理表明:知識人介入公共議題,不必把自己變成“政論家”,但必須在關鍵處給出基於學術與良知的判斷;這種判斷的公開化,不是為了製造“敵我”,而是為了守住話語共同體的最低線。
筆者認為,余英時無論作為一個學者還是知識人,都超越了時間、超越了空間、跨越了他的時代,人格、學術,俱成不朽。“超越”不是誇讚的形容詞,在他這裡有具體的指向。所謂“超越時間”,並非無視時間的變化,而是在不同時間點上保持一種可被識別的價值坐標;“超越空間”,並非脫離具體國族,而是在不同制度空間裡保持學術的可遷移性與可溝通性;“跨越時代”,並非拒絕時代,而是在時代轉折處提供歷史的深度與道德的方向。《回憶錄》證明,他確實做到了:1949年的去留不是逃離,而是為學術另闢空間;1969年的堅守不是退隱,而是為學術建立邊界;1989年的表態不是衝動,而是對長期坐標的兌現。將這些放回他與錢穆的師承關係裡看,“立場鮮明、選擇正確”不等於簡單的“站隊”,而是一種複雜的歷史理性——知道何時應當說“不”,也知道怎樣把“不”說得有分寸、有根據,能經得起時間的審核。
當然,《回憶錄》也有其“留白”。它並不試圖在一己經歷中囊括所有爭議問題,有些敏感處點到為止,有些學術恩怨不作展開。這既是回憶錄體裁的自我邊界,也是作者一貫的行文審美:把重點留給“問題”而非“八卦”。讀者若想在人物關係與學術糾紛上“看熱鬧”,可能會感到意猶未盡;但如果把這本書當作進入余英時學術世界的“索引”,再去讀《歷史與思想》《士與中國文化》《現代儒家思想的興起》等論文集,去讀他對錢穆、胡適、殷海光、唐君毅、牟宗三的系統討論,乃至重讀他早年關於晚明黨社與清初思想的研究,就會發現這本回憶錄已經提供了必要的脈絡與鑰匙。
我尤其喜歡書裡關於“尊嚴的知識人”的幾段自述。余英時並不把“尊嚴”理解為離群索居的高蹈,而是理解為“說清楚自己所知、所信與所不為”的能力。尊嚴不是姿態,而是方法:在史料上精確,在概念上克制,在判斷上負責任。把這三點揉進來,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他同時被視作“政治歷史學者”與“思想史大師”。“政治歷史學者”幾個字,若放在一般語境裡,容易被理解為“立場先行”;而余英時的做法恰好相反:先把歷史問題的層次理清,再給出政治倫理上的判斷;判斷不是為了結案,而是為了讓討論在更高的明晰度上繼續。這種秩序感,是他給這個時代的罕見饋贈。
最後,把視線回到廖志峰在後記中記錄的那些微小瞬間:普林斯頓後院從一株到成林的竹子,書房那張少有人能得的照片,扉頁那首“昨髮長安驛”的口占詩,以及那句“許多事一言而決”。這些片段之所以動人,不僅因為它們滿足了讀者的“在場”想象,更因為它們與《回憶錄》的核心主題相合:學術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也因此而被賦形。我們在書裡見到的並非一位“超凡脫俗”的賢者,而是一位“在歷史裡過日子”的學者:他也會為一則書名斟酌,他也會為一次訪談改題,他也會因電話線被颶風颳斷而失聯,但他總能夠在下一次書寫中,把生活的雜音轉化為學術的清音。
《余英時回憶錄》不僅可讀,而且可學。它教會我們如何在不同時間節點上做出與學術相容、與人格相符的選擇;教會我們在面對政治巨浪時,怎樣把“判斷”與“研究”擺在各自的位置上;也教會我們把“尊嚴”從抽象詞彙變成日常功課。如果說書名之外還需要一個副標題,我願意加上八個字:在風雨中安放學術。對今天的中文世界而言,這八個字並不輕鬆,卻格外必要。讀完此書,我們不只是在回望一位大師的來路,更像是在確認一條仍可行走的路徑:在1949、1969、1989的節點之外,仍有2029、2039……歷史在延長,問題在更替,而一位“政治歷史學者”的價值,恰在於他已經用一生把一套可操作的秩序留在了我們手中。
近期文章:
既是一份告別信,也是一份懺悔錄,還是一份控訴書
請用文明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也談最近一份泄露文件
跟着依娃走陝西——讀依娃小說集斷想八則
譯者眼中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作家,戴上了諾貝爾文學獎桂冠
想起電視劇里說的:“你爺爺一失誤,我爺爺就要飯”
川普起訴媒體、天價索賠,算不算打壓新聞自由?
狂熱分子,極左和極右本是同一種人
這一場白宮晚宴可能影響美國未來,值得詳加解讀
介紹孫立平兩篇短文:瘮人危機前景下的“哄你玩”
訂正一個民間失實之辭也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