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麻风病的理解和对麻风病人的宽容,迟迟没有体现在政府的规章和法律制度中。直到进入21世纪,修订《民法》才解除对麻风病人包括结婚在内的公民权利的禁令。官方资料强调了麻风控制的成功,但对于麻风病人而言,歧视和隔离的历史充满血泪
应隔离的迟迟不隔离,不该隔离的却被久久隔离
《伐林追问》第60期,2020年2月14日首播
◆高伐林
鼠年开年半个多月来,“隔离”大概算海内外中国人说得最多的词。
在人类抗疫历史上,人们干过应隔离却迟迟不隔离的蠢事,也干过不该隔离却长久隔离的蠢事。
后者,我指的是麻风。
20天前,(2020年)元月26日,中国鼠年大年初二,新冠病毒肺炎闹得最人心惶惶的高潮,没有人记得这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防治麻风病日”。1953年由法国一位律师发起,经由世界卫生组织确立,每年1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为“世界防治麻风病日”。各国都在这一天举行活动,目的是调动社会力量来帮助麻风病人克服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维护他们的权利。中国也决定,从1988年起“国际麻风日”作为“中国麻风日”。(今年,2023年,“世界防治麻风病日”是元月29日。我看到不少中国官方报道:疾控中心和江苏、长沙等不少地方都做了安排,要开展相关活动,让我感到意外的高兴!——老高注)

基督徒义工小宝与麻风康复老人合影。她说:我们一家在麻风村八年了。
传染病有急性和慢性之分,鼠疫霍乱天花肺炎这些都是急性传染病,麻风、梅毒和结核被通称为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麻风是由麻风杆菌引起,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很广,主要伤害皮肤、粘膜和周围神经,也能侵害深层组织和器官。麻风感染初期并不会出现症状,潜伏期可达5至20年。会在神经系统、呼吸道、皮肤与眼部出现肉芽肿,发作的部位失去痛觉感知的能力,常造成四肢反复损伤而需部分截肢,人越来越虚弱、视力变差。
得了麻风不致于死,但它会导致患者机体残疾和面部损害。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患者的畸型残疾会越来越加重。对于许多病人来说,身体的痛苦加上社会的排斥歧视,这比死更可怕更难受。

西方绘画中的麻风病人。
麻风的传染源是麻风病人,传播方式有两种,密切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世界公认的主要方式,是麻风患者的皮肤或粘膜,与健康人的有破损的皮肤或粘膜长期接触所致,但95%以上的人对麻风杆菌有抵抗力,所以感染麻风杆菌的比例其实并不高。
麻风不是遗传病,但如果父母是麻风病人,孩子可能会有易感基因,发病的几率相对较高。
麻风病经治疗后可以痊愈,世界卫生组织免费提供治疗药物,抗生素能治麻风病。据统计,1980年代全球有五百多万麻风病人,三十多年来这个数字已极大下降,但还有新病例,发生在16个国家的缺医少药地区。
公元前1000年古埃及发现第一例麻风病,公元前600年的印度宗教典籍中出现关于麻风病的记载,在中国也有2000多年的流行史,最早被称为疠病,宋朝称“麻风”,就这么固定下来了。因为麻风病患者形象骇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秦律》规定:“疠者有罪,定杀。或曰生埋。”那时就设立了收容疠病的“疠迁所”。历朝历代也都有类似设施。宋朝设立“安济坊”,由官府管理并提供经费,逐渐形成常态化的隔离防控机制。十二世纪初,被列为“北宋六贼”之首的奸臣蔡京主持朝政,做了一件好事,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官府和社会救助体系,落实人力财力,穷人得到了实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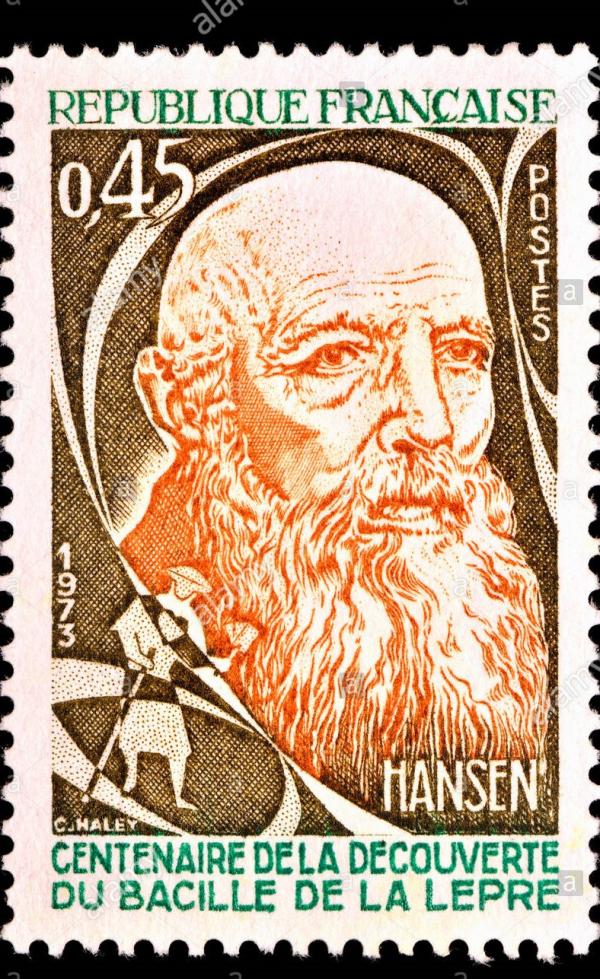
挪威医师格哈德·阿玛尔·韩森因发现麻风杆菌的功绩而上了纪念邮票。
1873年,挪威医师格哈德·阿玛尔·韩森在显微镜下发现了麻风杆菌,在医学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人类终于了解麻风病是一种传染病。才找准了防治思路。
孔子弟子冉伯牛可能患有麻风病,孔子曾赴冉伯牛家探望,冉伯牛可能因病不让他进门,孔子只能站在窗外握着他的手。公元七世纪文坛上有“初唐四杰”: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列的诗人卢照邻,词采富艳,境界开阔,他的代表作《长安古意》68行,在中国古诗中算是少见的长诗,其中“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被称为千古名句。卢照邻人到中年染上麻风,辞了官职去长安养病,曾向有药王之誉的孙思邈讨治疗药方,孙思邈是当时治疗麻风病的专家,但卢照邻患病十年左右,无法忍受痛苦,投河自杀。

“初唐四杰”之一、诗人卢照邻因久患麻风病而自杀。
麻风不必隔离却被长久隔离。《凤凰周刊》曾经发表曾鼎的文章《斑斑血泪的麻风病隔离史》说得比较详细。因为麻风病人面目残缺、肢体残疾,人们望而生畏。但现代医学可以使两周内连续服药的麻风病人失去传染性,并在一年内康复。曾经强制隔离并聚集了大批麻风病人的麻风村,成了历史的活化石。现在住在这里的都是耄耋老人,早就痊愈,失去了传染性,也不会再有人因为患麻风而被隔离至此,但他们过去被强制隔离,法律禁止他们结婚,孤独老去。
麻风被严重污名化,被视为极度可耻和可惧的疾病,历史上是长达几百年来对麻风病人的强制隔离乃至围剿。至少从明代以来,一直到民国时期,再到1949年以后,整个社会提到麻风就是隔离,根据香港大学教授梁其姿的考证,麻风是16世纪后中国唯一需要为了预防传染而进行收容隔离的慢性病。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麻风的强制隔离手段才终于走进历史的坟墓。
对麻风的误解,长期以来根深蒂固。民间相信麻风是“最容易污染他人”的疾病,麻风病人最缺德;一些愚民甚至相信,患麻风病的男女会想尽办法和健康人发生性关系,以便“移疯”——把疾病传给他人,自己脱身。

坚守麻风防治岗位30年的于为晋医生站在山东省莒县麻风隔离村食堂前。这里曾经有300多人免费就餐,如今只剩下了3位村民。。
18世纪中国留下大量杀害麻风病人的刑案记录,讲述了这个群体所面临的周遭敌意。其中一起案件发生在1742年前后,江西乐平县一个村里,村民指控几个住在村外茅棚里的麻风村民收留外面的麻风乞丐,偷鸡偷菜,还在村里水塘洗澡,污染水源。一天晚上,几个村民趁他们睡觉时烧毁了他们的茅棚。结果两个肢体残疾的麻风病人因为行动不便而被烧死。一名行凶的村民受审时供认,主要是害怕,“将他们烧死,也替地方除害,省得传染别人”。
18世纪有官员奏折披露,四川省患麻风病的人不是被置于火中烧死、投入水中淹死,就是被赶走。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则报告了一些地方将麻风病人活埋的风俗。这样的故事延续到近代。

晚清年间福建某地村民,该村麻风病人集中。
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梳理历史文献发现,中国最早的麻风院是在1518年在福建闽县,由一名地方官员主导兴建的。福建是建得最早的,大多数麻风院都建在明朝;而其他省份大多建在清朝,有各种别名,如癞民营、疯子院、麻风寮等。到了清代尤其是18世纪以后,麻风院在南方很多省涌现。民众害怕接触传染,麻风院就越搬越远,迁移到人烟稀少的偏僻地方。不过,病人此时并不算是被关押,机构给他们提供基本食宿,也允许他们到处游荡或就近讨饭。
很多地方官府从麻风病人当中挑选头目,指定他们负责管理麻风院。1865年,西方传教士卢公明详细描述了福州每个麻风院“都有一个‘麻风头’,本人也是患者,或至少名义上是。麻风头管理日常事务,并定期向县衙门报告死了多少人,新进了多少人等等事项,遇到他无法处理的事则向知县报告。”
后期还有一种隔离麻风病人的方法:把病人赶到船上,在河海漂泊行乞。1870年代一项记载称:“广州的麻风院不够大,接收不了那么多的麻风病人,河上建了几个停泊点,供麻风船停靠。”

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以法国艺术大师保罗·高更的生涯为素材,主人公在塔西提岛患上麻风病。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估计有3万麻风病患,社会认为麻风病是不折不扣的“国家耻辱”。当局采取激进的措施,包括彻底隔离、强制绝育和堕胎,不惜以强大国力剥夺他们的自由权利。满清当局也视麻风为耻,有地方武装甚至围捕、集体处决麻风病人。1936年《广东省政府公报》的记载称,顺德县长陈同昶提议,应该像希特勒为国家种族将肺痨、花柳、癫狂病人阉割那样,对麻风病人强行灭种。其提案得到政治精英的普遍支持,只不过因为实施困难而且怀疑有效性,最终没成。
外国传教士推动中国建立了比较符合现代规范的麻风院,根据教会资料,从1887年到1940年,中国至少建立了51个麻风院。广东省的北海麻风院,病人分成男部与女部,禁止通婚。地方政府习惯用武力来强行隔离麻风病人。东莞的石龙麻风院就是典型,它是民国时期病人数量最多的麻风院。1913年,地方政府把大约750个麻风病人送到这里,大多数人是被从广州街头抓捕过来。全盛时期,这里的病人多达1000多名,直到1940年,这里还收容有大约900名麻风病人。当地政府派遣了两个班的武装士兵驻扎在岛上,他们的任务是防止病人逃跑,防止男女病人接触。

《凤凰周刊》介绍麻风隔离的文章,配发了麻风村村民与外国传教士医生合影。
专家强烈批评这种强制隔离的做法。在麻风治疗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传教士麦雅谷,可能是20世纪早期在中国麻风病问题上最权威、最直言不讳的专家,他一直对麻风病的传染性心存怀疑,也从来不太相信隔离的有效性。早在1911年,他就写道:目前中国的麻风院作为隔离场所,它们大多数根本毫无用处。1920年代末,麦雅谷公开批评中国政府推行的隔离政策。1930年,他和我曾介绍过的取得东北抗鼠疫胜利的传染病专家伍连德,共同执笔写了一份报告呈交卫生部,提议组织一个麻风病中央委员会,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隔离目前是不可取的”。麦雅谷以菲律宾为例:首先,隔离所有麻风病人在技术上不可能,因为麻风病早期病人没有症状,难以辨识,他们听到要被隔离的风声会躲藏逃跑,反而增加了传染风险;其次,国家背负不起这个沉重经济包袱,麻风病人主要来自农村,数量庞大;第三,麻风并没有很强的传染性,门诊治疗才应该是国家政策的重点。
但是当局不接受他们的建议。正如梁其姿教授所说:对政府而言,“把有传染性、染患麻风病的人关起来,曾经是、一直是最简单、最能想到、最直接的解决方法。”
中国大范围麻风病强制隔离史,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结束。1985年召开全国麻风会议,中国更积极与世界接轨。1986年强调病人在家治疗的麻风防控新策,麻风宣传的重点转向麻风可治愈,传染性极弱。不过对麻风病的理解和对麻风病人的宽容,迟迟没有体现在政府的规章和法律制度中。虽然麻风病已经很容易控制,但要到十多年以后,麻风病人才能获得包括结婚在内的基本公民权利。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仍剥夺麻风病人结婚的权利,此后尽管专家不断发文反对,但关于“母婴保健”的法规中还是再三强调禁止,直到进入21世纪,2001年,新民法才正式解除不准麻风病人结婚的法律禁令。多数官方资料都强调了麻风控制的成功,但对于麻风病人而言,歧视和隔离的历史充满了血泪!

中国影片《红高粱》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故事是由女主人公“我奶奶”不愿嫁给麻风病人发端。
直到现在,虽然从理性上说,我们知道了麻风病并非不治之症,没有那么可怕,一般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麻风病人,但提到麻风还是心里怕怕。莫言的著名小说《红高粱》中,女主人公“我奶奶”被迫嫁给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家独生儿子,这个儿子就得了麻风病。小说形容当“我奶奶”看到那张开花绽彩的麻风面容,她感到万分恐怖,所以才在高粱地里委身于男主人公“我爷爷”。麻风病这一点在电影中并没有直观表现。
日本著名社会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写了一部小说《砂器》,多次被搬上银幕,七十年代末这部电影在中国非常走红,写一位年轻音乐家为了掩盖父亲患麻风的悲惨处境,狠心杀害照顾他父亲的知情人。
很多作品特别是惊悚恐怖电影,尤其喜欢以麻风病肆虐、一切生命最终都被吞噬的村落、岛屿为故事背景。
英国女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所著的长篇小说《岛》,讲述了希腊克里特岛上以佩特基斯家族四代为代表与麻风病抗争的故事。小说以位于地中海的两个真实的希腊岛屿——克里特和斯皮纳龙格为背景,这两座岛屿隔海相望,如同海上两颗明珠,都被湛蓝的海水所环绕,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斯皮纳龙格岛却让人闻风丧胆,原因是因为1903年后这里成为麻风病隔离区。生活在克里特岛以及周围地区的人,一旦被确诊为感染麻风病,就要被迫遣送到斯皮纳龙格岛接受隔离,几乎再也出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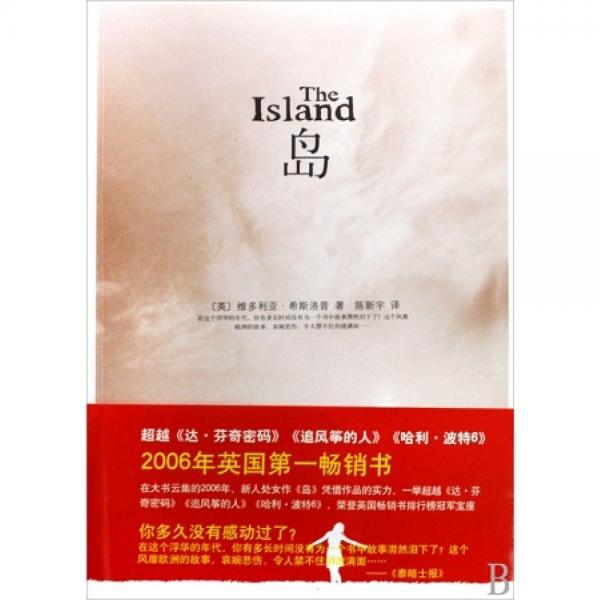
英国女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所著长篇小说《岛》(The Island)中文版。
在当时,一个家族中一旦有人感染麻风病,整个家族都会陷入绝望。这位女作家用几组对立的人物和线索来构建故事,她看到了麻风病带来的痛苦和绝望,以爱与希望来编织小说的主线。正如《卫报》对该小说的评价———这部哀婉小说的最大魅力在于:在最悲凉的情节里,也始终能看到希望。
《岛》和《砂器》毕竟是虚构作品,中外另有不少叙述麻风病的纪实作品。林志明所著的自传《苦难不在人间》,是中国第一部反映麻风病人的苦难与新生的纪实。林志明八岁时感染麻风病,对于麻风病人的生活艰难感同身受。这部作品着重描述,感染麻风病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它也写出了人们对抗麻风病的顽强,追求人生意义的执着,也反映了防治麻风取得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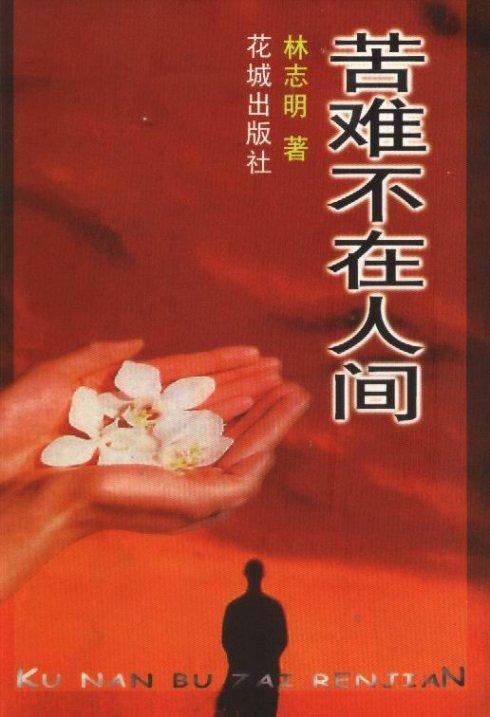
林志明以麻风病人的身份写下自述《苦难不在人间》。
《苦难不在人间》是第一人称的自述,而《生命的力量:一个麻风病人的纪实》是第三人称,这本图文并茂,内涵丰厚的纪实作品,作者林强既是国内知名的摄影家,也是四川的资深教育工作者。十多年里,曾无数次走进四川西部大凉山摄影采风,与普格县的麻风病康复者钱智昌成为知己。钱智昌12岁被发现身患麻风病,为了不传染别人,他选择进入大山深处与世隔绝独自生活,后来得到国家救治来到麻风村,自己种地,还帮助了不少身边的人们。这本书配上令人震撼的照片,展示了麻风病人这一特殊群体在残酷的命运面前的坚韧和乐观。书的封面引用了诗人纪伯伦的一句话:“悲哀的创痕在你身上刻得越深,你越能容纳更多的快乐。”林强创作本书,正是为了让人们更了解那些麻风病人的故事,纪念那批已经老去、充满爱的麻风病人,也纪念那片快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所遗忘的土地。

林强在图文并茂的《生命的力量》一书中,拍摄记录的麻风村民。
近期文章:
面对突来灾情,一个合格的地方官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屡屡爆发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瘟疫
从西方名著《十日谈》说到中国的“三信危机”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不受瘟疫侵袭的
乱世中抗击瘟疫竟然赢了,盛世下抗击瘟疫竟然惨败
推荐三部中国作家描写瘟疫的优秀长篇小说
习近平为何要学毛泽东坚决不下罪己诏
中共保密造成的民族灾难,比泄密大千百倍
中共的公信力是怎样磨损到最终折腾精光的?
宣称人民公社制度适用20年的华国锋,陵园大得不像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