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前,有位认识三十多年的前辈作家和夫人,从纽约到新泽西来郊游散心,很关心地问我:女记者高瑜被判刑了,说她犯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你担任《反右绝密文件》的责任编辑,会不会也被扣上同样或者类似的罪名遇到麻烦?
到美国查阅档案成座上宾,回中国搜集史料当阶下囚
中共有法不依死守档案,究竟有何不可告人的苦衷
《伐林追问》第114、115期,2020年6月26、29日首播
◆高伐林
老高按:三年前《伐林追问》节目连做了两期关于档案的专题,即114期《到美国查阅档案成了座上宾,回中国搜集史料当了阶下囚》、115期《中共有法不依死守档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苦衷?》。整理文字时索性就合二而一,删除些重复的文字和图片。
五六年前的春天,有一位认识三十多年、在国内就认识的前辈作家和夫人,从纽约到新泽西来郊游散心,见到我,很关心地问:最近女记者高瑜被判刑了,说她犯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她弄到一份所谓“中办9号文件”传到了海外;我看到报道说你担任《反右绝密文件》这套电子书的责任编辑,12大本呀,都是“绝密文件”,获取这么多文件,又披露和传播,会不会也被扣上同样或者类似的罪名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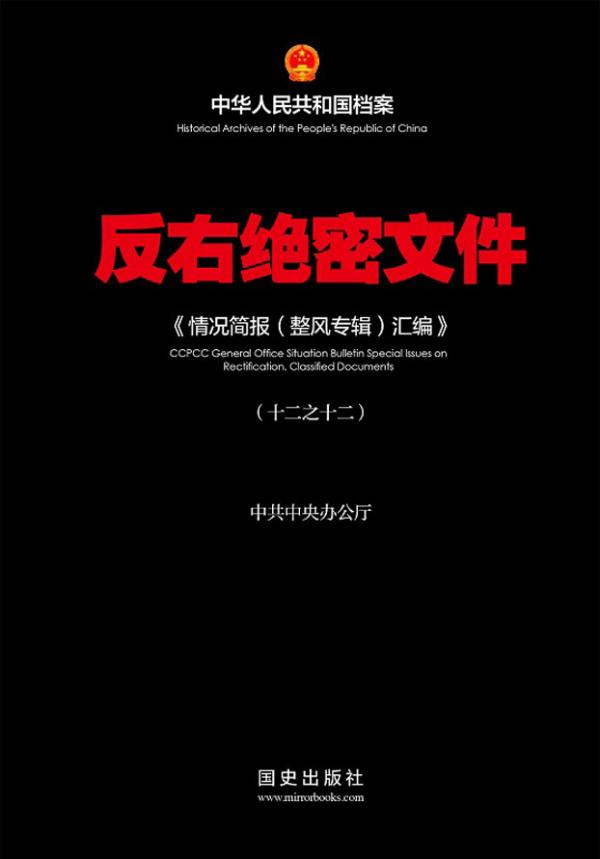
中共违反自己制订的《保密法》关于解密的规定,许多史料只能靠学者在海外出版。图为国史出版社出版的《反右绝密文件》。
这个问题真要讨论,就说来话长了,会扰乱老人郊游的兴致。我没有多解释,只是感谢老人关切我的安危,并请他放心,我相信不会惹什么麻烦的。会不会呢?其实我心里多少也在打鼓。我人在美国,自然不会惹什么麻烦;但我要回国了,会不会有人找麻烦呢?
我这么心里打鼓,自然也是因为有前车之鉴。这位老人家所说的这套电子书,我扮演的角色只是跑龙套而已:受明镜集团旗下的国史出版社委派,代表出版社出面处理编辑出版方面的具体事务。主编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资深馆员宋永毅教授,他率领了一个团队,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郭建、明州诺曼学院丁抒、芝加哥大学周原、中国厦门大学谢泳、中国复旦大学董国强等几位中国和美国的教授,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编委会。这也基本上就是他们二十年来编辑出版《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的原班人马。

宋永毅牵头搜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资料。(高伐林摄)
正是这位主编宋永毅教授,1999年筹备建立文革数据库。当时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迪金森学院任职,利用暑假回中国到处搜集红卫兵小报,包括到北京潘家园这样的旧货市场淘宝。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什么叫“红卫兵小报”恐怕完全不了解。1966年底到1969年中共九大之前,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有过一段相对言論自由的时期,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办小报,有的是油印,很多是铅印,在特殊形势下官方拨点经费当启动资金,再通过发行得以运转。有人曾经估算全国有5000多种,也有人估算为8000多种,其中有的发行量很大,如《清华井冈山报》,因为当时有中央文革小组撑腰,在全国多个城市有航空版印点,可以通过邮局订阅。我当时是武汉的中学生,读到湖北武汉有影响、时间比较长的红卫兵小报就有十多种。一般是四开,像《参考消息》、《新民晚报》那么大;但也有很多是对开,就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那么大。这些宣传印刷品,在文革中风行一时,但时过境迁,就很难寻觅了。当时中国官方正规机关报本来就不多,武汉就是《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两三种,这些报纸还往往因为报社内部的群众组织造反、外部的群众组织冲击而被迫停刊,红卫兵小报的作用就更为重要。它们是文革的第一手记录,要研究文革,研究红卫兵小报是必不可少的。

一份红卫兵小报。文革期间这类群众组织编印的报纸铺天盖地。
宋永毅万万没有想到,竟因搜集红卫兵小报而被北京的国家安全局人员逮捕,所有资料没收。他被怀疑是FBI的情报人员,罪名是“盗窃国家机密”、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不准出境的文件”。拘押好几个月之后,在1999年圣诞节前夕正式被捕。
这个荒唐案件,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关注。发生了让我感动的事——我们最近接连听说中国不少大学的校方毫无担当,一有风吹草动,就把老师或者学生抛出去,与国民党时期大学校长坚决顶住当局压力保护老师学生,有天壤之别。而宋教授所在的迪金森学院,得知他在中国出事之后,第一时间在学院官方网站主页上刊出宋永毅全家三口的照片,呼吁大家关注。随后,一批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发起请愿,呼吁人们签名,要求中国政府高抬贵手释放宋永毅。

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马若德,1930~2019)。
宋永毅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美国学界为营救我出狱,由我在迪金森学院的同事、知名汉学家全大伟教授(David Strand)起草了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请愿书,发动了一个国际汉学界的签名运动。宋永毅写道,据说,当时不少海外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于公开签名还是有不少顾虑的,主要是怕中共报复,不允许他们入境,使他们无法继续研究中国。正当签名人数踌躇不前时,素不相识的麦克法夸尔教授毅然签名——麦克法夸尔是哈佛教授,有个中文名字叫马若德,马若德还对《纽约时报》等媒体公开发表对中共这一做法的抗议:“如果宋永毅这样纯粹的学术研究都要被逮捕,那么外国学者还怎么在中国做学术研究?中美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关系还如何维持下去?”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带领下,签名的国际知名学者人数一下子突破了170余人,加上国际媒体对请愿信一事的广泛报道,给中国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这也开创了国际汉学界大规模地签名营救被中国政府拘禁的同事的先例。
我看到一个数字,在网页上签名的超过三千一百人,并扩展到世界各国各地区,签名者中有很多知名人士,像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ton Friedma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宋永毅被捕也引起美国国会的关切,率领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访问北京的共和党众议员沙尔蒙,同江泽民见面讨论人权问题,当面提出了宋永毅被捕问题,敦促江亲自了解这个案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在2000年1月13日记者会上,被迫做出回应,他说:“宋永毅接受境外机构的资助,涉嫌为境外非法收买、提供情报。”但这一说法实在荒谬,不仅是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如何强词夺理,更让人们看到这个体制如何疑神疑鬼。海外媒体纷纷反驳:

文革文字和音像资料在北京潘家园等地正常交易。
其一,红卫兵小报过去是公开发行,铺天盖地,不过年代久远,才需要费心收集而已,就像文革的纪念章、纪念邮票和领袖早年文章一样,称其为“情报”不是有意混淆视听吗?
其二,什么叫“非法收买”?买卖旧报纸旧书刊难道不是正常合法的交易吗?触犯了什么禁令?
其三,“接受境外机构的资助”更不知所云。宋永毅在美国任职,拿的当然是美国大学的薪水和项目基金,在国外的华人华侨谁不是凭劳动从“境外机构”得到一份收入?
在江泽民亲自过问下,闹剧终于收场,宋永毅在2000年1月被无罪释放,回到美国。他被抓的时候还不是美国公民,回来之后,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拜登等几位有影响力的人士联名,参议院授予宋永毅美国公民身份。
那位担心我的安危的老作家询问我之后,我又受国史出版社委派,协助宋永毅先生出版了一系列历史资料电子书,总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例如《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续编10卷,《千名中国右派处理结论和个人档案》6册,《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文化大革命中的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等等。我扮演的还是打下手的角色,但是越来越感觉到历史档案的份量。借用那句俗话:档案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档案是万万不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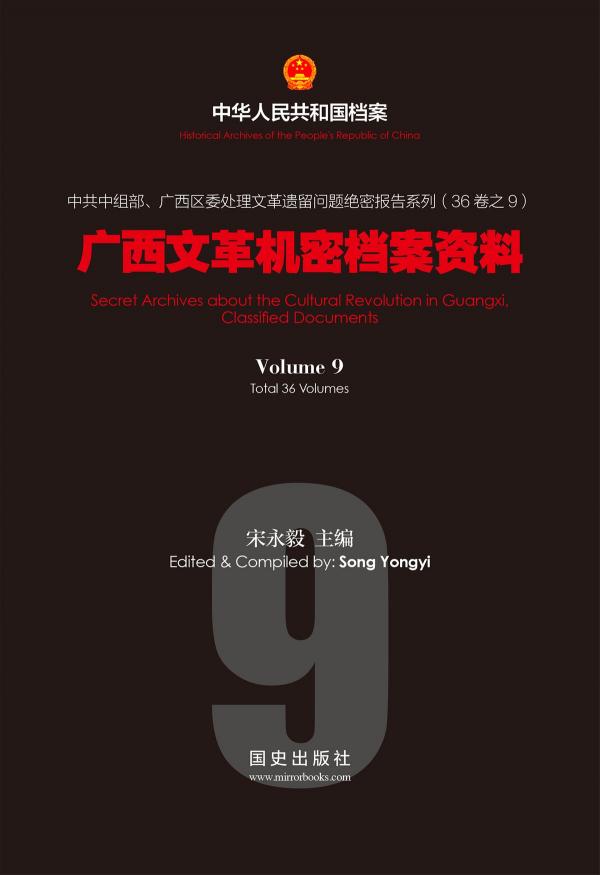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36卷之9)(国史出版社)
不幸,档案的重要性,当权者也深知。所以他们才不仅封住真正的档案,就连谈不上档案的红卫兵小报也要把住。他们的用心,正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写的那句名言:“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研究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甚至中国历史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一肚子苦水,一肚子怨气。我想起资中筠研究员的文章《关于解密档案的一段往事》。
资中筠是1930年6月22日出生于上海,精通英语及法语,是翻译家,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美国研究》杂志前主编资中筠女士。
资中筠回忆,1985年11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第一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这应该算是中外关系史界的一项带有开创性的活动。摆脱纯粹以“帝国主义侵华史”来概括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套路,以客观的、全方位的视角探讨中美关系史。主办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这两个单位都是新成立的。当时中美建交才五年,中美关系及其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气氛空前活跃。几天会议中,有一个问题不断凸显出来,就是档案资料问题。资先生感叹,中国近代史的档案查阅困难重重。她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接触国外图书档案亲身体验,痛感其便捷与我国鲜明对比。
美国按照法规,30年解密政府档案(后改为25年),每年由政府出版,全世界都可订购。中国当时能进口这套资料的只有极少数几家图书馆。2011年,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FRUS)》举行150周年纪念——第一次正式公布外交档案始于1861年南北战争期间。每当与外国签订条约,需要国会批准,除提供条约文本外,还须附谈判经过的原始文件。1861年是第一次全面、正式公布,不仅是个案,而是全部外交档案;不仅对国会,而且对公众对媒体公开。1861年那一卷被定为首卷。

美国国务院。每年出版按规定年份解密的外交档案汇编《美国对外关系》。
开此先例后,每年都有外交文件解密。后来美国对外关系日益扩大、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保密制度日益正规化,就需要正式的解密制度。1966年约翰逊政府通过《知情权法》,中国通常按字面直译成“信息自由法”,资中筠认为“知情权法”更准确。该“法”的主要精神是把档案的解密从“需要”,变为“权利”,就是说,过去是因为某种工作需要知道而公布,现在是确定了解真相为公民的权利。因此定期公布档案是政府的义务。英国早已有30年解密政府档案的法律。美国是沿用了英国的办法,此法也适用于一切政府部门的档案,时限不等,只少于不会多于30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历史办公室”,由专人负责整理分类,到期必须公布出版。如有特殊需要继续保密的,像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或者敏感问题会引起外交纠纷的,必须有法可依,经过特殊批准。即使一份文件中,有几句话因故尚不便公开,就在那份文件中用虚点标出,明告查阅者:此处有省略。也就是说,解密是自然的,不需要批准;保密倒需要批准,而且要明白告诉查阅者。根据《知情权法》,有关人士如果指定要看某项暂未解密的档案,可以提出特殊申请,如得不到批准,可以到法院告档案馆或有关部门,资中筠说,已经有不止一起学者因写书需要而打官司胜诉的案例。

美国众多历史文献档案。
她说,我1979年调到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图书馆发现了FRUS,如获至宝,像发现金矿一样。那个图书馆进书及时,1949年的已经上架。我钻进图书馆,详细翻阅自雅尔塔会议以来有关中国和远东的那几卷,外加历年国会记录等等,经过大半年,写出美国在中共夺权前后对台政策的详细决策过程,在当时是国内第一篇根据最新外国解密档案写成的有关这一热点问题的论文。由于材料很多,资中筠决定写一本书。1982年正好有机会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和档案馆。
她说,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曾专程到华盛顿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工作人员熟悉业务,敬业而热情。接待她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对她研究范围的资料如数家珍,查找效率极高。他们的业绩是以查阅资料的人次和数量计算的。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资中筠曾遇到提出要看的文件在目录上有,但是标明此件暂不公开。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竟怂恿她根据《知情权法》去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开放,如不允,还可到法院告他们。资中筠大为惊讶,说外国人也能告吗?他说能,已经有先例,有一位苏联学者告过,而且胜诉。

美国国家档案馆。
资中筠说,美国档案管理者站在档案馆立场,越多公开越好,因为这是他们的财富。对比中国的档案管理者,是与“机要员”混为一谈,以保密为己任,所谓“管理”,目的是防泄密,没有为学术研究服务的观念,“机密”的范围更随意扩大。养成一种心态,越少让人知道越好。虽然她没有碰到宋永毅那样的遭遇,但处处受限,总是“未敢翻身已碰头”。
资中筠举例说,自己搞研究,在大量运用美国的档案之后,照理应该有中方资料的旁证,才算完整。我要求不高,不指望在国内也像在美国一样自由地钻档案馆,只想找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与中共之间有限几次重要交往的中方史料。但是在国内寻访处处碰壁。首先是不得其门而入,托了人走了“后门”,才找到了门路,一路打报告,列出少量要查的文件,级级审批,终于拿到了特许的“批件”,找到中央档案馆,通过层层管卡,递上清单。档案馆的规定是,只能看明确列出的那几个文件,不能根据某一个范围查目录。即便如此,我列出的单子上最重要的几个是与苏联有关的文件,还是被拒绝。我报的题目是中美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是美苏冷战的背景,实际上是美、苏、国、共的四角关系。管理员说,他们领导认为研究中美关系,不该涉及苏联,与我的研究范围无关,“就不必看了吧!”我据理力争也无效。资中筠说,由档案管理人员来决定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一大奇闻!

在党务政务公开栏公开的,却是“保密行为十不准”。
资中筠回忆,1985年11月那次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中美关系史研讨会。与会学者不约而同地围绕档案问题大倒苦水。特别是让他们心里不平衡的是,外国学者看中国档案反而比中国学者得到更多机会。“西安事变”是近代史研究不可绕开的课题,中国学者多少年来看不到有关档案。但是有一位常来常往的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邀请某档案馆主管赴美访问一次,就取得了阅读西安事变档案的许可,从而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论文,提出新的看法。江青接待美国女学者维特克,就给她很多材料;美国商人库恩要写江泽民传,中国有关部门大开绿灯。

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外国学者从中国官方拿到更多关于西安事变的档案。
当然,话说回来,只是说比中国同行要好一些,并不是说他们在中国就能毫无限制,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他们能得到的,只是中共想喂给他们的。当局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保守对自己没有利的,这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这种“内外有别”,屡见不鲜。但当时开会的人痛心疾首,有人甚至拍案而起,大家认为应该上书,争取档案依国际惯例开放——这是1985年,改革开放高潮中,人们都比较天真和单纯。于是资中筠被推举执笔,给主管档案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等人写了信。
资中筠说:能够打动上面最正当的理由,是“对我政治上有利”——她所说的“对我”,当然不是指她本人,而是指我党我国。她特地在信中举例:有一名美国负责外交档案解密工作的人员曾对我国学者说:“我们根据法律必须公布档案,而你们什么都保密,……从长远看,历史将对你们中国不公平,因为以后的世界史都是我们一面之词。”
资中筠说,此件送上去,胡乔木有批示,重申他过去的指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档案可以开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暂缓。也就是说,以中共成立划线。“暂缓”,缓到何时?上级想怎么缓就怎么缓。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有了三十年解密的法律规定。但是资中筠说,实践中还有种种阻力。她就碰过钉子:
写《财富的归宿》这本书时,涉及福特基金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这件事。福特基金会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批准在中国正式设立办事处的,主管单位为资中筠供职的中国社科院,1986年双方领导签有正式协议。

美国福特基金会。
上世纪末,资中筠远涉重洋在纽约福特基金会总部的档案室中查到这份协议的英文本原件,回来后希望从社科院找到中文本。以为很简单,就在本单位么。不料她与有关办公室联系,得到回答:这份文件确实存在这里,但是经请示领导,不能查阅——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资中筠很不解:按理说,这一协议当时就是公开的,不是机密文件,只是一旦归档,就“侯门一入深似海”,是什么心理作祟?
其实,中国在这个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制订了多个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等。对照当今中国现实,究竟是谁违法呢?我念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第十九条 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档案馆应当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并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简化手续,提供方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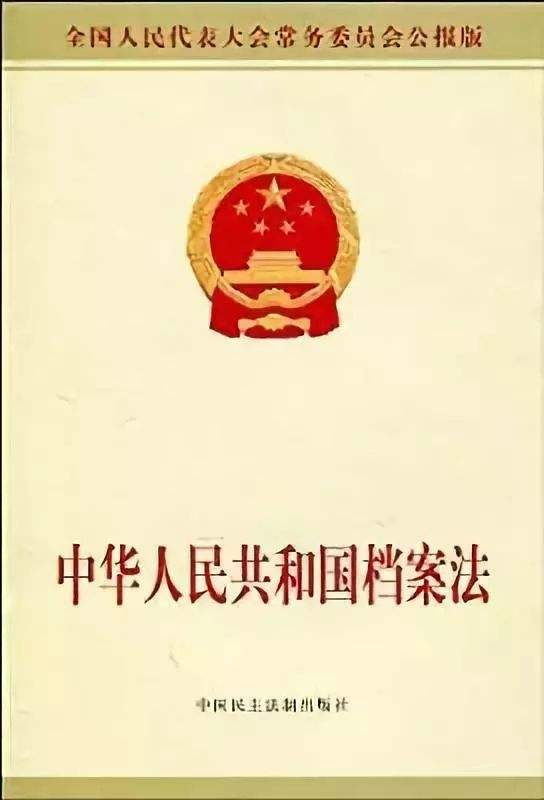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我再念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第十条 国家秘密的密级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
绝密级国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的损害;机密级国家秘密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的损害;秘密级国家秘密是一般的国家秘密,泄露会使国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
第十五条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应当根据事项的性质和特点,按照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限定在必要的期限内;不能确定期限的,应当确定解密的条件。
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规定外,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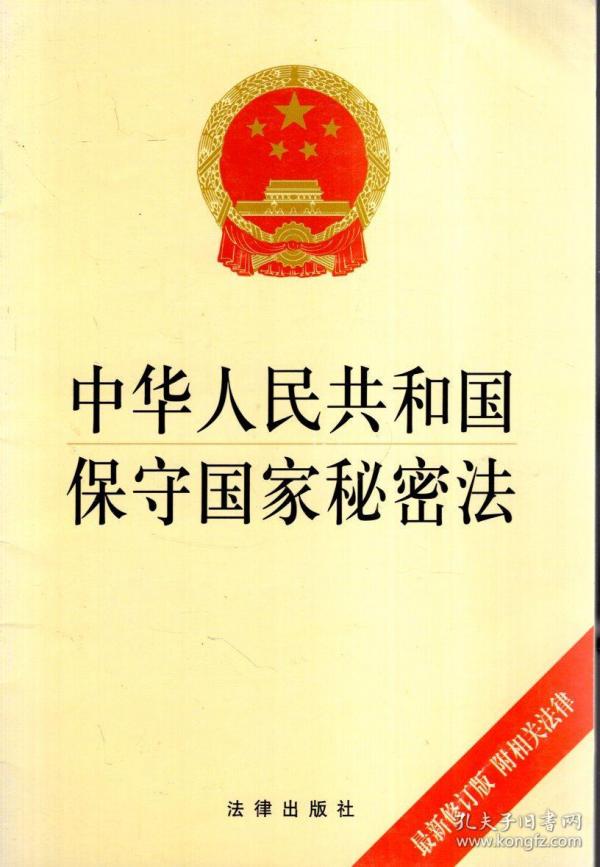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机密法》
可见,在这个档案领域、保密领域,并不是无法可依,但是挡不住有法不依!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教授有一次在当时还在运作的共识网回答问题,杨教授就谈到法规成为一纸空文的种种情况。
主持人说:我听到一个观点,研究历史隔多长时间更合适。有人提出,隔20-30年或者30-50年最好,因为相关利益的人已经过世了,或者已经退下来了,就不会再干涉历史研究了。您觉得这种看法靠谱吗?

杨奎松教授
杨奎松回答:我觉得不靠谱。中国8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档案开放得最好,当时的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的个人卷宗都可以查阅。后来突然就宣布不开放了。为什么?国民党那些人早就已经跟中国大陆没有什么关系了,隔的年代也够久了,按道理没有敏感性了呀。但是不行,问题在于他们有家属。因为某研究者从二档看到某国民党人的一个什么东西,发表出来了,这位国民党后人的家属就到处告状,二档怕惹事,只好把个人档案全都封起来不让看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好几个档案馆都发生过,包括学术刊物和文章作者都有因此被告的。
政治干涉的情况就更多了。而且不是时间隔得越远,开放就越好。杨奎松说,如果我们去看北京、上海等许多地方的档案馆,都能发现,那里的档案开放目录,今天比八九十年代许多部分都大大减少了。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开放目录,几年前我去看时,十几册目录,几乎每册都满满地贴着白纸条。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曾经开放了很多目录,后来上面说这个方面不能开放,下面就把这个方面的目录一条条都贴起来不让看。过一段时间上面又说另外那个方面的不能开放,下面又赶紧把那个方面的目录也贴起来。到最后,许多本开放目录里面就剩不下几条可能看的目录了。

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收藏1912年至1949年间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权的档案。
杨奎松说得一针见血:在我们国家,虽然1987年通过了《档案法》,也明文规定了30年解密的法律条文,实际上权远比法大。实际管档案的机构,会给下面的档案馆下达哪些可以开放,哪些不能开放的规定。档案馆不是听《档案法》的,因为《档案法》管不了他们,上级主管机关是管他们的。因此,开放什么,不开放什么,全是管理机构说了算。
我们看到,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领域,有好几位学者能脱颖而出,著作等身,固然有他们各自的勤奋刻苦、胸襟眼光、聪颖才气等等主观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一度在接触机密档案的部门工作——在一般的体制内单位都不行,他们是真正对机密档案“近水楼台先得月”。
杨奎松写了多本重要著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研究》、《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他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任编辑的经历,应该说是有巨大帮助的。

刘统研究员
刘统也是这样,当过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门类责任编辑,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当教授。他著作也不少,早年有三部纪实——不是纪实文学:《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后来又有了《跨海之战》、《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刘统于2022年12月21日去世。享年71岁——老高注)
还有一位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退休了,到华东师大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当研究员。著有《旋转的历史》、《从革命到改革》,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56—1960、《中国共产党历程》第二卷等。他多年积累了档案资料,就有机会做更多发挥。去年(2019)9月,我参加在纽约举行的土改镇反国际研讨会,王海光教授提交了两篇论文,一篇题目是《土改前夕的中共新区征粮问题》,另一篇题目是《民变和“匪乱”——中共贵州建政初期的征粮和剿匪》,介绍“土改的前奏曲”——由中共大军所到之处征粮激起民变,投入重兵剿匪。他介绍的很多史实让我大开眼界:

王海光教授
从1950年2月开始,西南形势突变。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叛风四起。半年时间西南土匪发展到65万之多,是当时全国105万武装土匪的一半以上。
西南大规模匪乱的爆发,为中共新政权始料未及。邓小平说:“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叛乱者“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
贵州的匪乱发生早、平息晚,是全国匪乱最严重的地区。中共贵州新政权刚刚成立,就一并推出征粮、禁银和禁鸦片三项政策,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冲击非常猛烈。称为“三股水一起流”,把贵州民间财富扫荡殆尽,引起了当地民众和少数民族激烈反抗。
西南地区征粮晚、数额大、行动激烈。征粮工作队中流传说,“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王海光教授引用了很多当时的报告称:有的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绑吊打,游行罚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农民卖子纳粮的。
1950年7月31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王海光指出:叛乱者的口号是,专打山东人(北方人、下江人、外省人)“破产保产,拼命保命”等等,可见他们的要求是维护自家利益,与国民党政权的“应变阴谋”并无干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官逼民反”。

论文集《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收录了王海光教授探究“土改前奏曲”征粮和剿匪的两篇论文。
贵州大面积匪乱的爆发,是在1950年2月下旬的春节过后。由小规模暴动,逐渐形成大面积叛乱,渐渐集中为成百上千的大股,活动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进而公开打出反对新政权和解放军的旗号。到1950年3月底,叛乱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叛乱达到高潮。较大的反叛武装约460余股,达十二、三万人枪,其他小股散匪和裹胁的民众不计其数。3月到至4月上旬,已经被解放军收编的原国民党军正规军成建制的14个团先后叛变,大部分地方保安团队和各地乡保武装也相继叛变。仅3、4月间,中共军政人员牺牲即达两千多人。公粮损失巨大。全省79座县城,被土匪反叛武装占领了31个。在中共控制下的48个县城中,大多数只是占据了县城和少数乡镇,政令不能出城。
王海光写道:
中共攻取南方诸地之顺利与各地新政权建立后突发起来的大面积“匪乱”,在不足半年时间内,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大反转。为了平定新区“匪乱”,中共当局调动了140个师约150余万人的兵力,花费了三、四年,共消灭了各种“股匪”260多万人。中共在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又在打平地方势力中进行了3年多的剿匪战争,所花费气力甚至不亚于前者。由此可以认为,整个“解放战争”的时间不是3年,而是6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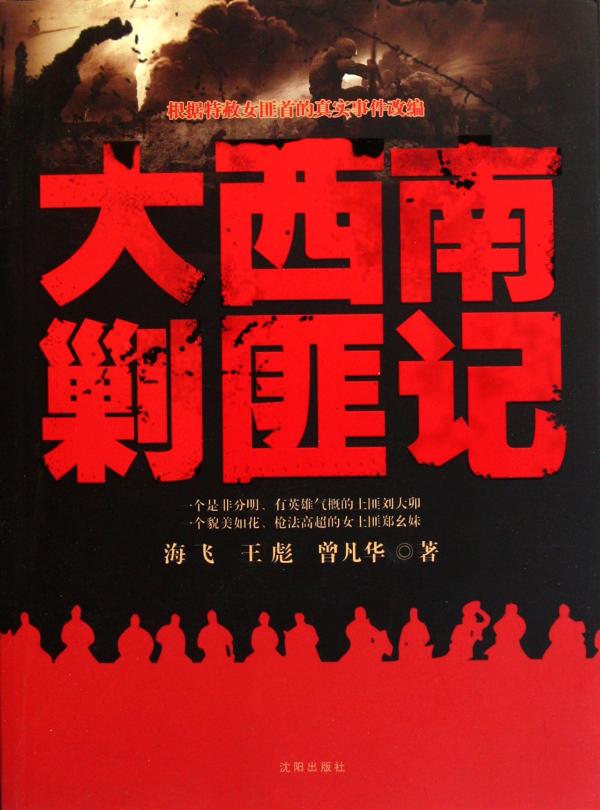
御用文人按中共政治口径创作了西南剿匪的作品,但档案史料揭示了“官逼民反”的残酷真相。
我相信,王海光教授的这些披露和论述,比随便什么人,例如某位网上写手、自媒体网红说同样的话,公信力要高得多——因为他的身份和学术背景,人们相信他有档案史料的依据。
我们在这里强调了对于历史研究来讲档案是多么重要,也就揭示了中共为什么要死死把住档案,但是还得把上期节目我们说过的话,倒过来再说一遍:没有档案是万万不能的,但是档案不是万能的。杨奎松教授说:对于近现代史,特别是现当代史来说,即使在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也一样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历史事件的大致线索与原因。不可能把历史过程中的每一块碎片都找到,具备足够的推理和分析的能力,就能够像拼图那样,把注定是残缺不全的各种资料拼接起来,并运用你的推理、分析和想象力,填补上其中空白的部分。
近期文章:
“中国的贝利亚”:关于康生的传言和真相
中共“左王”另一面:曾是有良知有胆略的改革闯将
十五年半软禁生涯重新塑造了一个赵紫阳
赵紫阳拒绝检讨,放弃复出执政的机会,是对是错?
昙花一现:中共历史上最顺应历史潮流的一次党代会
胡耀邦被逼下台后,孤掌难鸣的赵紫阳艰难打赢改革保卫战
八十年代改革史:三个半权威先后废掉两个大脑
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交底,为什么让邓小平勃然大怒
赵紫阳为什么执意访问朝鲜,犯下平生最致命错误?
赵紫阳在大跃进中发动“反瞒产”铸成大错
母亲早对赵紫阳讲:你给共产党拉套,不会有好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