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反感乃至痛恨此刻正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希特勒式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历史学家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我们过去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任推出去
老高按: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因其最近“价值观重于事实”“任何怀疑否定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都是历史虚无主义”之类言论,不仅成为越来越多网络写手的靶子,也让越来越多体制内学者不以为然,忍不住要站出来以正视听。例如,清华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就写了一篇《对不起,葛老师的意思我还是没完全弄明白》;还有人搬出了北大历史教授罗新的多篇文章,虽然不知其具体锋芒所指,但是其内容足以反驳葛剑雄的观点。姜克实教授在中国的一次远程演讲中还不指名地批评了葛剑雄。
其实,反驳今天葛剑雄的,还有葛剑雄自己——昨天的葛剑雄。我读到葛剑雄最新反驳的微博《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过,今后也不会变》,文中的观点是否对头且不说,他说“基本观点没有变过”,这简直是矢口抵赖嘛!
我找到《葛剑雄编年自选集:我们应有的反思》,一本中信集团出版的大书,其中有一篇葛剑雄1997年的文章《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我的史学观》,扫描下来,请今天的葛剑雄读一读白纸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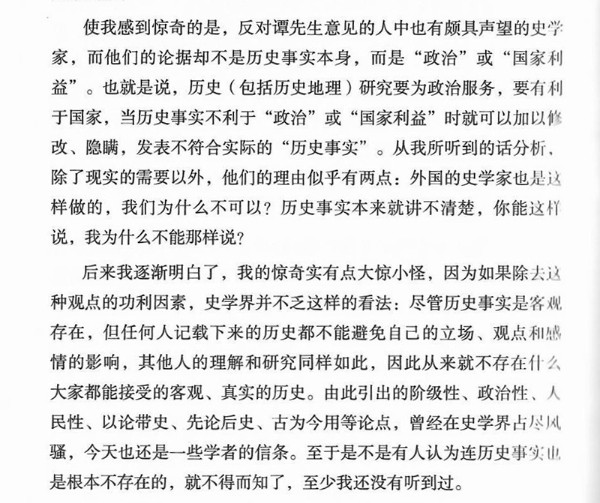
以上294页这段,他谈到那些反对他的导师谭其骧的学者的观点(他当然是站在导师一边的)。他现在所持的,恰恰就是他当年反对的观点。
再如298页这段,看他如何归纳历史的基本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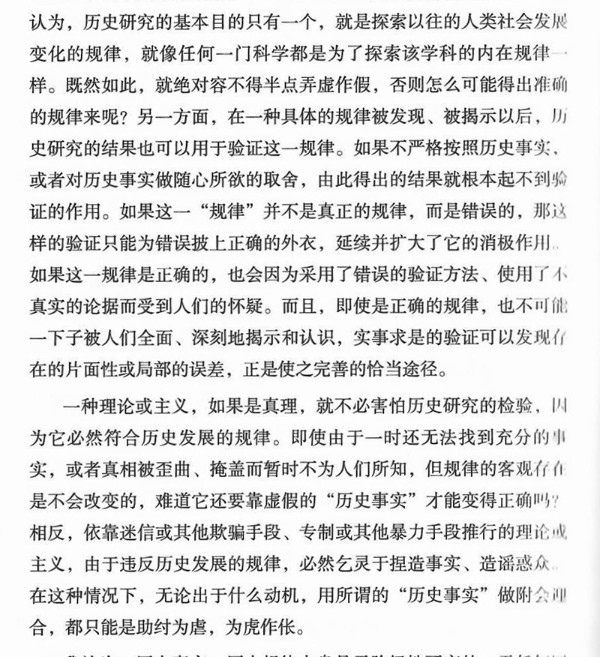
今天我想推荐孙立平和罗新的三篇文章,篇数虽然多,好在都不太长,一共六千多字而已。
对不起,葛老师的意思我还是没完全弄明白
孙立平,公众号:孙立平社会观察
1、最近,网上为了葛老师的一个观点,吵得不亦乐乎。我看了一些网友的质疑,也看了葛老师义正词严的回复。总的感觉,葛老师绕的能力是真强。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她经常说,不行,我的脑子慢,你让我捋捋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看来,现在争论的这个事情,不从根上捋捋还真会被葛老师带入了迷宫。
2、社会学家默顿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显功能和潜功能。我把这对概念的含义稍微改造一下,大体是下面的意思。任何人们制造或设计出来的物件,一般都有两层意义的功能或作用。一层是显功能,即人们想用它来干什么?它主要是干什么的?这种功能是明确和显而易见的。另一层则是潜功能,即潜在的功能,也就是这个物件实际上还会起到的、并非是当初人们有意设计的、而且不是特别明显的作用。
3、如果这么来看历史学的性质和作用,就比较清楚了。为什么人们要研究历史?为什么社会中要有一个历史学?其显功能无非是这么几个。第一,了解过去。人类是智慧动物,总想知道自己的过去是什么样的,不管有用没用;第二,实现文化的传承和积累,沿着前人的足迹出发并走得更远;第三,提供历史的借鉴,避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有一点需要说明,这几项功能的实现都要以真实为前提。虽然历史研究不可能完全达到真,但必须尽量去接近真。
4、但历史学起的作用绝不仅仅是这些,它还有潜功能的一面,比如说,搞历史研究,从社会的角度当然是一项学术活动,但有时对研究者个人而言,又是一个饭碗,弄好了还是一个不错的饭碗。不信去掉这层含义,还会有几个人会以历史研究为业?当然,潜功能还包括葛老师说的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等。但这时也要说明一点,潜功能作用的发挥,往往也要以显功能为前提。试想,没有那个相对可信的真,就是为了别的目的胡编乱造,谁会给你饭碗?你即便是想拿着那假历史去给别人帮忙,也只能是帮让人笑话的倒忙。
5、如果是这么看问题,就可以看清楚葛老师带我们绕的是一个什么迷魂阵了。实际上,在历史研究这个大的题目之下,不同的人是在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为了保存历史的真实,宁可付出哪怕是生命的代价,也要秉笔直书;有的人出于探究过去的兴趣,一辈子皓首穷经;有的人为了挣个饭钱,做着可能毫无意义的考证;有的人为了之外的某个功利性目的,尽量去挖掘有利的史实,甚至不惜扭曲一点。现实中这些都是存在的。如果用葛老师的说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不同意,但也不想反驳。
6、问题是,这些事情是应当分开的。用这几天流行的话来说,为了真实的历史与为了政治正确的历史应当是分开的。而葛老师的问题则是,尽量把这些事情搅合在一块,并且把这种搅合叫作“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他不无诚意地说:我说这番话,意在告诫青年人、天真的读书人不要以为近代史是学术,可以自由讨论。在葛老师这里,政治正确范围里的事情,马上变成对青年学者学术研究的要求。这哪里是在“捅破一层窗户纸”,这是在窗户纸上倒了一盆浆糊。
7、为了让这盆浆糊更好地黏在窗户纸上,葛老师又援引了这样一个似乎是不容质疑的说法: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这句话,从政治上说,我不想评论。但葛老师是学术圈中人啊,难道葛老师不知道除了研究和宣传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发表和讲授的问题?你说发表和讲授是属于学术还是属于宣传?应该用哪个标准?还可以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形:如果那些真实但“政治上不正确”(其实这种不正确往往是人们臆想出来的)的成果都只能存在于研究者个人的电脑里,那将来人们学到的历史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8、为了让绕的这个圈子更有科学性,葛老师又提出了一个选择性和价值倾向的问题。大体的意思是说,历史研究总是有选择性的,总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因为历史是浩瀚的大海,你的研究不可能没有选择。表面上看,这话也说得很聪明。但其实是似是而非。谁也不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秦始皇哪天洗脚哪天没洗脚,乾隆皇帝哪天打喷嚏哪天没打喷嚏,我们是还原不出来。但不能做到完全真实不等于不努力去接近真实。这不是历史学的基本常识吗?价值观下的选择也是如此。我为什么研究这个不研究那个?我为什么注意这个细节不注意那个细节?因为对理解历史的意义及重要性不一样。但这与从政治角度考虑的选择不完全是一回事。
9、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去徐水,回来路上顺便去看那个大午。当时他正在走火入魔地研究黄帝还是炎帝(我记不清了)的出生地,说那个出生地离他们那里不远。然后还郑重其事地托付我向历史学界的朋友征询一下意见。恰好,过一段时间开会时遇到葛老师,我就说了这个事,问他这个事靠谱吗(因为我对这个一点不懂)?葛老师的回答是,黄帝(或炎帝)这个人有没有都说不清楚,哪来的出生地?我知道,大午弄那个也是想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找点文化资源。而葛老师的态度也很明确,历史要以事实为基础,不能为了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
10、最后我还要说一句,葛老师在有的地方的表达上还需要斟酌一下。比如说,历史上的历史都是为政权合法性辩护的。这里,合法性这个词有点敏感,最好不用。而且,历史上的统治者为什么有时用扭曲事实的方式为自己服务?那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少数人的利益,有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我相信,在我们今天的时代,历史真实性与政治的正确性之间的一致性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可以更好地得到统一。葛老师可能有点多虑了。
质疑与反抗是历史学家的使命
罗新,公众号:歴史在加速
我几年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一年,那里有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90多岁了还每天到办公室上班,经常写文章、演讲。他写的很多文章是适合专业之外的人读的。
后来我看到他有一本书叫作The Scientist as Rebel,就是《作为反叛者的科学家》,书名很有意思。我想我们应该也有一本书叫作The Historian as Rebel,《作为反叛者的历史学家》。这涉及历史学是干什么的,我们为什么做历史,我们做历史是为了谁。
▌质疑与反抗是历史学家的使命
历史学家归根结底不是传承什么文化,也不是要把某种古代的东西保存下来。他的使命本质上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
我们身边的情形是,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历史,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滥用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己也不免于滥用和错用。可以这么说,我们讨论的历史,我们所使用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经不起追究的。
在我的领域也是如此,我是做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的,很多大家常常提到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的。
比如有一个常见的说法,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从此以后南方人口、经济的占比大大增加,整个历史都改变了。
说起原因,中学教科书里有一句简单的话,而且大学里也有很多老师这样讲,说是因为北方战乱,大量北方农民到了南方,带来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所以南方就得到了大开发。
我做学生的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说法,等当了教师自己在课堂上可能也讲过。其实这个说法经不起追问: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是指什么呢?是作物品种,是生产工具,是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比南方稻作农业的技术更先进吗?那么旱作农业的种种技术能够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去吗?
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这个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换个思路,首先要问的是,那时的南方劳动者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北方逃难南下的流民吗?难道不是以土著为主吗?土著是些什么人呢?除了原有的在郡县体制下的国家编户,大量不说汉语、不服属国家管理的山区土著人群,所谓蛮人、山越,是如何进入国家体制的?
今日所谓南方人,他们的祖先难道都是北方移民吗?当然不都是,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不是北方移民,而是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过的,从蛮人、越人改造成了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劳动者,他们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
由此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华南变成了华夏、也就是后来汉人的家园。
然而这一转变不是那么简单流畅,那么理所当然的,不是一首浪漫曲,不是英雄史诗,其中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近似情形下已为我们所知的那种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制造的痛苦。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被遗忘、被转化,成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南开发史。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哪怕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那些说法,也经不起追问,经不起深入推敲。
▌做主流的抵抗者,重新质疑已有的说法
那么历史学家做什么呢?历史学家去重新考察这些东西,作为一个rebel,作为反叛者、起义者、异议者,去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重新质疑、一再质疑。
在座各位不只有做历史的,还有各个学科的朋友,我想rebel这个定位对大家都适合,各个学科都差不多,要做的都是重新质疑已有的说法,我们都去做已有说法的异议者,都去做主流的抵抗者,不限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和政治环境。
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在什么样的时代,所有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应该是反叛者、抵抗者。
正好最近我在想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历史学家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熟悉的,就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是哪里来的?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
对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不只是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营养即来自这里。
看看我们今天,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发展状况,大家各有自己的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比如,大家肯定知道这几年大批网络爱国者对姚大力先生的围攻谩骂。(复旦姚大力教授在本是小圈子的讨论中谈到“大一统”背后的血腥代价。特别指出汉代征讨匈奴,我们的历史书只津津乐道“赫赫武功”“民族自豪感”,忽略了其中非人道惨烈现实。其专业意见触犯了大众“常识底线”。——老高注)
所以姚大力接着引申说,如果要全面地认识历史,不能只看到一个“大国崛起”的威风,而忽视背后的问题,并期望今人能以史为鉴,在遭遇到类似处境时,尽量减少流血冲突。
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你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来的?
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
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
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任推出去。
1945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20世纪的学者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
历史学家做什么,为谁做?所谓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该探究什么,为谁、为什么探究?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没有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人能宣称自己真正掌握了真理,这是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完全明白的事情。但是做什么、不做什么,做到哪个程度,这确实需要我们反思学术史上、历史上的教训。
李礼让我在签到板上写句话,我就写了句“有所不为”。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rebel,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
为那些被遗忘的人发出声音
罗新,公众号:歴史在加速
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常识,历史是一种记忆,史学被当作一种记忆来讨论。
但事实上,是遗忘在塑造我们的记忆,理解记忆的关键在于理解遗忘。
遗忘有很多意义。比如一天记诵一万字,我怎么也记不下来,这种遗忘是个人生物属性上的局限。
过去有“集体失忆”的概念来与集体记忆相对应,也是强调由于记忆能力的不足而无法维持与过去的联系,这种失忆是一个消极过程。
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积极的遗忘,是出于某种目标,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联系的遗忘。
焚书、文字狱、删帖、屏蔽敏感词或禁言,就是要造成一种主动的遗忘、一种强制性的遗忘。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样的遗忘是有历史学意义的。
记忆的形成过程,一方面是努力记住一些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努力忘记一些东西。
▌看似不存在的,也是必须关注的
我常常强调“遗忘的竞争”,因为我们能够了解的所谓过去、所谓历史,都是不完整的碎片,这些碎片是往昔岁月中持续进行的各种竞争——记忆与记忆的竞争、遗忘与遗忘的竞争、记忆与遗忘的竞争的结果。
那些相互矛盾冲突的史料碎片,不再是简单的孰是孰非、孰真孰伪的关系,值得我们辨识的是它们各自体现着怎样的叙述传统,代表着怎样的竞争力量,反映了什么样的竞争过程。
我们要考察那些被排斥在记忆之外的内容,特别要看到某些特定内容是被什么样的权力组织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的。
过去几千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传统史学,就是这种被安排的结果。
中国史学有官修正史悠久的、独特的传统,这反映了政治权力作为历史叙述竞争力量的绝对优势地位,所有其他竞争者都因弱势而难以发声。
傅斯年说传统的史学是“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
当我们意识到存在着遗忘的竞争,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能了解掌权者为何、如何实现某些事项的遗忘,以及这些事项大致上可能是什么内容,那么无论进行什么样的道德伦理批判,都不能使我们向历史走得更近一些。
因此,那些遗忘,那些看似不存在的,也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史学”。
▌探寻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关于记忆与遗忘的竞争,我举一个很好的研究实例。
陈侃理在日本出版的《中国史学》第26卷(2016年)有一篇《〈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对于《史记》的史料学特色有非常好的讨论。
讨论的主要线索是,秦二世胡亥之继秦始皇为皇帝,到底是不是秦始皇临终指定的?
传统史学中只有《史记》一种说法,即胡亥本非秦始皇指定的嗣君,而是在秦始皇死后由赵高、李斯矫诏诈立。
对于如此充满潜在争议价值的事项,秦末汉初必定存在多种说法,但是因《史记》的独特地位,两千年来,司马迁所取的说法便成唯一幸存者,其他说法早已消失。
如果不是因为今日幸见出土竹书,研究者即使对《史记》的说法颇存疑虑,也因全无证据而无从质疑。
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恰好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叙事,说秦始皇临终让大臣议嗣位人选,李斯建议胡亥,始皇说“可”。
不同的史料足以引发对这个问题的再检讨。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肯定是接触到了《赵正书》所记的这个说法的,甚至应该还接触过其他说法,但为什么《史记》选择了现在这个版本的故事呢?
陈侃理指出,《史记》版叙事起于楚人反秦时的政治宣传,“胡亥不当立”的说法遂与汉朝的法统发生关联,自然为《史记》所取,其他说法慢慢消退,终至湮灭。
《赵正书》属于“小说者流”,在传统史料学框架下当然不足与千古杰作《史记》并列,但正如陈侃理所说,《史记》的史料来源大多数本就是和《赵正书》差不多的百家杂纂,今人应该在史料意义上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审查。
不同研究者也许会在这两种叙事间各有自己的倾向性,但这里并不是急于是此非彼,而是在这个案例中看到了把史料当作史学的必要性。
《赵正书》与《史记》有关秦二世继位的两种叙事,与其他我们已不知道的叙事之间,当然是一种古老的竞争关系,本来《史记》版叙事已经取得绝对胜利,出土竹书却使这种竞争死灰复燃。
面对这种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偏向任何一方(或如传统史学那样,过度信任《史记》的经典地位;或如当今某些研究者那样,一味偏向时间更早的出土文献),而要把它们都视为一种史学写作,看看各自分别由谁写、写给谁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写。
这样,史料分析首先是一种史学分析。如陈侃理所说:
“我们所要求得的历史之真,不仅限于史料记载的‘事件’之真。……历史学家不会轻易满足于接受胜利者的战报,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的是回到历史记忆战争的现场,考察战争中的各种细节和可能,追寻真相,以及真相失落和被涂抹的历史。”
▌为那些被遗忘的人发出声音
我说过,今天的历史学家应该为所有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去探究现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历史叙述是如何形成的。
当然这主要是年轻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的责任。现有的历史叙述充满了神话和陷阱,因为历史是被说出来的,被制造出来的。
我们要知道,历史越是单一、纯粹、清晰,越是危险,被隐藏、被改写、被遗忘的就越多。我们要拂去竞争的烟尘理解过去,展示历史本来的多种可能。
这两年十分红火的《人类简史》,虽然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很好的历史著作,但书里常常有一些很好的思想和表述。
比如书里讲到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说历史和其他那些所谓科学的学科不同,历史不能试验、实验,不能反复发生,也不可预测。
学习和研究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扩大人类的视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过去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而不是如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呈现在某些叙述中的那样单一和绝对。
近期图文:
反对犬儒,更反对鹰犬:谈复旦葛剑雄教授风波
中共迎来百年寿辰,学者总结八条教训
陶斯亮回忆文革中一桩告御状公案
美国是不是“清教立国”的基督教国家
您是否满意大选诉讼中法官们的表现?
知识精英是最需要启蒙的一群人
衡量国家进步与否、鉴定制度好坏的标准
《今日简史》作者提醒:人类面临两个重要选择
与其说维护英烈名誉,不如说维护统治权威
想象一下2019年底一场核爆炸危害全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