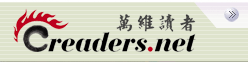这是姐姐这次来美时告诉我的真实故事。 说故事有点牵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一些映象和画面的组合,有少年人的联想,成年人的回思, 而又有一些看不见的潜意识在飞针走线,将飘断的片云一样的思绪织起有点淡有点散有点远的故事。
那时我们家住学校的筒子楼, 父母住南边,我们住北边。 我们的筒子楼在学校最北边,从我们房间的窗子往外看,楼下的一条幽暗的小路, 边上是一块长满野草的荒地, 然后就是学校的北墙。
姐姐讲的这个映象是北墙外的一个深宅大院。我们家住二楼, 面对的正是这个院子。 这是一个古老的院落,院子的右边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正前方便对着高高的厅堂,厅堂的门很大, 所以姐姐可以清楚的描写屋里的摆饰, 有两对太师椅面对面放在屋子两边, 有一个很老但很别致的摇椅, 那里生活着一个长得很白很精致很小巧的老太太, 和三个年轻人。
我对那个房子是有印象的,它坐落在一条幽深的小巷的末端, 我们每次放学要经过这个小巷,过了这一家,就到了校园大门。 我对这个小巷最深的印象是晚上,那里的街灯清冷得有点诡异, 而街两边的人家窗户里只是发出非常虚弱的灯光,幽暗冷漠, 惹人心思发紧。 只有这一家,它的灯光是一种很温情的橘黄色,这种橘黄色散发着安详的暖意,赋予了小巷人间烟火气。
六七年,正值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在一种可怕的盲目的力量驱动下,人们象在汹涌的波涛里, 挤在一条疯狂的破船上,没有理性,却激扬着拯救世界的热情, 没有目标,却崇尚着没有绿洲贫瘠的海岸。大字报象白色的海浪一样翻滚在校园,虚张着空洞的热闹 , 小将们肆意演绎着血腥的浪漫, 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去奔赴魔鬼的盛宴。 白天,大广播,大辩论, 批斗会,忠字舞, 将平素安静的校园变成了游戏园和决斗场。 可到了晚上,家家闭门锁户,森蔽得象是战争年代的城市戒严。 除了时时听到的枪声,连孩子的哭声都听不见。 姐姐那样的半大小人只能缩在家里安静得象小猫一样。百无聊赖中,姐姐趴在北窗下注视着外面的世界, 她的目光停在了对面那个安详的小院。
这个小院是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世界,与外面乱乱哄哄,热热闹闹,粗粗糙糙的气氛截然相反, 当你的目光经过这里,你象透过清晨的露珠看到了天空美丽的倩影,你的心思变成山间的清流小溪,带着你的灵魂流向有着韵律的安宁。
这个家显然是没有男主人的,女主人,便是那个精致的老太太, 老太太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 即便是这个年纪,仍具有优雅的风韵。 老太太的头发盘成一个结在后面,她的装扮 象古画里出来的一般高贵,那样的装扮在那个时代几乎是见不到的。 她的神情总是很安详, 带个老花镜,手里总是在织着一件线衣,她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纤细的身子轻得象片叶子。很难想象她是三个高大的男孩的母亲。 三个儿子永远是很整洁的衣装。 家里的老大不常在家,也许在外地工作吧, 姐姐这样解释着。有时也会看见他,他不太爱说话, 手里总是拿着一本没看完的书,坐在母亲对面的椅子上。 老二比较爱动,老是进进出出的,不是给母亲倒水,就是取什么物什, 每次进出都要碰到那个摇椅,那摇椅就象秋千一样,摆个不停。家里的老三最高, 喜欢拉小提琴, 常常看到他在他母亲边上拉琴,老太太时时会放下手中的活计,抬头和小儿子说点什么,这个年轻人总是弯着身子很谦恭温和地和母亲交谈,母亲的目光象晚春的阳光一样温暖, 充满慈爱的光泽,儿子先很专注的聆听,然后点头微笑,在结束谈话时总不忘亲昵地搂一下母亲的肩头。
姐姐特别提到小儿子很特殊的举止风度,尤其是他对母亲那种特殊的关爱,似乎不仅仅限于儿子对母亲的爱护,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尊崇, 显出做为男人这个世界上的强者应有的宽广胸怀。姐姐说,这个神情举止使她每每回味起来都有一种新鲜的异感,那是一种直逼于心的不可抗拒的柔和了文明,智慧,力量和某种微妙情愫的美感。 直到后来开禁之后看了一些西方的电影,方知这便是西方文明里的绅士风度,这种由古老的骑士精神衍生而来的现代文明生活中男人的基本人格准 则 ,兼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侠义情怀。 男士自觉地把女子作为爱和美的代表,以尊 重和 保护女性为基本教养,崇尚荣誉, 坚守道义,保护弱小,力持公正, 他们勇敢,幽默,风度翩翩, 是西方男子崇尚的贵族精神。(话外: 中国文化男人的高境界是“君子”, 而君子也崇尚道义,但这种道义主要是针对君王和知己 (也是男人), 和女人没关系的。 所以,在欧洲,有为女人而引发的特洛伊战争,没有人会谴责这个女人, 而在中国,会有“女人是衣服,兄弟是手足”之说。 西方世界里,如果 效忠的是一个女人,是很值得骄傲的, 绝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
这一家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度过,和外面的风风雨雨无关,好像那一扇大门,那一道灯光便将现实中粗糙,丑陋,和荒谬 挡在了外面。 这样一幅画面, 印在了围墙外的一双眼眸里,也在这个女孩心灵深处建起了一座神圣的祭坛。它颠覆了这个少女对世界的基本认识,让她看到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优雅高贵,它比外面红太阳普照的张扬癫狂世界更具有迷人的魅力, 它给这个会画画的女孩的心里植入了美和爱的种子, 并使她长出文明的花。当姐姐在四十年后描述这样的画面,仍是动容 : 我感念这份美与爱的启迪,它让我对美的事物有了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我把心灵当做祭坛,从晨光嘉微,夜莺啼啭, 枝叶窸窣;从少女的娇颜,青年人的温文尔雅,老人的智慧安详,去体会这个世界的美。在可以肆意捕捉美的眼里,青苗是长了翅翼的种子,芦苇是大地散落的琴弦,风是传播花香的天使,清晨的露珠儿是人们醒来后所面对的第一对笑靥。 我将美作为神殿里的祭物去膜拜,发现美里蕴涵的自然韵律,寻求美里真理的温暖光明,接纳美里透出的每一抹微笑, 享受美里散发的每一丝爱的芳息。。。
姐说她希望能打听到这一家人的下落,她要登门拜访,感谢他们家开启了一个少女对美善和博爱的门,让她认识到世界上还生活着心灵高贵举止优雅的人们。 ( 话外: 当姐姐上中学时,方知,这个男孩比她高三届, 在学校小乐队里拉提琴。 )
(写于二〇一二年八月底 )
(姐姐的话总让我想起这部电影里这个片段,也是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和电影音乐。)
Lyrics:
As evening fell, a maiden stood
At the edge of a wood.
In her hands lay the reins
Of a stallion.
And ne'er I'd seen a girl as fair,
Heard a gentler voice anywhere.
Whispered, "Alas..."
She belonged, belonged to another--
Another forever.
Yes, she belonged to
the twilight and 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