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遜近百萬字上海文革運動史稿題名為“革命造反年代”,顧名思義要探討為何千百萬民眾捲入造反運動的動因。對此,過去研究中已經有過“受蒙蔽說”、“領袖崇拜說”和“人性險惡說”等等,李遜則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革命名分的誘惑”之說
老高按:文革研究者都知道“李遜”這個名字。去年在加州舉行文革50年大型國際研討會,李遜也出席了,在會上宣讀了學術論文《巴黎公社原則在文革中的蛻變》。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女學者。不過,聽她的發言比較遭罪——聲音不大,語調平板,毫無一點肢體語言,甚至不抬眼看聽眾,聽得我要昏昏欲睡,抓不住她論文的要點和脈絡。沒辦法,金無足赤,不是所有人都有演講才能的。後來編輯《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與當代中國》這部論文集時,才細細讀了李遜的這篇論文,十分佩服!
最近讀到中國愛思想網站上王國偉的文章《“革命名份誘惑”的歷史註解》,評述李遜出版於兩年前的專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讓我對這位女學者更加敬佩。這裡轉載王國偉的文章。
加州大學宋永毅教授在2015年李遜的新書剛出版時就有專文介紹,也一併附後。李遜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出版過近40萬字的《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台灣時報出版公司);她應美國研究文革的著名女教授裴宜理邀請來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當訪問學者,又一起出版過英文專著《無產階級的力量》。她在美國潛心研究幾年之後,毅然辭職重返上海,重新調查上海文革史。她在給宋永毅的辭行電話中說,準備用十年,寫出一本有深度廣度的文革地方史。賈島有詩:“十年磨一劍”,當時年近花甲的李遜再一次表現出青春期的熱誠。而且,既沒有所謂“科研項目經費”,也沒有任何機構支持。十年後,她推出了這本厚厚的學術著作。這種為追尋歷史真相、提煉歷史教訓而執着獻身的精神境界,是那些喋喋不休地鼓譟“要向前看,不要死盯着過去”、“要謳歌中共領導下經濟巨大成就,不要成天翻騰陳穀子爛芝麻、沒完沒了揭中共的瘡疤”的人,想破腦袋也沒法理解的。
“革命名份誘惑”的歷史註解
王國偉,愛思想

20多年前,李遜女士曾跟我說起,她在研究文革中的上海工人運動,我沒在意。20世紀90年代,她去了美國,還是為了這個研究項目。21世紀初,她返回了上海,繼續為這個項目在奔波,但研究的對象和範圍,已經從上海文革工運史拓展為整個上海文革運動史了。今天,剛出版的100多萬字的新書《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下稱史稿),就擱在了我的案頭。當面對耗費了作者20多年美好光陰、憑藉作者的信念和樂在其中的堅持而完成的書稿,不得不讓我肅然起敬。
細讀這部書稿,字裡行間的紛繁、離奇、詭異、荒唐……那個年代所有的人生亂象,向着我們蜂擁而來。對我們這些文革親歷者而言,就像一幅大型歷史風景畫和動態全景畫,它帶着強大的歷史張力,緩緩展開。同時,書稿又像一個平靜的敘述者,故事中充滿着細節和活的生命形態,記憶、經驗連同感情一起被驚醒。
作為一部重要的斷代專史,其歷史使命顯然不僅是滿足當代親歷者們的閱讀,更重要的是要給未來的讀者和研究者們留下歷史。未來的讀者,他們將在遠離當代的時空中,從字裡行間讀出事實的真相,這才是本書最大的意義和價值。
為了確保真實或者說更接近真實,作者長達20多年的歷史書寫過程,不外乎就是當事人訪談、尋找閱讀各類歷史資料、伏案寫作三種方式,三種形式都極其枯燥乏味,其行為過程絕對稱得上是一種高級別的行為藝術。而這種堅持身就是一種態度,有學術的、有人生意義的。因此,我不想僅用職業眼光和學術價值標準來研讀此書,我更願意把書與人之間那種機緣和命運之間的默契作為本文寫作的基點,當然,還是一貫的寫實。
一、讓歷史活過來,是撰史的一種境界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而我們眼下的當代史都是“農轉非”和“臆想性寫史”。虛構或觀念先行,成就的史書也一定是利於撰史人或活着的人的歷史。脫離了歷史現場,又不願花時間和精力去挖掘現場、還原現場,這是當代史學界的通病。而這樣的歷史只能是冷歷史,因為它缺乏生命溫度和學術真誠的點化。
因此,讓歷史活過來,是撰史的一種境界。而活過來的前提是接近真實,還原歷史細節。通達這種境界沒有捷徑可走,只有認真的態度和踏實的歷史尋蹤,腳踏實地在歷史資料中爬梳,其過程十分艱難。無論你是田野調查還是徜徉於故紙堆,艱難如同修煉。所以學界有一種說法,歷史書寫是成本最高,成效最低的學術勞動。有時可以為一個細節、一句話的考證,花去你幾天甚至幾周的時間。尤其是當代史的寫作,文字資料匱乏,許多信息和材料缺乏足夠時間和學術沉澱,所以,查詢資料、去偽存真,更需要一手田野調查和反覆甄別。
20世紀的中國,曾有過不少優秀的學者,通過深入紮實的農村田野調查做出來的學術成果,至今還有生命力。如梁漱溟30年代山東鄉村實驗,陳翰笙帶着薛暮橋和孫冶方做的農村調查,費孝通《鄉土中國》和《江村經濟》,他們都是深入現場,零距離的調查才做出嚴謹的學術判斷,因此,這些著作的學術坐標意義至今尚存。尤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在戰火紛飛的20世紀30年代,在十分簡陋的交通通信條件下,艱難走遍大半個中國,實地考察分析中國歷史建築及其地理和文化環境,寫出《中國建築史》已近80年了,其留下的的歷史建築圖像和著作的經典意義,至今無出其右者。
顯然,做史態度決定立意高度。《史稿》作者,不但有着不同於上述前輩學人的工作難度,而且,因為是當代史撰寫,大量資料閱讀、辨識、甄別就是首要工作。落定的官方檔案至今未解密,只能以散落在民間的資料為主。
雖然文革時期,傳播介質比較單一,但還是生產出非常多的信息資料。作者面對的是海量的傳單、大字報、學習資料、批判材料,還包括公告、文件等半官方材料,還有各類組織的文件和內部資料。資料來源越來越多,不斷發現也就意味着不斷否定之否定,需要十分認真閱讀、比對、核實、甄別。這種閱讀和核實的過程,工作強度非常大,絕對是重體力+重腦力複合勞動,經常為一個剛反覆求證並形成的事實判斷高興不久,就被新發現的材料而否決,這種心神俱疲感,有時真讓人崩潰。
其次,作者基本遍讀文革結束近40年來,一些領導人陸續出版的回憶錄、傳記;各類關於文革的研究著作和資料類讀物;還包括已經出版或半公開的回憶資料和文革中官方公開的各類文件。這些書稿和資料的撰稿人、辦刊人都有各自的立場和角度,甚至有很複雜的情感因素,因此,多重角度釋放的大量信息,錯綜複雜,需要核實比對。但這些材料同上述生產於文革中的資料形成很強的互補性,原始資料加上理性回憶,對形成書稿的基本框架,和關鍵性細節的核實起了關鍵性作用。
二、深入訪談文革當事人——一條更加艱難的取證和印證的道路
對這類固化的文字資料予以活化,不但需要仔細閱讀和分析這些歷史資料,更需要通過經驗和感受的通道,來回看歷史。在還原歷史真實的過程中,作者依然受困於資料的單一所帶來的思維片面性。為了進一步求證,作者選擇了另一條更加艱難的取證和印證的道路——深入訪談文革當事人。顯然,這個過程更加艱難。作者沒跟我說過訪談當事人的具體過程和心理狀態,但作者的多次當事人約談過程,我是親眼所見。
當事人訪談方式,曾有學者做過,但《史稿》作者所規劃的當事人訪談數量和訪談內容非常廣泛。事實上,實際完成深入訪談約120多人,訪談過的人次約數百人次,有的人需要多次訪談。全部訪談記錄整理之後,都給被訪談人仔細確認。這項工作不算上後期整理,即是前期預約、訪談過程,工作強度就非常大,絕對是耗時、耗力、耗精神。而且作者堅持直接訪談,就給訪談帶來了更大的難度。
文革當事人身份狀態各異,身體狀況不一,有的當事人身體狀況很差甚至病重。大部分當事人都在文革中出盡風頭,他們或者是造反骨幹先鋒,或者是文革文膽,無論是使用鞭子還是筆桿子,都做過錯事或壞事,文革後要麼被處分,甚至被判刑。其中當然也有文革中的受害者。這些訪談對象群體的複合型特徵,造成了這個群體心理狀態複雜多變,他們大部分人生狀態低迷,內疚、悔恨、甚至憤怒等等,組合成一個基本的心理狀況。不願再回首那段經歷,是大部分訪談對象的普遍心態。
因此,突破當事人的內心障礙是第一個難題。而要突破訪談對象的心理壁壘,首先作者自己的心態和心理必須健康和強大,因為,一個心理訪談者首先必須是訪談對象的情緒垃圾筒。訪談者自身心理狀態,決定吸納和消化信息的能力,這種方式的撰史做法,作者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做好訪談前的功課和必要的知識資料準備外,更需要意志和心理的充實。同時,面對被訪談人,需要熱情、耐心和真誠。作者為本書堅持了多年訪談經歷來看,平等與理解的訪談姿態十分重要,就容易獲得訪談對象的信任,能順利進入話題。
預約當事人是訪談的第一步,預約有時意外的順利,有時被斷然拒絕,過程充滿戲劇性。需要用十分仔細和理解的態度預約,還要預設訪談話題,不斷的交流和不厭其煩,才能獲得當事人的理解和信任。對一些重要的事件或為了一個細節的核實,有時需要多次反覆訪談,才能廓清。有的當事人文革後受到法律懲處,不再願意重揭瘡疤,寧可把過去帶進墳墓。所以這種訪談針對不同的訪談對象、或者不同的情緒下,該選擇什麼方式預約、訪談,都體現一種藝術性。
訪談原則必須是平等和暢所欲言,訪談的基礎是真誠而不帶先入為主的偏見。今天,不少當事人已經作古,作者長達多年的訪談,也為我們搶救了一段重要的口述歷史資料,在《史稿》成書之外,形成了另一個特殊的史料價值。
三、革命名分的誘惑
《史稿》面對的是長達10年文革史,而作為文革重鎮,上海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史稿》準確地鎖定上海工人造反組織和上海“市革會”寫作組,這兩個上海文革造反運動中的兩個典型對象。從現象上看,北京紅衛兵運動是文革的緣起,反體制、破制度是紅衛兵運動的直接後果。但紅衛兵運動高潮只持續了近兩年,大部分學生就上山下鄉被放逐了。
而差不多時間興起的上海工人造反組織,才是文革的主力軍。上海工人運動和上海“市革會”寫作組,是貫穿上海整個文革史、影響全國的兩個典型符號。如何駕馭這樣大的歷史題材,其實是非常困難的。這需要整合紛繁的線索,梳理出清晰的寫作脈絡,敘事展開要有邏輯,與事實要形成準確對應,還要符合基本的學理規範。作者在《史稿》寫作中,創造性地發現並提出了“革命名分”的概念,繼而發展成一個完整的可擴展的敘述句式:“革命名分的誘惑”,這不但準確而又有說服力地落實了寫作的邏輯起點,也順利地形成書稿主體脈絡。
顯然,作者提出的“革命名分”概念對應的是“經濟名分”概念。經濟名分不但是全世界有史以來的社會群體分層的基本依據。“經濟名分”的階級認定標準是財產占有量,其中包括兩個辨量:一個是財產可量化;另一個就是財產類型可分解。“經濟名分”的歷史合理性在於,它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它充分體現了社會、歷史、意識的邏輯性進步。這樣一種名分,其穩定的基礎是依靠法律的對合法財產的保護,以及超越不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的社會、文化趨同的社會基本倫理道德的支撐。雖然對財產及其來源的合法性解釋,各個歷史階段、各種社會制度會有不同的設定,但基本都認可並維護這種經濟名分。這種整體性社會評介力量不但推動社會發展進步,也是對人類天性的一種保護。
而“革命名分”概念,一般都是在社會特定時期被某種政治力量使用的一種工具。相對經濟名分的理性操作模式,革命名分基本採取暴力模式,包括思想暴力、語言暴力、身體暴力等整體性暴力操作,才能推動這種非理性的社會分層的基本實現。大動亂、大革命、大變動,一定與現存體制和制度結構形成對抗。打破現存制度的前提,就是打破制度的社會基礎,即以經濟名分為標準形成的階級分層。而打破不是目的,而是為建立一個取代現存制度的新的制度。革命名分通過暴力方式,快速地重置了上中下層的社會結構,形成了地富反壞右等下層階級分層、這種非理性的階級分層,成為被普遍認可的嚴重社會後果。
文革初期,區別於北京紅衛兵運動,上海工人運動開始也短暫體現民間性質,但很快就被組織性特徵所替代。上海作為文革實踐的重地,儘管其間有武鬥等亂象,但從開始真正的大規模發動到最後被整體收編,經過的是動員——失控——再動員的過程,民間群氓力量始終得到來自上層的明示或暗示,都體現了行政動員的運作特徵。當實現了這種收編之後的上海文革,已經有了與革命名分對稱的新的政治社會制度。因此,短暫的身體暴力後面,跟着的就是在革命名分旗號下的,長期的思想暴力、語言暴力,隨着這種暴力的不斷落地,也就鑄定了每個人的命運歸宿。
這種所謂的“革命名分”概念的形成,其實已經持續發酵了幾十年。49年後的社會,經歷過各類運動的清洗,已基本消滅並重構了經濟財富概念,只是到了文革期間,發展到概念荒唐性實踐的頂點。但這種逆歷史潮流的社會階級分層一直處在十分尷尬之中。當脫離整個世界價值倫理軌道後,就需要設計一個新的政治倫理,賦予文革行為的正當性。“革命名分”就是這種歷史過程發酵的必然結果。
上海“市革會”寫作組,其早期源頭是在文革之前,從樣板戲的策劃和操作到批《海瑞罷官》,寫作組的早期政治思想霸權症候已經形成。文革中,區別紅衛兵和工人造反隊實行身體暴力,作為上海工人運動形式變體的寫作組,基本是思想暴力和語言暴力的執行者。其主要功能是通過理論的御用轉換,為“革命名分”提供歷史和現實的“合法性”。這也是國家層面的行政性動員機制和控制機制形成的思想基礎,從政治學上或社會基本倫理上,建構一種能產生全民性認同的價值觀,實現人們和社會從抵抗到擁護的意識反轉。
因為文革期間,在“革命名分”概念下,人的身份是被指稱的,隨意、主觀和粗糙的任意指稱,這就給任何手握這種權力的人,有了泄私憤、報私仇的各種機會。而社會群體本身隱含兩個含義,一個是具體的人,一個是抽象的人。“革命名分”只能非常牽強地解釋抽象的人,就如阿倫特所言,“是行政性結構性行為,進而構成了整體性犯錯的條件、環境和氣氛”。而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在作用於一個個具體的人、事件和行為時,就必定是十分離奇和荒謬。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和語言暴力對人的傷害是深層傷害,其傷害的深度和廣度,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思想文化運動。所以,《史稿》作者對上海“市革會”寫作組予以大筆墨敘事的意義也在於此。
同樣,相對於經濟名分的長期性實踐,“革命名分”的荒誕和不穩定性,也就註定了這種模式的短期性。今天,作為國家層面的整體的觀念反撥,需要民族性意識反思。《史稿》正是通過本書,再次提醒我們,我們該如何從感情思維邁向理性思維,並形成社會的整體理性意志和自控能力。
作者曾跟我說,《史稿》是努力追隨《史記》的書寫風格。作為一部當代史,用冷靜筆法,作者猶如講故事,敘事語言文學化,歷史就變得十分感性。從《史記》到《萬曆十五年》,任何一部優秀的歷史著作,無不都是這種敘事方式——感性敘事中,隱含觀點和判斷;建章立意,尤其是標題方式,也就從故事中自然提取,呈水到渠成的自然呈現。
《史稿》有十分合理的謀篇布局,章節標題取捨和每章之後的小結,充分體現了作者精心和設計,以讀者閱讀的方便進入作為寫作價值標杆的態度值得史學界的借鑑。語言樸實反而顯示嚴謹和誠懇,作者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不做過多的裝飾性或者過於矯情的語言。因為,這種牽動萬眾讀者神經和情緒的歷史書寫,本身就會遁入一種情緒失控的怪圈之中。因此,濫用情緒和過於矯情,都是歷史書寫的大忌。從這個意義上看,《史稿》是保持了一種歷史專業主義的矜持和嚴謹,因為,感性敘事方式足以牽動讀者閱讀情緒,並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相應的亢奮和衝動。而這正是寫作者的所追求的理想結果,其實也是作者和讀者返璞歸真的互動過程。
我們今天正處在社會轉型的時代關口,當整個史學界基本都在迴避這段歷史時,李遜女士卻做了一個史學家該做的事。而更該稱道的是,這20多年的寫作成書過程中,既沒有我們眼下許多人追逐的所謂科研項目經費,也沒有任何機構或單位資源的支持,只是憑藉一己之力和心中那麼一點理想,為我們留下了一部未來文革研究繞不過去的《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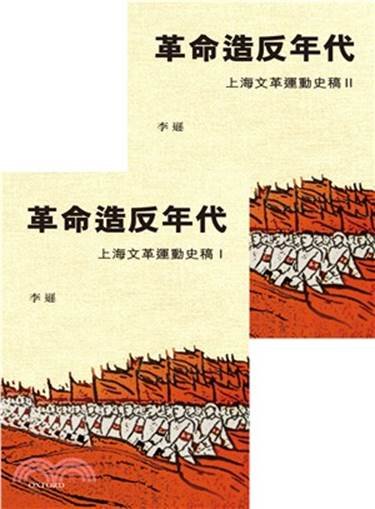
李遜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第一版
文革研究拓展縱深的標誌:讀李遜《革命造反年代》
宋永毅,《動向》雜誌2015年10月號
文革爆發迄今,已經快半個世紀了。海內外的文革研究,已經出現了向縱深拓展的新趨勢。今年年初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兩卷本、近百萬字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便是這樣一個可喜的標誌。一方面,它代表了文革研究從概括性的全國史向細節性的地方史的發展。另一方面,它又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出發,對整個宏觀的文革作出了一些深度的理論思考。
“十年磨一劍”的產物
該書的作者李遜,原是一位旅美女性學者。她可能不廣為人知,但在文革研究圈內卻絕不是新手。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她就出版過近四十萬字的《大崩潰:上海工人造反派興亡史》(台灣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六)。應美國研究文革的著名女教授裴宜理邀請來伯克萊加大當訪問學者後,又一起出版過英文專着《無產階級的力量》(一九九七)。本來,熟悉她的朋友們都以為李遜會一直留在美國,邊工作邊繼續她的研究。不料,十一年前我突然接到她的一個告別電話,說她已經辭去在美國的工作,馬上回上海,準備用十年的時間,重新調查上海文革史,寫出一本有深廣度文革地方史來。接到這一電話,我久久無語……李遜和我是同代人。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曾為所謂的“革命”欺騙而狂熱過,今天一般說來已經很少再有獻身的熱情了。而年近花甲的李遜卻再一次表現出那種久違了的青春期的熱誠──當然,這一次是對曾經欺騙了我們的“革命”的歷史解剖的獻身。十年後,當我看到李遜這本厚厚的學術著作時,我深深地體會到它不僅代表了李遜十年磨一劍的不懈,更包含了一代人對自己以往人生的沉甸甸的思考。
宏大歷史敘事中的細節和偶然
李遜的專著分為四十章,時間上早到“批判《海瑞罷官》”,晚到“粉碎‘四人幫’後的清查”;事件上大到赫赫有名的“一月革命”和工總司,小到鮮有人知的“中串會”及一些“另類思潮”,實在是前後左右、事無巨細,都包羅在她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就來自邊緣的“另類思潮”而論,從憧憬河歸舊道的“共向東”,到直接挑戰毛澤東的王申酉,也無一遺漏。儘管我也是上海文革十年的親歷者,但閱讀李著,仍給我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新掠影之感。
這裡,歷史的新視野不是由抽象的理論,而是由細節和偶然在於無聲處展現的。例如,被毛澤東高度評價為上海一月革命發端的《文匯報》造反派的“接管”,後來曾被認定為全國造反派向走資派奪權的序幕。但根據李遜的深入調查,它其實並不是源於該報造反派的“路線鬥爭覺悟”,相反是一種本位主義和自私自利的訴求。因為打倒了太多的“走資派”,當時的《文匯報》已經處於癱瘓狀態,大多數員工怕被上海的另一大報《解放日報》吞併,個人利益會受到波及,才匆匆忙忙宣佈接管,以保住大家在亂世中的飯碗。不料這件事竟會被千里之外的毛稱讚為“一場大革命”,並拔高到了對全國文革運動起了巨大的方向性的指導作用的程度。
文革研究中的新理論新思考
有建樹的歷史研究,不僅在於深入細節的紮實調查,還在於從萬千細節中升華出閃光的理論來。縱觀李遜百萬字的史稿,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在每一章的史實重構以後,她都立出一個千字左右的“小結”,作一點別開生面的理論探討。如第二十二章“砸聯司──鞏固文革新秩序”的小結指出“砸聯司事件也顯示造反派組織之間,沒有雙贏,只有你死我活。……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文化傳統,又一次在這裡發揮影響。”再如,第三十五──三十六章“新幹部:轉換了身份的造反派們”的結尾總結道:“文革初期造反派到處炮轟和批判,而他們對規則和秩序被破壞後的混亂卻不必擔當責任,一切後果都由原來的幹部承擔,並成為打倒他們的理由。不過,當文革開始恢復秩序,擔任了領導的造反派開始嘗到他們自己破壞秩序的後果……他們面臨的是兩種角色身份的矛盾”──所有這些言簡意賅的小結都有畫龍點睛之妙。
李著題名為“革命造反年代”,顧名思義要探討為何千百萬民眾捲入造反運動的動因。對此,之前的研究中已經有過“受蒙蔽說”、“領袖崇拜說”和“人性險惡說”等等。李遜在她的“導言”里,提出了一種全新的“革命名分的誘惑”之說。李著認為:“共產黨執政後,消滅了以財富為基準的不平等,但又建立了另兩個不平等的等級身份體系:以戶口、編制和工作單位所有制為歸屬的等級身份,即體制身份;以階級鬥爭理論劃分出的本人成份、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現為標準的等級身份,即政治身份。”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則為底層民眾提供了難得的轉換等級身份的機會,而在“所有的政治名份後面,實際仍然是利益和權利的分配,因為革命名分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通過政治運動,提高政治身份以提高其它身份,從而獲得被共產黨嚴控的各種資源。以革命名份改變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夠發動起如此眾多民眾的重要原因。”
讀完李著,我在想:如果全中國每一個省市縣,都能有一部由民間學者撰寫的有分量的文革地方史的專著,那該多好呢。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十二月圖片主題:嘉樹)

柬埔寨吳哥窟,荒蕪了幾百年的廢墟,許多大樹與崩毀的廟宇神殿幾乎合為一體,難捨難分。
近期文章:
沒意思的社會,也還是有很有意思的故事
在海外教文革歷史課不是件容易事
西方學者怎麼看中國大饑荒?
紅歌,在中共奪權掌權大業中起什麼作用
文革的火藥早被紅歌埋下,只待引爆
驅趕之後,如何解決城市化中新移民問題
旁觀者清:外國人看中國言論審查制度
歷史這一團亂麻,是否真能理出線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