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拥抱或同情特朗普主义的人来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一个没有普世价值、缺乏有效国际法约束的世界里,相互对立、实力不均的国家,究竟如何才能和平地解决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的经济、领土和权力争端?历史的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老高按:今天与各位博友和读者分享两位历史学家对特朗普主义的分析。第一位,昆恩•斯洛博迪安,我完全不熟悉,此前从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第二位,尤瓦尔·赫拉利,我读过他的《简史》三部曲和近年出版的《智人之上》(当然都是中文译本),相对熟悉。
赫拉利剖析了特朗普所奉行的世界观,简明扼要,一针见血;而斯洛博迪安揭示了特朗普背后一股“不太可能联盟”的思想渊源,更为深刻。
当然,我“不懂历史,稀里糊涂”(这是博友读者对我的中肯评价),说得对不对,各位尽可得出自己的结论。
特朗普主义的过去与未来:赫拉利“如果还有人对他感到惊讶,就是自欺欺人了”
不懂经也叔的Rust,公众号“不懂经” 2025年4月18日
经过多年的困惑和不确定,一个“后自由主义全球混乱”的轮廓正逐渐清晰。
自特朗普踏入美国政治核心舞台以来,“特朗普现象”便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和时局中的最大变量。他到底是咋回事,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到底想要什么?
特朗普的崛起、执政风格乃至卸任期间的持续影响力,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困惑。这位“非典型”政治人物,其言行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逻辑?他的支持者又被何种力量所吸引?
要理解这一复杂现象,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以及他本人独特的世界观。
最近看到两份资料。一是《哈耶克的私生子》的作者、波士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昆恩•斯洛博迪安,在《名利场》的访谈中,揭示特朗普背后一股“不太可能联盟”的思想渊源。
二是《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精辟地剖析了特朗普所奉行的世界观。在赫拉利看来,特朗普的政策高度一致,世界观又如此清晰,如果至今仍有人惊讶,恐怕只能归咎于故意自欺。
下面我们结合这两位学者的洞见,试着勾勒出“特朗普现象”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它的逻辑演绎以及对未来的冲击。

昆恩•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
一、“新融合主义”:特朗普背后“不太可能的联盟”
许多人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新自由主义的火焰从此熊熊燃烧。然而,斯洛博迪安教授指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发现,并非所有新自由主义者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恰恰相反,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如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与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n Hoppe)等人,反而深感忧虑。
1. 冷战后的焦虑:当“敌人”成为变色龙
斯洛博迪安在其研究中惊讶地发现,在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尽管传统意义上的“红色敌人”看似消失了,但他们所警惕的“利维坦”(leviathan,即庞大的国家机器)依然存在。社会福利国家规模庞大,各种福利项目照常运行。
更令他们警惕的是,一股新的“威胁”浪潮正在涌现——女权主义、环保主义、民权运动、政治正确、平权行动等等。在他们眼中,这些新兴的社会和文化运动,无非是旧敌人的新伪装,是对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构成的新挑战。斯洛博迪安写道,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就像变色龙”。
正如斯洛博迪安所观察到的,右翼人士后来常用的“文化max主义”、“性别意识形态”乃至近期的“觉醒”等标签,实际上都是他们用来描述这些“新敌人”的术语。
这种认知催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联盟,形成了特朗普现在背后的深层力量。
2. “新融合主义”的诞生与“三大硬要素”
面对新的“威胁”,这批思想家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武器。他们将目光投向了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在该书中论证了政府干预市场与个人自由的内在矛盾。
然而,斯洛博迪安认为,默里、罗斯巴德、霍普等人对哈耶克的思想进行了“致命的曲解”。他们不仅继承了哈耶克对国家干预的警惕,更极端地认为,只有某些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在心智上天生适合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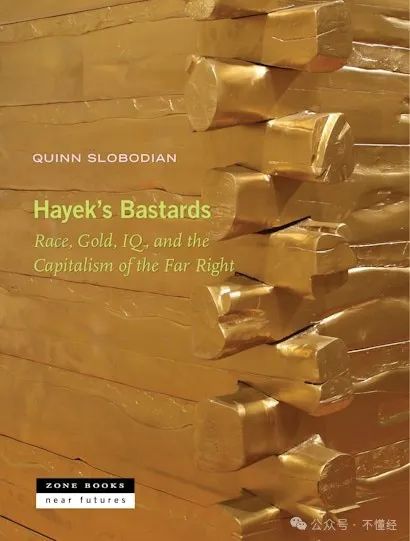
昆恩•斯洛博迪安《哈耶克的私生子》
斯洛博迪安将这群人称为“新融合主义者”(new fusionists)。他指出,他们的政治主张植根于所谓的“三大硬要素”:
硬(天生)人性(Hard-wired human nature):他们相信人性中存在着固有的、难以改变的等级或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人们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同表现。
硬边界(Hard borders):他们主张严格的边界控制,反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认为外来文化和人口会稀释本国文化的纯粹性,甚至拉低整体智力水平,从而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硬通货(Hard currency):他们推崇金本位或类似的“硬通货”,认为只有黄金等实体货币才能对抗政府滥发货币(他们称之为“货币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灾难。
为了支撑这些主张,他们不惜与生物学家、进化心理学家甚至种族民族主义者结成“肮脏同盟”,积极推广将种族与智商(IQ)挂钩的伪科学理论。
1994年出版并引发巨大争议的畅销书《智商钟》(The Bell Curve),便是他们推崇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由查尔斯•默里和心理学家理查德•J•赫恩斯坦合著,暗示不同种族之间存在智力差异,并对社会政策产生影响。
3. “新融合主义”与特朗普的连接
这种“新融合主义”思想,虽然在主流学界备受质疑,却为后来特朗普的崛起以及他所凝聚的“本土主义右翼”(nativist right)打下了某种思想基础。
斯洛博迪安指出,特朗普的第一届政府内部,就充满了试图利用他来实现各自目标的、意识形态各异的人物。其中,新自由主义智库的宠儿亚瑟•拉弗(以“拉弗曲线”闻名)和史蒂芬•摩尔(曾直言资本主义比民主更重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特朗普任内唯一重大立法成就——2017年大规模减税的主要推手。
然而,特朗普政府中也有像贸易代表罗伯特•莱蒂泽这样的人物,他们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加征关税),实际上与传统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原则背道而驰。这种矛盾在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中或许会更加凸显。
更有趣的是,斯洛博迪安认为,“新融合主义”有助于理解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为什么硅谷的部分科技精英会愿意与特朗普站在一起?他解释道:“这表明他们拥抱了一种——坦率地说——按智力与IQ来排名人类能力的意识形态。”
4. 硅谷的“智商迷恋”与“生物化信用评分”
硅谷精英们谈论IQ的方式,可能不像默里等人那样赤裸裸地与种族挂钩,但斯洛博迪安认为,这种对智力或能力的排序思想,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观念。
IQ作为话题:在硅谷的社群和网络论战中,IQ仍然是一个不时出现的话题,有时甚至会牵扯到种族与IQ的关联讨论。
代理指标:更常见的是,这种“排名”思想通过对“能力”、“效率”、“贡献”的强调,体现在具体的政策辩论中。例如,关于H1B工作签证的争论。一方(如特朗普阵营的史蒂夫•班农)可能更强调公民身份所带来的“族群归属权”;而另一方(包括一些科技领袖如马斯克)则更倾向于从经济效用出发,主张让有能力为经济做出贡献的人(无论其出身)获准入境。
“黄金卡”设想:特朗普提出的“黄金卡”(gold card)制度就是上述理念的一个自然延伸。按照该设想,顶尖大学(如哈佛、耶鲁)的外国毕业生,可以通过支付高额费用(例如一百万美元)留在美国,这就是是将基于能力(或学历)的筛选与经济价值直接挂钩。
斯洛博迪安认为,这种“移民定制”策略,实际上是用一种关于能力差异的“暗号”,来暗示其背后的等级观念,将人按某种标准(教育背景、智力、财富)划分并“标价”。
斯洛博迪安将这种趋势称为潜在的“生物化信用评分”,即试图用某种看似客观的、甚至与生物特征相关的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和资格。
5. “硬通货”的回响:从黄金到加密货币
“新融合主义”的第三个硬要素——硬通货,也在当代找到了新的回响。斯洛博迪安观察到,“金本位主义者”(goldbugs)与“加密货币兄弟”(crypto bros)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共同的动机:两者都对由国家控制的法定货币体系深感不信任,将其视为政府“无能”或“干预”的表现。他们都渴望一种独立于政府控制的价值储存和交易媒介,无论是古老的黄金还是新兴的加密货币,都被视为对抗通胀、甚至防范某种“市场末日”的终极保障。
乌托邦式的幻想:斯洛博迪安指出,无论是回归100%黄金储备的金本位,还是实现一个完全由加密货币驱动的经济体系,在现实中都是几乎不可能的神话。
这样的体系会极大地限制信贷扩张,可能导致严重的通货紧缩,扼杀经济活力。黄金和加密货币,在现实中更多是作为法定货币系统的对冲资产或投机工具存在。
极端的逻辑:但有趣的是,这种对“硬通货”的极端忠诚,有时会让他们拥抱可能毁灭资本主义本身的方案。斯洛博迪安形容这类似于一种“准red卫士”倾向: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压倒了经济理性。
在他们描绘的“末日景象”中,当现有金融体系崩溃后,人们可以用随身携带的金块,或者数字钱包里的加密货币,进行原始的易货交易。这是一种将人类生活简化到极致的“阴暗乌托邦”。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往往相信自己能在混乱中“事先得到证实”,并有机会廉价收购他人的资产。
尽管这些硬通货主义者对高度金融化、虚拟化的现代经济有着敏锐的批判(他们准确地看到了其中的荒谬之处),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无论是回归金本位还是全面拥抱加密货币。
6. “直接经济学”的诱惑
斯洛博迪安还提出了一个“直接经济学”(direct economics)的概念,来解释特朗普某些政策和行为的吸引力。他认为,“三大硬要素”——硬人性、硬边界、硬通货,都是对现代生活中过度抽象化、去物质化的反扑,试图恢复一种人们感觉正在失去的“直接感”。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人们会本能地寻求“安全避风港”。这可以是真的黄金,也可以是象征性的身份认同(如白人特权、国民身份)带来的安全感。史蒂夫•班农提出的从“股东价值”转向“公民价值”的口号,恰恰迎合了这种对“直接感”和补偿失落感的渴望。
特朗普深谙此道。他通过一系列“把戏”或“策略”,让支持者感受到一种“政治收益感”和直接的权力体验:
行政权力的运用:总统利用行政命令调整贸易政策(如加征关税),似乎只需“一挥手”就能改变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航向。对于那些将总统视为自身意志延伸的支持者来说,这带来了巨大的赋权感。
直接现金补贴:疫情期间发放的、印有特朗普名字的纾困支票(被戏称为“特朗普元” Trump Bucks),让民众直接感受到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恩惠”。
象征性经济参与:购买与特朗普相关的meme模因币(如“特朗普币” TrumpCoin 或 “MELANIA”币),也被视为一种绕过华尔街精英、银行家、经济学家等传统权威,直接参与“经济”的方式。
斯洛博迪安认为,当有人提供这些“直接经济学”的途径时,人们会感到满足,觉得权力回到了自己手中,变得真切而具体。
二、赫拉利的警示:特朗普的“对立堡垒”世界观
如果说斯洛博迪安侧重于挖掘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暗流,那么尤瓦尔•赫拉利则着重分析了特朗普所展现和奉行的独特世界观。赫拉利认为,人们之所以对特朗普的政策感到惊讶,往往是因为未能理解其内在的高度一致性和清晰逻辑,甚至可以说是“故意自欺”。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未来简史》《今日简史》《智人之上》等书的作者。
1. 自由主义秩序 vs. 特朗普主义零和博弈
赫拉利首先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自由主义世界观:将世界视为一个潜在的“双赢”合作网络。它相信人类拥有共通的体验、利益和价值,这些可以构成普世价值、全球机构和国际法的基础。合作(如全球抗疫、自由贸易)能够让所有参与方受益,冲突并非必然。思想、商品和人员的跨国流动,被视为潜在的互利机会。
特朗普主义世界观:将世界视为一场残酷的“零和游戏”,每一次互动、每一笔交易都必然有赢家和输家。因此,思想、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本质上是可疑的,可能被用来剥削或削弱己方。国际协议、组织和法律,在他们看来,要么是某些国家用来算计另一些国家的工具,要么是一个削弱所有国家、让少数跨国精英受益的阴谋。
2. “堡垒世界”的蓝图与致命缺陷
基于这种零和博弈的认知,特朗普所青睐的替代方案是什么?赫拉利将其描绘为一幅“对立堡垒”的图景:
理想世界:地球被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堡垒,彼此之间由高耸的墙隔开——不仅是物理的墙,也包括金融壁垒、军事壁垒、文化壁垒。虽然放弃了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但特朗普和与他类似的民粹主义者声称,这将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稳定与和平。
被忽略的历史教训:然而,这个蓝图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数千年的历史反复证明,孤立的堡垒并不会安于现状。每个堡垒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安全、繁荣和权力(领土、资源),而与邻近的堡垒发生冲突。
那么,在一个没有普世价值、没有全球机构、没有国际法约束的“堡垒世界”里,这些对立的堡垒该如何解决彼此的纷争呢?
3. 冲突解决方案:“弱者必须屈服于强者”
赫拉利指出,特朗普对此的“答案”简单而粗暴:弱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强者的要求。依照这个逻辑,冲突之所以会爆发,完全是因为弱者拒绝接受现实、拒绝低头;因此,战争的责任永远在弱者一方。
解读特朗普的“怪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会将俄乌事件咎于乌克兰自身。许多人对此感到费解,甚至以为他被俄方宣传蒙蔽。
但赫拉利认为,更简单的解释是:在特朗普的世界观里,正义、道德、国际法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权力对比。既然乌比俄弱,它就应该投降。既然乌拒绝投降(拒绝“和平”,在特朗普的定义里,“和平”即“投降”),那么战争的责任自然就在乌克兰。
格陵兰的例子: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特朗普考虑“购买”甚至“吞并”格陵兰的想法。在他看来,如果丹麦(相对弱小)拒绝将格陵兰割让给美国(相对强大),而美国随后动武,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暴力和流血,责任都在丹麦一方。
4. “弱肉强食”逻辑的三大弊端
赫拉利强调,这种“弱者屈从”的逻辑存在至少三个严重的弊端:
谎言被揭穿:它彻底戳破了“堡垒世界能让所有国家更安全、安心发展”的谎言。现实是,弱小的堡垒很快就会被强大的邻居吞并。世界不会变成马赛克式的独立堡垒,而是会重新组合成少数几个帝国。
特朗普本人也从不掩饰其帝国野心。他在国内筑墙的同时,却觊觎他国(包括盟友)的领土和资源。他对丹麦的态度就是明证——丹麦作为美国几十年的忠实盟友,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按人均计算,丹麦士兵的阵亡率甚至高于美军),但特朗普不仅毫无感谢,反而希望丹麦屈从于他的意愿。
赫拉利直言:“他要的不是盟友,而是附庸。”
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既然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被视为“弱者”而任人宰割,那么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将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被迫将大量资源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领域转移到国防上。结果是,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蚕食各国的繁荣,却让所有人都感觉更不安全。
判断强弱的困境:特朗普主义要求弱者向强者投降,但从未说明该如何准确判断谁强谁弱。历史上,国家对自己和对手实力的误判屡见不鲜,并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
* 1965年,美国坚信自己远强于北越,足以迫使对方屈服,结果却陷入战争泥潭并最终失败。如果美国当初知道自己是“弱势”一方,是否应该提前投降?
* 1914年,德国和俄国都自信能在短期内获胜,结果却陷入了残酷的世界大战。沙皇俄国最终崩溃,德国也因未能预见到美国的干预而战败。那么,当初究竟是德国该向俄国让步,还是沙皇该向德国投降?
* 在当前的东西竞争中,谁又该是那个“识时务”先行投降的一方?
赫拉利指出,与其陷入这种危险的零和思维,更好的选择是共同努力,寻求互利共赢。但一旦你这么想,就已经否定了特朗普主义的基本前提。
5. 回归旧秩序与面向新挑战的无力
赫拉利最后警告说,特朗普主义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它本质上是人类在自由主义秩序兴起之前的数千年里一直奉行的世界观——一种充满了帝国扩张、弱肉强食和无休止战争的模式。人类已经无数次尝试过这种模式,历史早已证明其最终结局。
更糟糕的是,在21世纪,这种“对立堡垒”的世界观不仅要面对传统的战争威胁,还要应对气候变化、失控的人工智能等全新的全球性挑战。这些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它们迫切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
然而,特朗普主义的世界观,恰恰否定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于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往往采取否认或忽视的态度。
结语:看清轮廓,预备未来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人们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稳定性充满了忧虑。经过多年的困惑和不确定,一个“后自由主义全球混乱”的轮廓似乎正逐渐清晰: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合作网络”正在被特朗普式的“对立堡垒”所取代;世界各地纷纷筑起高墙、升起吊桥。
从斯洛博迪安对“新融合主义”意识形态根源的挖掘——那种对“硬人性”、“硬边界”、“硬通货”的执念,对智力/能力排序的迷恋,以及对“直接经济学”的运用,到赫拉利对“对立堡垒”零和世界观及其危险后果的剖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特朗普现象”的复杂性及其潜在破坏力。
如果这条路线继续下去,短期内可能带来更多的贸易战、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从长远来看,其最终结局可能是全球性的冲突、生态的崩溃以及技术的失控。
正如赫拉利所言,我们可以为此感到悲伤和愤怒,并努力扭转这一趋势,但我们或许再也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惊讶了。
对于那些拥抱或同情特朗普主义的人来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在一个没有普世价值、缺乏有效国际法约束的世界里,相互对立、实力不均的国家堡垒,究竟如何才能和平地解决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的经济、领土和权力争端?
历史的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近期文章:
历史学家眼中当今如何应对全球变局的最优对策
川普许多举措我不认同,但背后的逻辑值得想想
胆小鬼游戏结束,认怂的川普怎么找到下台阶?
川普本身可能不算大问题。但他是未来大问题的先兆
真希望有人能拉住他。但愿人类这一次运气能好一点
秦晖剖析西方左派依赖身份政治,形成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
这次大选民主党输在哪里?权威重磅分析终于出来了
世界可以重置,正义不可出局——反白左反的是什么?
他如何重掌美国:关于权力、法律与人格的沉浸式政治解剖
川普在一惊一乍吓唬世界的声浪下,正在真抓实干什么
|
